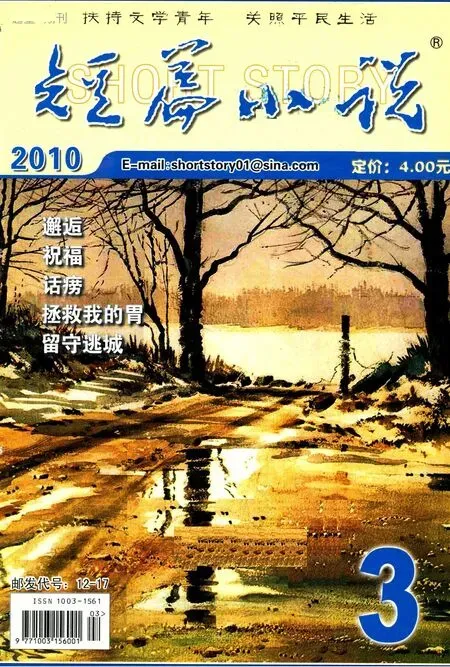大魚
◎廢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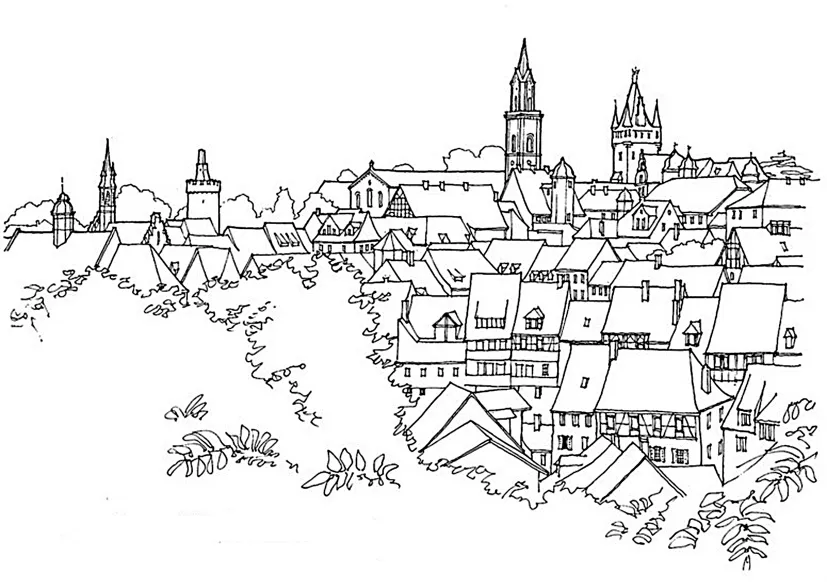
1
今年清明沒有下雨。小毛坐在小賣部門口嚼著口香糖,他想吹一個大泡泡,試了好幾次,泡泡沒吹起來,口香糖倒粘一臉,他把臉上的口香糖扯下來,再塞進嘴里,又嚼了起來。最近到桔村賞油菜花的游客越來越多,小賣部的生意也紅火了起來,以前兩三個月才去鎮里進一次貨,現在隔幾天就要打電話給供銷社,叫他們派人送貨過來。小賣部的葛老頭瞧著小毛悠閑的樣子,心里添火,說話直攆小毛走。小毛當沒聽見一樣,鳥都不鳥他。
屋外頭的大樟樹沙沙作響。小毛一抬頭,枯葉嘩嘩地落在他的臉上,似乎有東西沿著樹梢向著界山嶺那邊游去;小毛回過頭,眼睛驟然放光,一口啐出口香糖,高興地喊著二苕。只見在河對面,二苕沿著田埂一路小跑,不管去哪兒,不管距離有多遠,二苕只會跑,心情好的時候,他奔跑的速度非常快,一溜煙,土路上揚起一層灰塵,他已經從田畈對岸跑了過來。
二苕不是本村人,他什么時候來到桔村,沒人說得清楚,反正嫂子們剛嫁過來、年輕人都穿著開襠褲的時候,就見到二苕在田野中奔跑。二苕的體力異于常人,吃飽一頓飯,能跑上一整天,穿過樹林,蹚過河流,只要在土地上奔跑,他就很滿足了。
葛老頭剛想喊二苕過來捆紙箱子,小毛搶先一步,跑過去拉住二苕,說東扯西。二苕樂呵呵地笑了,他穿著大一號的舊校服,捯飭得有模有樣,像是輟學在家的學生,一開口說話,嘴里含了石子似的,呲呲的,除了幾個簡單的字眼,根本聽不清他說什么。大多時候,二苕也只能通過比劃手勢與別人交流。
小毛跟別人不一樣,他喜歡跟二苕說話,要么是從七姑八婆那里聽來的玄乎故事,要么是沒油沒鹽的家長里短,無論說多久,無論二苕是否在傾聽,小毛說個不停,還不會感到疲倦。他也有想過,是不是要好好教一下二苕說話,免得總是自己一個人說,聊天這種事當然是兩個人有呼有應才好。
葛老頭見狀,不大高興了,嫌小毛閑得沒事做,光礙事,于是對二苕連連招手。二苕沒有理會他,徑直走進小賣部。每次路過小賣部,二苕都會鉆進去拿兩包干脆面,他不多拿,就拿兩包,他不拿別的,就拿干脆面,而且從不給錢。葛老頭也沒打算找二苕要錢,他直接把干脆面擺在柜臺上,隨二苕拿去,一天兩袋干脆面,一個月 60包,頂多 30塊錢,而自己一個月的低保就有好幾百,別說一天兩袋干脆面,就連一天五袋他都頂得住。
村里的勞動力統統上桌打麻將的時候,二苕就幫人干點砍柴、種地、喂養畜生的粗活營生。干完一天的活,別人給他一張10元,二苕會生氣罵人,他要十張1元的;別人要給他二十張五角,他就更高興了。二苕不認識錢的面額,簡單地認為錢就是數張數,越多越好。村里人發現這個規律之后,每次去鎮上辦事順便散一把零錢,回來吩咐二苕干活,順手塞給他幾十張一角。二苕拿到零錢,歡欣得要死,點頭哈腰地說,好人啊,好人。好人這兩個字,二苕發音發得最清晰,也最響亮。在營生方面,二苕也有自己的原則——幫葛老頭干活堅決不收錢。
二苕吃干脆面嚼得嚓嚓響,他喜歡這個聲音,一聽到這個聲音,面餅也變得好吃了起來。他正準備轉身離開,葛老頭一把拉住他,歪著嘴說道:“你吃了人家的面,總得聽人家說幾句話吧。”
二苕望著葛老頭笑了笑,露出兩顆黃色的大門牙。
葛老頭心里想,跟二苕說的那件事,二苕肯定接受不了。他一向快言快語,這會兒卻猶豫了,支吾了半天,竟一個字也沒說出口。
二苕指了指河對岸的界山嶺,他要到山里挖天麻。葛老頭擺擺手說,不是那個事。二苕見葛老頭扶著老腰,猜測他的腰病又犯了,跑過去一腳把紙箱子踢飛,比劃了兩下,老家伙不討媳婦,賺那么多錢干嘛。二苕又樂呵地笑了起來,他不管葛老頭明不明白他手勢的意思,掉頭就跑。葛老頭的話還沒說完,跟在后頭,無論怎么喊二苕,二苕頭也不回。
2
這個季節油菜花開得正燦爛,百畝花田在春風中分出一條小徑,陽光灑在花瓣上,閃爍金黃色的光芒。二苕喜歡這種被陽光刺得睜不開眼的感覺。他常常在正午跑到山坡上望太陽。村里人罵他瘋,三歲的小孩都知道正午的太陽最耀眼,可是二苕覺得陽光射在眼珠上,刺痛之后,全身就舒服了。在一片白花花的光芒中,他能看到許多特別的景象,最令他驚奇的是那一條巨大的鯉魚。二苕也不知道為何能看得見大魚,或許是山影,或許是流云,或許只是因為他怕尖銳的魚刺,始終不敢吃魚。
大魚常常悠閑地出沒在田野、森林、河流,它喜歡在農作物和樹枝里游蕩,青色的鱗甲發出彩色的光線,那是一副迷人的景象,特別是它的眼睛,水汪汪的,像是一泓清澈見底的泉水,水面波光粼粼,多望兩眼就會讓人上癮。二苕跟在大魚的后面,雀躍地奔跑,從山丘到河谷,從村莊到田畈。大魚游弋得很緩慢,像是故意在等待二苕,然而,二苕無論使多大的勁,就是追趕不上它。二苕不停地奔跑,喘著粗氣,直至筋疲力盡,實在跑不動了,才癱坐在田畈里,凝望著大魚漸行漸遠。這時二苕笑了,他笑得很開心,盡管沒有追趕上大魚,他曉得自己迷戀上了這只自由自在的大魚。
在路邊,二苕隨手摘了一把油菜花,一朵接著一朵辮成他喜歡的橢圓形,然后扎成大魚的形狀,今天肯定會遇上大魚的。他把編織的大魚舉過頭頂,一邊奮力地跑動,一邊想象著大魚在油菜花海里游弋的景象,不由得歡呼雀躍。二苕對自己的作品很是滿意,他想把這個玩意送給冬梅。冬梅一定會高興的。
二苕忘性大,他忘了許多事,但是,他忘不了初次見到冬梅的情景。那年鬧饑荒,餓死不少人。家里搬得動的東西都拿去換了芋頭,連做飯的鐵鍋都換了四個饅頭,只剩下一口沒人要的破缸。實在沒辦法,為了活命,二苕被他娘拽著出去要飯。路上聽說桔村田多糧多,娘兒倆咬定牙,下狠心,就是走也要走到桔村。他們忍饑挨餓走了三天,拖著爛草鞋,硬是走到了桔村。娘只剩下一口氣了。一進村,一條狗一只雞都沒有,房前屋后安靜得有些詭異。他娘一下子明白這個村子也沒有了余糧,就痛哭了起來。
蹲在一邊的二苕不知所措,他轉頭發現一個拄拐杖的小女孩躲在門后,正目不轉睛地望著他。二苕不由自主地跑了過去。女孩怯弱地問他是不是餓了。他點了點頭。女孩打開門,從口袋里掏出一把炒米遞給他,說外面冷,叫他把他娘帶回去。
二苕愣了半天,聽她娘哭得厲害,他才轉身跑了回去。不一會兒,二苕又跑了回來,一聲不吭地望著女孩。女孩說她叫冬梅。二苕好像聽了進去,又像沒聽進去,沒等冬梅說完,他哼唧幾聲走了。二苕打那時起就記住了冬梅。
3
小路越往前走,油菜花開得越發喜人。這片肥沃的土地是何強家的自留地。
何強是冬梅的堂哥,也是桔村為數不多沒有外出務工的青年,結識了幾個小混混,學得流里流氣的。山頭有一塊集體經濟林,何強承包下來搞藥材種植,天麻的價格一路走高,一年也賺了不少錢,他沒上繳過半毛錢的租金,嘴上還罵村里不給他申請擔保貸款,好把天麻種植的面積再擴大。桔村人少,黨員更少,村黨支部都是幾個老頭子,再死幾個,連舉手表決的人都沒有了。黨支部看中了何強的年輕,能為村里打點大小事,見他天天嚷嚷著山林的事,干脆拉他進班子充人頭,至少落得個清靜。何強巴不得進入村委班子,好發展他的天麻種植。兩者一拍即合,先讓何強火速入黨,隨后被選舉為村委會委員兼治保主任。
上次,二苕爬到大槐樹上掏鳥蛋,無意瞧見何強跟年輕的女人在油菜地里脫光了。那女人的皮膚真白,水嫩水嫩的,何強松垮的肉緊緊壓在女人的身上。二苕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他覺得睡在那個女人身上肯定很暖和,連何強的表情也變得和平時不一樣,橫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臉的暢快。二苕感覺自己也有些不對勁,他一低頭,褲襠硬邦邦的,嚇得他從樹上跌落了下來,紅著臉,飛快地跑了。自那以后,二苕渾身有使不完的勁。他覺得身體里有一條蟲子在蠕動,導致全身酥癢癢的,他跑到河里洗澡,可是無論怎樣清洗身體,就是消不掉身上的異樣。是不是得病了?二苕郁悶了。直到有一次他無意間在小賣部前看見兩只狗在交配,于是湊過去仔細觀察,瞅瞅摸摸的,把兩只狗嚇得分不了身,不知如何是好,疊著身子往屋后跑。葛老頭生氣地敲了幾下他的腦殼,狠狠地罵他“下流”。二苕大概明白了些什么,似懂非懂地傻笑了起來。從此,他無論是喂豬、挑糞還是扯花生,都自顧地笑著,腦子里一遍遍回放著兩只狗交配的畫面。他傻笑了好幾天,嘴差點笑歪了。這時盤桓在他頭頂的大魚也嘶嘶地叫了起來,很明顯大魚也看透了二苕的想法。
二苕走累了,干脆在田埂上躺下,從口袋里掏出一袋干脆面。干脆面嚼起來像炒米一樣香脆。油菜田不遠處,一群游客趴在地里專注地采摘野菜。南方氣溫稍稍升高,野菜就瘋狂地滋長,把裸露的黃土地裹得嚴嚴實實的。當下正是吃野菜的時候,比如說田畈里的軟萩,桔村人會拿它做成軟萩粑,香甜糍糯,是農家春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佳肴,而在城里,新鮮的野菜和地道的土味都是緊俏貨。無需門票,還能帶土特產回去,這樣的旅游行程最受中年婦女的喜愛,她們一窩蜂地涌入桔村。桔村人看出商機,麻將都不打了,重新抄起舊家伙,熟練地在田間地頭挖野菜,再轉賣給游客,這種錢掙得太簡單快捷了。他們從光屁股蛋子的時候就在田里摸爬滾打,自然對土地熟悉,知道哪兒的野菜長得肥,重秤。
游客、野菜什么的,跟二苕沒有絲毫關系,他不認識野菜,只知道那些隨處瘋長的東西就是賤,不值錢,更不會好吃。二苕將手臂枕在頭下,仰頭望太陽,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空空如也,怎么也尋不著大魚,它躲哪兒去了?二苕的臉色一下子變得陰沉,大魚不見了,就會發生不好的事。上一次大魚不見了就是在他娘死的前一天。一整夜,娘都在不停地吐血,二苕見過血,卻沒見過那么多血,烏黑烏黑的。他端著一個大木盆,接了滿滿一盆。娘生了三個兒子,機靈的都在為過日子精打細算,只有二苕守在娘的身邊,娘的心比灶門星子還涼。二苕剛開始還覺得吐血蠻好玩的,他學著他娘吐血的樣子,咳咳卡卡的,滑稽可笑,娘也笑了。等二苕發現娘的臉蒼白得如同一張白窗紙的時候,才覺得事情不對頭,他趕緊跑到灶頭,拿了一塊軟萩粑塞到娘的手里。軟萩粑是他前幾天去后山偷來的,那兒新建了一座寺廟,來了一位講四川話的老和尚,老和尚說話的聲音像是唱歌一樣,很快就吸引一群虔誠的婦女圍著他打轉,軟萩粑就擱在老和尚的柜子里,柜門也沒鎖,一共五個軟萩粑,二苕只拿了兩個,自己只吃了一個。他娘捧著冰冷的軟萩粑突然哭了,有氣無力地喊道,兒啊,娘要死了,把你托給誰啊,你兩個哥哥連娘都扔下不管,肯定不會管你的,你還是跟娘去那邊吧,免得活受罪。
二苕干瞪著眼,看著娘又笑又哭,他覺得有些莫名其妙。娘怕是瘋了吧。二苕覺得娘要是瘋了那該多好玩。
娘知道命又不是能哭出來的,很快就平靜了,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瞅著那一塊軟萩粑,軟萩粑是由糯米做的,粘性大,中間夾著芝麻糖心。娘知道自己吃不下一整個,她只能咬一口,這一口最好是把芝麻糖心全咬下去。芝麻糖心是軟萩粑的精華。娘愛吃甜食,日子過苦了總希望能嘗到甜味。如娘所愿,她一口咬下了整塊芝麻糖心,只不過這好不容易到口的甜味,如何使勁都咽不下去,芝麻糖心卡在了她的喉嚨里,娘急了,雙手緊掐著脖子,沒掙扎幾下就斷氣了。二苕對死亡的概念或許就是軟萩粑上凌亂的牙印,他也想吃芝麻糖心。
一連幾天,二苕怎么叫都叫不醒娘,他扇了娘好幾個耳光,娘還是沒反應。他就跑到寺廟里找老和尚扯皮。老和尚阿彌陀佛了老半天,才嘆氣地說,埋了吧!
4
躺在油菜花地里的二苕驚愕地跳了起來,干脆面撒了一地。他想起了瘦如干柴的娘,也想起了老和尚的話,“埋了吧”這三個字反復在他的耳邊咬。埋娘是一件輕松活,他在大哥房屋后面的山坡上挖一個坑,把娘拖到坑里,再蓋上土,壓上石頭,完全不費力氣。他做完這些事,沒花幾個鐘頭,他哥根本不知道娘被埋在了自家的屋后。有沒有娘對于二苕來說毫無改變,他像是沒事的人一樣。只不過偶爾發覺來來去去總是自己一個人,行影孤單;特別是睡覺的時候,沒有娘捂腳,腳背總是冰冷。現在關鍵的不是娘,二苕心想,是大魚消失了。一旦大魚消失,就會發生不好的事情。他怕不好的事情會與冬梅有關。
二苕在油菜花田里踏來踩去,尋找大魚。它到底躲哪兒去了?大魚是從來不會膽小的,它吃過何強家的豆子,吞過葛老頭的錢匣子里的硬幣,它龐然大物的體型能躲到哪兒?二苕不停地奔跑,金黃色的油菜花蕊快速地從他眼角劃過,濃郁的花香撲鼻而來。忽然,冬梅的笑容出現在二苕的跟前,二苕的心一下子溫柔起來,笑著露出兩顆大門牙,叫喚冬梅的名字。二苕從小就愛笑,笑多了別人罵他是傻子,他沒有心思理會別人說什么,只希望能天天見到冬梅。
冬梅患有腦癱,雙腳不能行走。他爹死要面子,生了丑姑娘見不得人,一直把她關在家里。等她長到足夠大的時候,他爹才意識到不能將她老鎖在家里,會悶死人的,這才把她放在門檻上,好歹也能看門。冬梅從未走出過院子。
只要是晴天,冬梅都會坐在門檻上,只不過半人高的磚石圍墻擋住了她的視線。她跟父親說過,想把圍墻拆了,種上油菜花,舊掛歷上的油菜花黃黃綠綠的,好看極了。他父親并沒有理會她,徑直地走進后院,埋頭劈柴。
二苕埋了娘,自己又跑回了桔村。他只想做一件事,告訴冬梅有關大魚的一切,那是二苕能想到的最好玩、最美妙的事情。他一路快跑,三天的路程,只花了一天半。一進桔村,他直接沖進冬梅家的石墻院子。此前,他偷偷來過許多次,對這兒的一切都熟悉。二苕見到冬梅,就迫不及待地向她描述眼前絢麗的景象,也許是太緊張了,他的舌頭像是打了結,以前能清楚吐出的幾個字眼也蹦不出口。冬梅叫他慢慢說,他急得用手左比劃右比劃,看得冬梅一頭霧水。一番折騰,毫無進展,二苕氣得扇了自己幾個耳刮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差點就哭出了聲。冬梅扔了一根竹棍給二苕,自己也拿起一根竹棍,在地上畫一座小房子。冬梅開始教二苕畫畫,這是她能在院子里做的為數不多的游戲。二苕如獲至寶,他扔掉了竹子,麻溜地鉆進竹林,找來了一根粗竹竿。斷斷續續地在地上畫了一條大魚,光魚頭足足占去了大半個院子。二苕無法將大魚畫得和他看到的那樣逼真,甚至線條都是歪歪扭扭。他也管不了許多,恨不得要把冬梅塞進他腦子里,一起觀看那條夢幻的大魚和那些絢麗的畫面。二苕一邊畫畫一邊回頭看冬梅,冬梅正認真地欣賞著地上的大魚,時不時發出驚嘆的聲音。他心滿意足了,賣力地打造他的首幅畫作。然而,就差畫完大魚尾巴的時候,何強突然拐進院子,見到興顛顛的二苕,話沒多說,一腳把他踹在地上,叫他趕緊滾。二苕最怕何強了,每次瞧見何強像是見了門板上的門神,躲得老遠。這次挨了何強的一腳,也只能欠欠身子,趕緊爬走。
冬梅他爹聞著聲音出來了,問什么事?
何強是來問冬梅他爹要山頭的地,那塊地正處于山溝的半陰半陽處,種植天麻再合適不過了,但是何強不說田地,卻說,叔,你是老糊涂了,冬梅妹子怎么和二苕搞在一起?我們何家是要臉面的。
冬梅他爹大喝了一聲打斷了何強,氣憤地說,我家的事不用你管,拉著冬梅往屋里走。二苕沒走遠,他趴在石頭墻邊,瞅了一眼冬梅,只見冬梅的眼睛紅彤彤的,淚水直流。二苕的心七上八下,不是滋味。
5
田邊采摘野菜的游客發現了二苕的異狀,她們杵在田埂上,像一群鵝伸長脖子四處張望,急著要去挖掘鄉村八卦。桔村的油菜花長得比人還高,二苕淹沒在油菜花海里,見不著頭,望不見腳。他一口氣跑得老遠,驟然打不著方向,一個踉蹌摔倒在地,壓倒大片油菜花。二苕瞅著黃燦燦的油菜花,腦海閃過五顏六色的光芒,好一會兒,他才緩緩睜開眼,太陽明晃晃的,望著特別舒服……
二苕忽然覺得耳朵灌入了風,涼颼颼的,難道是大魚的呼吸,他驚得坐起來,左右打量,不見任何蹤影。奇怪的是——冰涼的風又往他耳朵里灌,弄得他渾身酥麻,八成是大魚的惡作劇,大魚常常玩這樣的戲法,但是耳廓敏感搔癢的滋味讓他忍不住想起了交配的場景,何強身子下面的裸體女人扭動的身子,發出性感的呻吟。他閉上眼,女人光滑的皮膚、豐滿的胸部,像是貼在了身上,熱乎乎的,無論他怎么甩都甩不脫,他又好奇又羞怯,或許,此時此刻大魚正臥在他的身上挑逗戲弄他,大魚比二苕更懂得這些秘密。這種舒服的感覺,也讓二苕想到冬梅。然而,一想到冬梅立馬睜開眼,翻身起來了,他明白想象冬梅裸露的身子是可恥、要不得的。他趕緊查看四周,沒有大魚的任何蹤跡,卻發現茫茫花海之中,自己孤零零的一個人。他有些寂寞,也有些失落,更加想念冬梅了。
要是擱在以前,他干脆跑到冬梅家,找她說會兒話。冬梅每次都是門檻上,似乎除了門檻,她就沒有在別的地方出現過。她捧著一只紙風箏,左右端詳,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直夸風箏五顏六色,真好看。
風箏是葛老頭做的,鳶兒畫得有模有樣,再貼上五色花紙,栩栩如生。葛老頭祖上是糊燈籠的,手藝是天生的,他最拿手的就是做紙活。以前他一年也只在農忙,沒人來打麻將的時候,才糊上幾只風箏,自己把玩。二苕見著風箏,嘴里發出呼呼的聲音,張開雙臂在院子里跑來跑去。他似乎把自己當做一只風箏,呼啦啦地想要飛上天。
我們去放風箏吧!冬梅小聲說道。二苕沒反應過來,傻愣在一旁。冬梅把風箏舉過頭頂晃了晃,放風箏啊。二苕疑惑一小會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猛地點頭答應。
我不會走路,那你得背我。冬梅噓了一聲,說道,小聲點別讓我爹知道了。
二苕點點頭,放慢動作,數著后院的砍柴聲,一步一回頭,如臨大敵般走到冬梅跟前。冬梅被二苕滑稽的動作逗笑了,縱身一躍,趴在二苕背上,“走”字還沒說出口,二苕一股勁沖出了半人高的石墻院子。冬梅仿佛看見二苕在地上畫的那一條大魚打了一個激靈,活了起來,左右搖動著尾巴,鉚足勁帶著她沖出水面。她緊緊地扣住魚鱗,身子貼近魚背,紅通著小臉,她好想大聲地喊出來,又怕驚動了他爹,只得緊咬著嘴唇,把興奮氣憋在小小的心房里。
出了家門,冬梅一把拉住二苕,用力將他拉上了魚背,他們倆并排坐著,二苕從沒追上過大魚,也沒坐過魚身子,這是第一次,他怕冬梅掉下去,特意扶著冬梅的肩膀。大魚向著山那邊緩緩游動,冬梅耐不住內心的喜悅,東張西望,她從來不知道家外面有一口塘,倒是那幾只走來走去的大白鵝,每天都會見到好幾次。塘邊種有一排叫不上名字的樹,除了石頭墻里的樟樹,她也不認識別的樹。這些樹還開著白色的花骨朵兒,她猜測這些天聞到的花香就是從這兒飄來的,大魚從樹梢游過的時候,順手摘了一朵小花,她塞在鼻子里,真香。石頭墻外面到處都是新鮮的東西,冬梅的眼睛都看不過來,頭暈目眩。她完全忘記了門口的那條光滑的門檻,也忘掉手中的風箏,只催促著大魚游快點,去更遠的地方。二苕見冬梅笑了,他也樂開了花,欣慰地拍了拍魚身。大魚也喜歡冬梅,它搖動魚鰭,游得更快了。
他們一同游過桔村的白墻烏檐,幾只雀兒懶散地漫步在石板路上,哪怕人走到身邊,它們還不愿飛去。老老少少都去摘野菜賣錢,村子寂靜無聲,靜得有些奇怪。二苕很少說話,冬梅卻一遍一遍重復著再遠點、再遠點。大魚游了十幾里地,翻過山頭。大魚在天空游蕩,二苕和冬梅坐在山丘上,眺望著生長在河岸邊的百畝油菜花,那些數不盡的黃色小花朵像是一條碎花長裙,冬梅恨不得把它穿在身上,喃喃自語道:這么多花一同開放,是不是也會一同凋謝,要是這么多花都謝了,真可惜啊。
二苕管不了油菜花可惜不可惜,他躺在山坡上,看著冬梅的背影,驟然又想起了那位赤裸的女子,他無法阻止這樣的想法,心怦怦地跳動。他想冬梅睡在自己身邊。二苕拍了拍冬梅的肩膀,示意冬梅躺下。他沒想到冬梅真的會躺下,一下子不知所措,眼睛直愣愣地盯著天空。天是灰蒙蒙的。二苕聽到了冬梅的呼吸聲,潤如春雨,攪得他的心亂七八糟。二苕好想翻過身睡在冬梅身上,他曉得那樣做不好,但是他又禁不住那樣想。他一動不敢動,四肢僵硬,全身發麻,似乎下一秒就要暈死過去,即便如此,他還是面帶微笑地望著冬梅。一旁的大魚嗷嗷地叫了起來,這讓二苕不知如何是好,直罵大魚是個壞家伙。
今天的天也是灰蒙蒙的。二苕踩著油菜花站了起來,他眺望著界山嶺,或許,他的大魚就在山的那邊。
6
那天,二苕摘了一大把各式各樣的花兒送給冬梅。冬梅接過著花束,咿咿呀呀胡亂地唱著歌,這些歌是從大魚那兒學來的,大魚在高興的時候,會哼唱古老的歌謠。冬梅他們又計劃去山的另外那邊,然而剛出門的時候,就被冬梅她爹發現了。他爹愣了半天,才回過神,緩緩閉上眼,一副欲哭無淚的樣子說:我何某粗人一個,一輩子是要臉的人,就聽不了別人笑話,生了你,我的臉系到了褲襠,今天,我的臉算是貼在了地上。
他爹一把將冬梅提進門檻,不由分說地痛打了她一頓。冬梅叫都沒叫一聲,眼睛像燈泡一樣瞪著她爹。他爹見狀,氣不過,下手更重了。站在門外的二苕鬼哭狼嚎,像是棍子全都落在他的身上一樣,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打滾。他爹一把鎖了大門。
二苕悄悄躲在院子外,站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屋子里沒有一絲聲響,他才離開。那天的夜黑得特別早,二苕像是一塊抹布,歪歪扭扭地甩在石板路上。他心疼冬梅,埋怨他爹下手真狠,比何強還狠。二苕沒看清路,一把撞倒了葛老頭。葛老頭的酒喝了不少,扯著二苕發酒瘋,他拍著二苕的臉說道,咋了?想媳婦了?一個二苕,一個癱子絕配啊。二苕一聽,的確他和冬梅蠻配的,心中的怨氣一消而散,呵呵地樂了。
葛老頭問二苕想娶冬梅不?二苕拼命地點頭。
五千塊。葛老頭豎起五個手指,你只要有五千塊錢做聘禮,你就可以娶她了。上次我和冬梅他爹喝酒,冬梅他爹親口說的。
二苕高興地從褲襠里掏出一個破舊的皮包,拿給葛老頭看。葛老頭說,這里頭都是分分角角,值不了多少錢,都是那些喪盡天良的騙你干活。你得學會認錢。五千塊你知道多少嗎?你只要從你哥手中把你低保的折子要回來,何止五千塊,要多少有多少,到那時,你領國家的工資,也算吃皇糧的。葛老頭忍不住罵道,你哥算是個狗屁的監護人,拿你的低保花,又不管你的死活,他怎么不斷子絕孫啊。
二苕搖頭,自從把娘埋在他哥的屋后,他就再也不想回到那個地方去了,更不想見到他哥。
葛老頭悻悻地說道,我兒子要是還活著,和你一樣大,也要娶媳婦咯!說完,葛老頭醉臥在石板路上不省人事。二苕也興高采烈地挨著葛老頭在大街上睡了下來。終于可以娶冬梅了,一想到這兒,他一夜沒合眼。
認錢是第一步,二苕在這方面真花了不少工夫。最后還是小毛聰明,他給二苕想了個辦法。小毛讓二苕什么面額的錢都不認,只要能識別綠色的50元人民幣就行,干一天活,只要一張綠色的紙幣,其他的一概不要,誰家想賴賬,就去誰家躺著,趕也不走,別人肯定會給的。二苕一下子就學會了這個法子。葛老頭還特地給他做了一個牌子掛在身上,教他哪兒都別去,就在小賣部外頭坐著,總會有生意上門的。
果不其然,二苕的第一筆生意很快上門了。何強叫他去挖天麻,而且預先給了一張綠票子。雖然何強有這樣那樣的不好,但只要他給錢就行。好歹何強也是冬梅的堂哥兒。一想到這里,二苕從褲襠的破皮包里掏出了那張綠票子,左看右瞄,又心滿意足地塞進褲襠。摸到了錢,二苕立馬渾身是勁,有錢就可以娶冬梅了,他越跑越歡,界山嶺近在眼前。
7
二苕沒走幾步就聽到小毛在后頭喊他。小毛跑得一身汗,喘著粗氣拉著他說:冬梅被一群外地人強行接走了,車上都貼著喜字,聽說她要嫁到隔壁省,光彩禮錢就是八千元,還帶來不少物件,你快去看看。
二苕開始還聽不大明白。小毛又重復了好幾遍。二苕明白冬梅被接走了,大魚在他心里驟然破滅,他一下子蹦噠了起來,面紅耳赤地往村子跑去。等他沖進冬梅的家,迎親的車隊早已離開,石頭墻院子擺滿了貼著囍字的嫁妝,冬梅他爹一臉失落地坐在門檻上。何強瞅著二苕恍恍惚惚地溜進來,一把拉住他,叫他趕緊走。
騙子,你們都是騙子。二苕一肚子的怒氣爆發了,沖上去和何強扭打在一起。二苕不及何強身強體壯,沒占到丁點優勢,很快就被何強按倒在地,他徹底放棄了抵抗,任憑何強的拳頭落在臉上,鮮血直流。他發出殺豬般的嘶叫,仿佛挨頓打,能讓他舒服點。
二苕不哭不叫,一動不動地坐在地上,表現得出奇的安靜;反而是何強喘著粗氣,嘴里罵罵咧咧的。二苕立起來,一米五八的個頭不高,但足以讓何強感到一股不尋常的氣勢。二苕死死地盯著冬梅他爹,好一會兒,才走出了院子。
望著二苕離開的背影,冬梅他爹捂著臉,驟然哭了起來。
二苕一路小跑,回到了土地廟旁的小棚子,土地廟不屬于任何人,沒人叫他從那兒離開,那塊地方就成了他唯一安身的家。土地廟不大,大概只能放得下一張八仙桌,二苕在旁邊搭的棚子可比土地廟大得多了。土地廟有絡繹不絕的信徒朝拜,擺滿各色祭品。二苕覺得跟土地神做鄰居剛剛好,餓的時候還可以跟土地神借點吃的。只不過信徒總會燒大把的往生錢,煙太大,能把他熏得淚流滿面,土地廟什么都好,就這一點讓他不滿意。
二苕躲在棚子的最里面,輾轉反側,像是身上長了虱子,怎么調整姿勢都不舒服。他想,冬梅去那么遠的地方,她該怎么辦?冬梅走了,自己又該怎么辦?大魚突然在二苕的腦海翻騰起來,仿佛要把他的腦門給擠破。二苕不停地搖頭晃腦,想要把大魚從腦海中甩出去,大魚如同感應到了他的所思所想,轉頭向他的腦海深處游弋。這時,二苕看到了他娘在床邊吐血;冬梅被一隊轎車帶走,這都是令他傷心的事,偏偏發生在大魚消失的時候。都怪大魚!他迷戀大魚,追趕大魚,大魚卻跟自己結了仇似的,老欺負自己,簡直太壞了。一想到這兒,二苕的身子也跟著顫抖起來。要不是大魚在油菜田里突然消失了,他也不會有這么多的噩運。二苕刷地站起來,打定主意要去找大魚復仇。他從袋子里摸出一把鐮刀,這是何強給他去割天麻的工具。
二苕沖出棚子向油菜田跑去,他知道大魚一定躲在某個不顯眼處,好讓他找不著。他鉆進油菜花田,肆意地踩踏著油菜,而且越踩越有勁。他把所有的勁頭都撒在這一大片油菜花上。如果把這些油菜花統統都給踩爛踏平,大魚自然沒有地方躲藏。正在這時,油菜花里傳出了簌簌的響聲,夾雜著微弱的呻吟聲,是大魚在嘲笑他嗎?二苕拿著鐮刀循著聲音跑了過去。呻吟聲越來越急促,越來越強烈。他走近一看,何強又和那個女人光著身子纏在了一起。二苕第一反應:這是不好的事,是下流的行為。他看見年輕女人甩動的乳房,他耳根子通紅,心里熱血沸騰,由此驟然想到了冬梅。他將體內的那股沖動轉化為怒氣,兩眼放著綠光,對著何強揮舞著鐮刀,從喉嚨里發出嘶吼,仿佛要把何強四分五裂。這可嚇壞了何強和那個女人,他們顧不了光著身子,東躲西藏。何強諾諾地說,冬梅的事跟自己無關,他只想得到那塊田地,把冬梅賣到隔壁省是她爹的主意,不是賣,是嫁,呸,賣就是嫁,嫁就是賣,賣和嫁是一回事。他給冬梅找了一戶好人家,有的是錢,不會虧待冬梅的。一提到冬梅,二苕就沒了主見,他傻愣了一下,想捋順事情,腦子里卻亂成一攤漿糊。難道冬梅真是被她爹賣了?
何強趁機一把奪過二苕的鐮刀,一腳把他踹倒在地上。二苕順勢閃了過去,搶走他們堆在一旁的衣服,撒腿就跑。
天完全黑了下來,桔村家家戶戶一邊收看著《新聞聯播》,一邊討論著今天冬梅出嫁的事,有人愿意娶她,也算是沒白當一回女人。外頭石板路上,二苕手舞足蹈地甩著手里的衣服。他大聲喊叫,吸引了不少村民圍了過來。葛老頭拍了拍二苕的肩頭,問他怎么了?這不是何強的衣服,從哪兒搞來的?
二苕對著葛老頭翹起了兩根手指,趴在地上學著何強的動作,臀部蠕動著,嘴里發出呻吟的聲音,臉上一副享受的樣子。村民一看就知道發生了什么,一哄而散。只留下葛老頭,他語重心長地對二苕說,你別鬧了,快走,回到家里去。
家?二苕癡癡地望著葛老頭。
對,家,你娘生你的那個家。
沒家。二苕泄氣地躺在冰冷的石板路上,不愿起來,像是一只忍饑挨餓的流浪貓,等待著漫漫長夜早點過去。他翻過身,望著亮錚錚的月亮。好大一輪圓月,月光落在他眼里,呈現出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大魚從他的跟前悠然游過,他伸手去抓,似乎能抓住一片閃閃發光的魚鱗,魚鱗上映著冬梅的臉。冬梅說,她想去更遠的地方。的確,她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
冬梅喜歡大魚,大魚也喜歡冬梅。二苕抹干了眼淚,即便為了冬梅,他也要找到大魚。他再次沖到田畈里,發瘋地奔跑,一片片油菜花被他踢倒踩爛。何強報了警。警察沒來之前,他作為治保主任組織村民圍捕二苕。
追捕行動一直持續到夜晚,桔村百畝油菜花田,大批油菜倒弋在田埂上,村民追逐著二苕。二苕開心地笑著、叫著、做著鬼臉,嘲笑那些掉在他后面的老老少少。突然,他一腳踩空,一下子滾到了田溝里,腿折了,趴在地上一動不能動。就在這時,他覺得耳朵灌入了涼颼颼的風,是大魚,他憤怒地抬起頭,大魚正安靜地看著他,魚鰭旁伸出了一只手,冬梅探出了頭,喊他上來。二苕喜出望外,應了一聲又一聲,全身又有了勁,輕靈地從地上爬了起來,拉著冬梅的手,躍上了魚背。
大魚游向了一片雜草叢生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