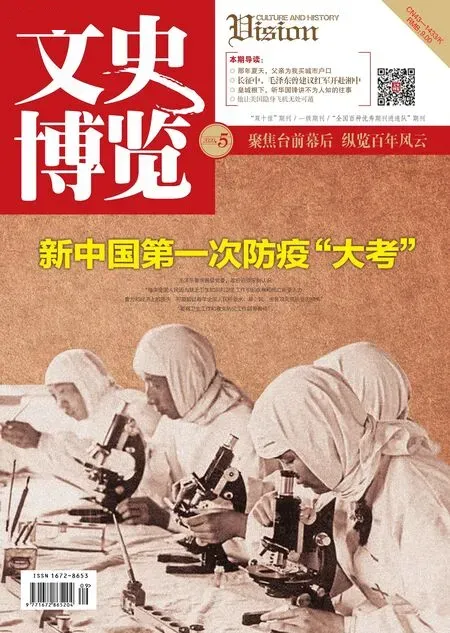新知
統一貨幣政策拖垮大秦?
秦 鑒 《莽撞的貨幣改革導致秦朝經濟崩潰》

一般認為,統一貨幣是秦始皇的歷史功績之一。但當代學者朱嘉明卻提出這是秦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什么功績反而導致秦朝滅亡呢?
咱們來簡單梳理一下這個脈絡。強行用秦國的半兩錢馬上取代原來六國的貨幣會造成以下這些結果:第一,原來六國人民的財富都是以本國的貨幣來計算的,廢除舊貨幣會導致人們的財富大幅度貶值,甚至瞬間蒸發,社會各個階層面臨同樣的處境,從而引起普遍的社會恐慌。第二,民間要獲得合法交易的半兩錢,可是秦政府沒辦法短時間內向市場提供足夠的貨幣,人們只能低價拋售物資,加重了民間的損失,造成“物賤錢貴”。第三,由于新錢稀缺,又會導致人們囤積新錢,這就更加重了市場上的通貨緊縮現象。第四,因為通貨不足,人們往往在互相熟悉的小范圍內,用以貨易貨的方式進行交易,或用當地人們普遍能接受的某種商品作為一般等價物,權且充當貨幣使用,比如楚地的人可以用當地經常使用的布匹臨時充當貨幣。第五,嚴重的通貨緊縮,使得交易活動陷入停頓,想買的人買不到、想賣的人賣不出,商人破產,并連帶更多的手工業者、農民破產,這種急凍式的經濟蕭條,造成大量人口破產,從而引發社會動蕩,也為六國舊貴族造反提供了廣大的社會基礎。
說到這兒還必須提及一個關鍵的背景問題:社會如果全都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全部的財產只有10%是以貨幣形式存在的,那就算改革手段很激進,消極影響也有限,而戰國末年至秦朝時期,社會商業活動相當發達,因此秦朝激進的貨幣改革給社會造成的破壞應該是相當大的。
瘟疫才是甲午戰爭中日軍的最大敵人?
言九林 《傳染病與腳氣病,才是甲午戰爭中日軍的最大敵人?》

甲午之戰影響近代中國及東亞歷史走向甚巨。在這場戰爭中,日軍的傷亡很大,但據日本學者藤村道生的觀點,其人員傷亡絕大部分非戰爭直接導致,而是來自疾病:“日本士兵的真正敵人是瘟疫。因為沒有建立預防體制,衛生設備很差,所以許多人病死了。在出征期間,入院治療的達17萬人。其中因重病而被送回國內的,約占派往海外士兵人數的三分之一,達67600人。在17萬入院患者中間,因戰爭而負傷的不過4519人。其余則是或患赤痢、瘧疾、霍亂等傳染病,或患腳氣病。”
藤村此說并非虛言。比如,進攻澎湖島時,日軍的戰斗傷亡甚少,但“患瘟疫而死者達980人,埋骨于馬公城東南陽明門外,病者更不計其數”。再如,進攻臺灣的日軍合計3.7萬余人,直接死于戰事者為164人,間接死于疾病者卻高達4642人。
傷病員回國,自然也會把傳染病帶回日本國內。有統計稱,開戰初期,日本國內已出現霍亂,導致3.9萬余人死亡。戰爭中期,日本國內又暴發了痢疾,共有15萬余人患病,3.8萬余人死亡。1895年進攻澎湖島的日軍染上霍亂,傳回國內又造成4萬余人死亡。政府與軍方吸取教訓,開始在戰地、港口與火車站設立檢疫所。
除了各種傳染病,因飲食中缺乏維生素B1而引起的腳氣病,也給日軍造成了極大的損失。這種疾病的癥狀是腿腳麻木無力,慢慢嚴重至感官衰退、全身虛脫,最后死于心臟機能不全。當時在以精米為主要食物的約17萬日本陸軍當中,患腳氣病者多達3.4萬余人,約4000人死亡。
脫去包公的外衣,發掘宋朝的真實面
鐘洋彬 《脫去包公的外衣,發掘宋朝的真實面》

在關于包公(包拯)的影視作品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包公與權臣顯貴的故事沖突。包公的地位與權臣顯貴相比天差地別,但他有三大權力道具:尚方寶劍、三口鍘刀、丹書鐵券。而事實上,尚方寶劍直到明朝萬歷年間才出現,三口鍘刀更是從未出現在歷史上,且鍘刀也從未在古代成為行刑工具。至于丹書鐵券,它在兩宋初年曇花一現后,直到明朝時才成為常制。因此包公也不可能擁有丹書鐵券。
那么宋朝法官在面對權貴罪犯時又該怎么處理呢?
宋太宗時期,許王趙元僖擔任開封府尹,犯錯被御史中丞彈劾。許王向太宗求情,太宗當即大吼:“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摘;汝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邪?”可見,在宋朝的司法制度面前,法官只需要憑借律法,就可將犯罪的權貴們繩之以法。
在包公審案的整個過程中,訴訟雙方被帶上公堂之后,需要一直跪在堂下。但其實,在宋代,除了特別情況之外,訴訟雙方根本不用下跪,只需站立即可。朱熹當地方官時,也曾說道:“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跂立”的意思是踮起腳后跟而立,可見百姓到官府告狀也不用下跪。跪著受審的制度直到元朝時才確立,之后元明清三朝逐漸將“跪”列為訴訟人的標準動作。唯有取得功名的讀書人,才不用在公堂下跪。
另外,文藝作品中關于包公大義滅親的情節,也忽略了法律程序上的程序正義。宋代司法特別講究親嫌回避,并設置了嚴格的回避制度。宋朝法院在處理案件之前,都會先核定有無需要回避的執法人員。所有跟訴訟雙方有親戚、師生、上下級、仇怨等關系的人,都必須回避。
1918年西班牙流感,為何中國死亡率遠低于世界
醫藥導報社 《1918年,中國靠中醫藥挺過了西班牙流感》

1918年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中國也未能幸免。根據當時的統計,北京有1/3的人口被感染,哈爾濱有40%以上的人口被感染,而廣州、上海等城市被感染的人就更多了。但流感在中國造成的死亡率遠低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大部分地方只有幾百人死亡。據統計,當時上海的流感死亡率為千分之1.3,而在歐美等嚴重地區,死亡率在10%左右。
中西死亡率存在如此大的差異,不得不說是中醫藥發揮了重大作用。西班牙流感在中國暴發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流感的措施,包括“在房屋內噴灑石灰粉或石灰水,焚燒中藥大黃和蒼術來消毒空氣”;在飲食方面“建議村民每天多食用綠豆和冰糖熬制的粥”;對于有流感病人的家庭發放中藥大鍋湯等。
1918年11月6日,上海 《申報》 全文刊登了當時定海縣知事馮秉乾撰寫的 《救治時疫之布告》,這份布告以通俗的六言詩形式公布了由清代醫家吳鞠通治療流感的名方“銀翹散”, 同時建議群眾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保持自身良好的衛生狀況。
事實上,流感在中醫歸為傷寒或溫病一類,漢代張仲景創立的“麻杏石甘湯”,清代吳鞠通的名方“桑菊飲”“銀翹散”等對流感均有較好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