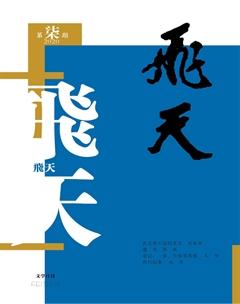揚揚張掖
賈雪蓮
一九五四年,考古學家在張掖市山丹縣城南發現距今約四千多年的四壩灘遺址,屬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馬家窯文化類型。同時發現了近千年前創立張掖的先輩的青銅像,其背部刻有篆體字:揚揚張掖。
——題 記
風
“阿蘭拉格達”,彩色的山丘。這個裕固族語言單詞,在誦念時需要輕輕開啟舌尖,慢慢發音,再款款吐出。世代依這座七彩丹霞山群居住的裕固族人民,用這樣一個回味悠長的詞語表達著對這山岳的熱愛和眷戀。站在最高點,舉目眺望,長久的凝視,長久的靜默,長久的相思。
她奇在七彩。我們看見過的丹霞地貌,大多是赭紅色;紅色的砂礫巖,接近佛的顏色。但這一片土地,她是彩虹女神的化身嗎,抑或是誰家調皮的孩子打翻了國畫大師的顏料罐?紅、黃、橙、綠、白、青灰、灰黑、灰白等多種鮮艷的色彩,染紅了高臺、染綠了肅南,絢麗了甘州境內無數的溝、無數的山丘,裝點了三十萬家庭的窗戶和窗子里每一個多姿多彩的童話夢!
她險在冷峻。斑駁的色彩下,一座座大山、小峰不陰柔、不俗艷,反而是陽剛的、雄渾的。擎天的石柱、高聳的麥垛、匍匐的恐龍、昂首的金龜、打坐的僧侶、微啟的大扇貝,層理交錯、四壁如削、奇峰突起、峻嶺橫生。是逐日的夸父,還是射日的后羿,飽飲了張掖黃酒,攜著一身神功,提著一把鬼斧,在這里砍呀、斫呀,劈開了上天的秘密,留下了磅礴大氣的天地杰作?只有荒蠻最配她。
她靈在自然。無需雕琢,不用打磨,千年的流水,萬年的光陰,鑄造了她的容顏,她的氣質,靈妙天樸,自在舒展。朝左看,她是艷麗的,似染晨霞的臉蛋,似披彩紗的少女;朝右看,她又是素淡的,是帶著鄉愁的中國水墨,是《石蕖寶笈》里的枯荷;朝前看,她是跳動的音符,是層次分明的色塊,擺動著一片片黛青、暗褐、丹紅的裙袂,袒露自己;朝遠方看,她又是變化的,神秘如水中的洛神,晴有晴的明媚、雨有雨的迷離,春有春的生動、冬有冬的沉淀。
她秀在幽靜。我曾兩上七彩丹霞地質公園,每一次踏入溝中,循谷而入,天闊云低,安靜、幽深從兩側的山巒中無聲襲來,不見喧囂,沒有紛擾。坑谷幽靜、千仞肅然,人移景變,幽洞通天。駐足的人,莫不忘卻紅塵的煩擾;休憩的心,無不浸染原野的安靜。神秘的茅屋里,有多少傳奇會歌唱?煙崗霧靄中,有多少秘密未解開?層層疊疊的沙礫中,有多少故事被風化?
盤踞山頂,詩眼怠倦。就讓我化作山里的一片云霞吧,看這彩山在四季變換中如何涂抹自己;讓我做山腳下的一塊石子吧,饑吞雪渴飲露,天地為衾被,萬象為賓客。或者,就讓我裁一片這七彩丹霞,做一件長長的舞衣吧,跳哪支舞?當然應該是《波羅門佛曲》,最原始的,而不是那段傳入宮廷后被改制的《霓裳羽衣舞曲》。那里面,填雜了過多的東西,太沉重、太喧攘,不適合我,也不適合這一片土地。
雅
甘州,這一把“塞上鎖鑰”,她是金色的,開啟了古絲綢之路的鎖頭;她又是綠色的橄欖枝,打開了中原通往西亞東歐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關隘。
五千年前,一群黑水國人,已不是茹毛飲血的原始人,他們在這里種桑、織麻、放馬,用石紡輪制作衣服。燒出彩色的陶器,在陶器上畫上自己喜歡的人;提水時她伴我去,洗臉時我撫弄她的發絲。你是我的黑陶罐,我是你的黃泥巴;你是我籬笆墻上盛開的扁豆花,我是你葡萄架下無香的一杯清茶。我們死去,樸拙皮實的陶器會替我們活下去。
一千八百年前,沮渠蒙遜在張掖建立北涼國。張掖依著黑河水,種著烏江米,享受著來自西域的恭維,彈著《秦漢伎》,譜著《西涼州唄》,在石窟里鑿出衣著時尚的外籍美女。我愛的那個人兒,她不正是菩薩的樣子么?春意闌珊,手起鑿落,菩薩笑著笑著,就從虛無縹緲中回到了煙火的人間,落在了潔凈的塵埃里。秋雨潺潺,佛心中有眾生,我心中有佛。
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隋大業五年,煬帝——中國歷史上唯一西巡的封建王朝皇帝,集美學家、詩人和散文家于一身的“不很高明的政治家”,在張掖會見了西域二十七個國家的國君王和使臣,打通了絲綢之路第三道,召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萬國博覽會”。
盛唐,一個讓無數文人騷客無比向往的年代——玄奘去印度取經,途徑張掖;裴矩編纂繪制了《西域圖記》三卷;陳子昂寫下了《上諫武后疏》;李白寫下了《幽州胡馬客歌》;王維寫下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波羅門佛曲》、《甘州破》、《甘州子》、《八聲甘州》、《甘州曲》直達天庭,響徹云霄,誦唱至今。那些坐在豪華宮殿里看舞聽曲的人,云屏香暖、翠銷酒酣,他們是否在揣度,風沙彌漫、荒涼偏僻的河西,靠狩獵、游牧的民族,是有怎樣的魅力吸引了這些文人大家來此駐足、吟唱?這一片神奇的土地,又如何能創造出這樣燦若繁星的煌煌巨著?
北宋時期,李元昊修建了大佛寺。西夏文化與當地文化無縫銜接,建成了塞上名剎,佛國勝境,成就了歷史文化名城坐標。
元時期,馬可·波羅、這個高鼻深目的意大利美男,被大佛寺的塑像精美宏偉建筑和張掖的繁華所嘆引,留居一年之久。
康熙六年,江南戲劇理論家李漁偕同家庭社戲班來甘州,上演了昆劇。之后,甘州詩人馬羲瑞的著名昆腔劇本《天山雪傳奇》問世。四十二出的《天山雪》,比孔尚仁的《桃花扇》早問世七年。甘州人,怎么能不自豪?
今天的甘泉書院、市區圖書館,有古籍善本《通志堂經解》、有《永樂大典》遺珍、有《四庫全書》,也有《甘泉》《焉支山》《黑河水》《棗林》和《牧笛》。
每一個朝代,張掖都在絲綢古道上留下了足印、韻味和味道。那是文化的步履,那是文字的芬馥。這書香墨香,飄蕩了五千年,經由祁連山,經由黑河水,經由絲綢路,飄到了全中國,飄到了全世界。
頌
從我的故鄉華銳雪域高原出發,去往甘州城金張掖,需要騎一匹快馬,黑色的高頭大馬。需穿上厚重的大氅,身負寶劍,長發高束,在清冷的戈壁灘獨自打馬。穿過銀武威涼州城,穿過戈壁石,穿過明長城,穿過蒼茫而空曠的歷史烽燧。
涼州冷,華銳高原更冷。烏鞘嶺翻飛的雪片穿峽而來,奠定了這一場出行清冷孤寒的基調。那么,甘州,是否甘之如飴呢?
四十年前,我二叔只有十六歲。他因肚子餓而扒上了一輛西去的火車,在山丹軍馬場當了一名工人。山丹軍馬場三場一連——這個通訊地址我從小就會背,因為我們隔個半年三月的,會收到來自那里的書信。
二十年前,我小姑一家四口,拉著我給的一臺舊電視機、一個高低柜和幾雙布鞋搬遷到了臨澤縣五泉公社。還有一千元貸款,那是他們全部的財產。
回首更疑天路近,恍然身在白云中。我的家人,從烏鞘嶺出發,走上了那條神奇而蒼涼的千年官道。朔風陣陣,飛雪數點。等待他們的會是什么?“往西走,往西走。西邊有果子吃。”這是哄娃娃的話,也是在勉勵大人走出窮窩窩。
張掖,以她固有的包容性和全民性,接納了我的家人。山丹、臨澤,以她的熱情好客、忠厚淳樸讓親人們在這里生養將息,繁衍子孫。
二○一六年國慶節,我們驅車去往小姑在臨澤的家里。一進入張掖境內,就能深刻地感知到其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物產豐饒,既有西北常見的雪山、草原、碧水、沙漠組成的荒漠綠洲景象,又有我們高原氣候下不會生長的瓜果蔬菜、林木稻谷,還有多民族聚居的濃厚文化氛圍。既有南國風韻,又有塞上風情,相映成趣,別具一格。
年長我三歲的小姑姑,松開了緊鎖的眉頭,白凈的臉上綻開少女的笑容。她不再為一包洗衣粉而苦惱,也不會為一件新衣服而落淚。她的孩子們說著當地的方言,哼唱著《河西寶卷》,歷數著張掖境內名勝古跡和歷史文物,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從住窩棚到七間嶄新的封閉式新房,從架子車到如今的小汽車;隨手就可采摘的枸杞、小棗;地里長著的玉米、甜葉,樹上結著有蘋果梨,沙棗。姑父說,這個地方不哄人,搬來第一年,我的娃娃就吃到了不要錢的果子!從那時起,我就不打算離開這里了。
感恩這片熱土,給他們的赤手空拳以厚實的黑土地;謝忱這片膏壤,給他們的一無所有以尊嚴,讓他們能夠繼續以一個農民應有的姿態,接近山川草木,觸摸甘甜大地,回報深情故土!
責任編輯 郭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