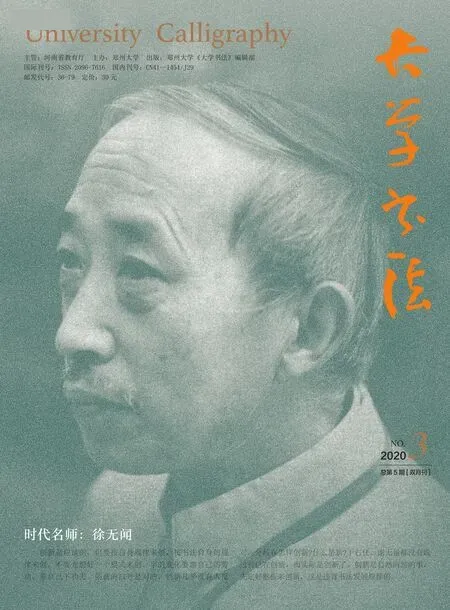當下書法學學科建設面臨的四大困境
⊙ 張榮國
一、“書法學”知識體系尚未構建完備
在《關于當代中國書學研究的現狀、問題和愿景》一文中,陳振濂把“當代中國書學研究”歸納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書學“學習時代”、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的書學“學術時代”以及新時代的書學“學科時代”三個階段。“在‘學術時代’我們將書學研究的重點,從資料對象逐漸轉換為研究方法,注重書學整體架構的搭建和分支的衍生,我們希望看到對材料演繹生發角度的不同,進而達到研究角度的多元化。”[1]但到了“‘學科時代’,意味著今后我們的書學研究者不會再有細致的領域固化和分類專攻自劃疆界,而是通過掌握書學理論的各種研究方法、思辨模式,來構建書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形成學術群聚的現象,開啟‘學派時代’”。[2]
陳振濂的這一“愿景”充分說明了書法的“學科時代”還沒有真正到來,盡管包括他在內的一批書法家、研究者不遺余力地著書立說并積極推進。[3]事實上,直到現在書學仍然艱難地走在“學術時代”,即開始有了框架、核心主題和分支研究,比如“書法學”旗下的“書法史學”“書法美學”“書法技法”“書法創作心理學”“書法社會學”“書法形態學”等。而各種獨立的學術分支交互發展,形成獨特的“書法學”學科體系的“學科時代”卻依然任務艱巨,路途漫漫。
劉宗超認為“書法學”學科建設至少包括20個分支,即書法史學、書法哲學(書法藝術原理)、書法美學、書法評論、書法比較學、書法分類學、民間書法學、書法文獻學、書法教育學、書法管理學、書法心理學、書法倫理學、書法文化學、書法社會學、宗教書法學、書法考古學、書法經濟學、書法市場學、書法傳播學、書法環境學等。“‘書法學’要想在國家‘藝術學’學科體系中占有一定地位,以上20個分支學科都要有一批研究力量,有合理的人員構成和學術成果才行,而目前的學科建設依然任重道遠。”[4]無疑,這是一個工程浩大而學科體系相對完備的“希望工程”,暫且不談以上20個分支的建設與完備,姑且套用一級學科文藝學(文學)一般認為的“三個組成部分: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5]為“書法理論、書法史、書法批評”,書學研究最為凸顯而有成就的學科也就僅有“書法史”,“理論與史論仍然差距懸殊”[6],“尤其是書法批評依然是書學發展的軟肋”[7]這一趨勢在《全國第十一屆書學討論會論文分類統計》(見表1)[8]中可窺一斑。
以上“書法學”學科的整體失衡狀態,充分說明“缺乏學科體制支撐與引導,并對其抱有學科偏見”[9],“書學研究的‘學科’意識不強,學科隊伍建設不均衡,缺乏有效的全國性的學科規劃”[10]。

表1:全國第十一屆書學討論會論文分類統計
二、“書法學”學科建設人才匱乏
在“書法學”學科建設中,人才是關鍵。目前成就最為突出的是書法史,而此成就的取得卻多依靠于文、史、哲背景出身的書法家,比如叢文俊、黃惇、朱關田、曹寶麟、邱振中、華人德、陳振濂、侯開嘉、朱以撒、周俊杰、李一、劉恒等,他們主要分布在中國知名高等院校、美院,從事書法本科、碩士、博士的教學與書法研究工作,“隨著這些學人的漸次退休、年高,今后的學術研究不乏令人擔憂之處”。[11]他們雖然培養了一批書法研究者,但到目前為止還難以成為“書法學”學科建設的主力軍。毫無疑問,現在書法學科建設的重任落在了一批中年甚至青年學者身上,20世紀60年代左右出生的書法創作者、組織者、教學工作者雖不乏文、史、哲背景出身,但其國學素養似乎難與老一代抗衡;“70后”很多為書法或繪畫科班出身,其文化底蘊堪憂。毋庸置疑,這批中青年現多在重要學術機構、高等院校等扮演著研究者、師者身份,不僅是“書法學”學科建設的實踐者,還是重要的引導者,甚至是青年學子的人生榜樣和精神導師,對書壇的健康發展起著重要的引領作用。因此,如何使他們進一步自我完善并成為學科建設的生力軍,扭轉當下學科意識淡薄、綜合素質不強和專業能力不精等局面,是擺在當下的重要任務。
“書法學”學科建設人才匱乏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書法學”各分支學科人才嚴重不均衡。就“書法學”學科體系的構建而言,現有的書法理論家、書法批評家、書法教育家等均屈指可數,即便是書法史家,真正被學界高度認可的卓越者也寥若晨星。二是現有的重要書法研究者的知識缺陷造成了自身“供血”不足,從而對學科建設的健康推進難以提供高效的“動力源”。換言之,他們對“書法學”學科建設的實質性貢獻率并不能令人滿意。美院、高等院校的本科任課教師和碩、博研究生導師目前主要存在以下情況:一是史論勝于實踐者,他們多是美術史論、文獻學、文字學、美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但疏于書法史論的精研和實踐探索,因缺乏該領域的深厚學養而導致認知短板,其研究結果難免有失客觀公正,有隔靴搔癢之弊;二是書法實踐與史論嚴重脫節者,他們多沉溺于書法創作的自娛體驗,而缺乏學理上的升華,在教學上強調“技”的表達而疏于“道”的傳授,對后備人才的有效培養大打折扣,在限制自身成長的同時也制約了對“書法學”學科的建設;三是理論與實踐并重者,這類人才多是經過了嚴格的博士階段的學術與創作的雙重訓練,既有扎實的實踐能力又有較厚的學術修養,能文能武。目前這類人才雖未真正達到技道雙修,但潛力巨大,后勁勃發,正成為“書法學”學科建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需要長時間的能量積蓄。
應該說,學術與創作不能互相生發、不能同頻共振是導致“書法學”學科建設人才匱乏的重要原因之一。“當前學術研究文章難做,也難懂,搞書法創作的看不懂,不愿看。除展覽現場的吹吹捧捧之外,理論研討會很少有國展創作者參加,似乎成為見怪不怪的現象。這暴露出了技術型人才與理論型人才含而不露但又相當深刻的沖突與矛盾:一種傾向是忽視感性的空洞材料積累或理性思辨;另一種傾向是忽視藝術研究的理性,片面強調藝術感性,這些現象在當下都有所表現……一些書法論文不關書法本體,不關書法發展,不關書法創作,讓人感覺到不搞書法的也能寫那類論文。這樣就慢慢把理論孤立起來了,劃了小圈子,丟了書法本身和廣大受眾(人民)。”[12]這種現象在當下很普遍。譬如,眾多書者對“二王”書風過于膜拜而忽略了書法資源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往往打著“承古出新”的旗幟游弋在“雷池”之中,更遑論在文化史、書法史等宏觀視野下,在歷史坐標的定位中進行創新性探索了,結果導致了“二王書風遍天下”的奇觀。基于這種“漸變式”思維模式的書者,當面對“跨越式”“變異式”的書法創作時,卻因其超越了自身的審美認知而被漠視或嗤之以鼻。“沃興華”們的書法作品被普遍視為“丑書”便是例證。同樣令人遺憾的是,不少書法研究者就猶若只樂此不疲于食材施肥、運輸等舍本求末環節的“大廚”,卻置若罔聞于食材的屬性、烹飪技術等本體探究。
概而言之,目前書法界整體似乎是一片繁榮景象,從事書法實踐和研究者也不乏其才,但從學科建設角度來看,真正能扛鼎者卻又屈指可數。這既是當下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同樣也折射出中國書法人才培養體系的缺陷。
三、書法人才培養體系缺乏合理性
倪文東等研究者在《當代中國高等書法教育現狀的調研與思考》中指出了書法教育的現狀:“發展迅速、特點鮮明、辦學層次多、教學方法活。但存在的問題也比較多,主要是學科不明確、專業基礎薄弱、缺乏統一規范、招生與就業脫節、師資力量不平衡、教學和培養機制不完善等。”[13]
書法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經形成了由專科、本科、碩士、博士乃至博士后構成的教育體系,培養了一批書法專門人才,為書法學科的建設提供了智力支持。但就目前的人才培養體系而言,依然缺乏合理性。金丹在《折射當代書學研究的現狀》中指出,十一屆書學討論會的1000多篇投稿,“可以說這是全國書學研究目前一個總體水平的反映,作者中書法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人群占據了主要比例,這是近年來書法研究生大規模招生的顯露,也是書學研究越來越走向專業化的一種表現,這也可能是將來研究的一種趨勢。投稿論文內容涉及史學、理論、技法與教育。史學研究的水平近年呈上升趨勢,理論研究的論文也漸有起色,而技法與教育類論文在其中顯得最弱,富于創建者較少,大多停留在簡單的敘述層面,不能盡如人意”。[14]由此折射出人才培養的弊端:其一,專而不博、專而不精,導致所培養的研究者不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難免導致以偏概全甚至指鹿為馬;其二,感性與理性不統一、理論與實踐不統一,導致重技而輕理,重術而輕道,這正是如上所言的“技法、教育類論文大多停留在簡單的敘述層面”之根由。
導致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課程設置的不均衡。當下書法專業更多關注書法實踐和書法史,甚至書法美學、書法理論、書法批評等重要課程也沒有真正落到實處,淺嘗輒止,就更不要奢談文字學、美學、哲學等相關課程了。據悉,很多書法專業碩士、社會工作者和教師多熱衷于技法訓練和參賽,真正靜下心來吃透書法史和書法理論者寥寥無幾,有的甚至不能寫出一篇像樣的學術性文章。二是實踐類書法專業培養過分強調“肌肉訓練”,對專業理論和文化素養重視程度不夠。這一結果與國家或省市的專業碩士培養方案的導向密切相關。例如,學位論文由于強調創作體會,導致不少同學“自說自話”,論文缺少基本的思辨性、邏輯性和學理性。三是不同院校培養目標的趨同性。現有的專業藝術院校、師范類和綜合型大學開設的書法專業尚未真正因地制宜,制定自己特色鮮明的培養目標。雖然說“這三類院校各有特色,而專業設置方面也不盡相同,特別是針對碩士及其以上學位教育各大院校專業設置及培養方向側重各有不同。綜合類院校書法教育……旨在培養綜合型書法人才;師范類書法教育……主要培養能夠進行書法教育、理論研究的專門型人才;藝術類院校書法教育……培養優秀的書法藝術人才”。[15]但實際在具體的培養過程中,不少綜合型和師范類大學不同程度地仿制專業美院書法專業的課程設置,試圖把培養書法專業人才作為培養目標,例如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見表2)。四是國家對專業的設置缺少統籌規劃。“書法學”學科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如何讓其全面健康地發展,如何合理有效地布局,國家在尊重學校自主辦學的過程中也要有所作為,進行通盤考慮,提出指導性意見。比如師范類書法專業就要加強書法教育學科的建設,既注重人才的創作實踐培養,又要注重理論修為,更要注重教學能力的培養和書法教育學、書法心理學、書法教材教法等課程的研究與開發,培養真正能夠擔負起“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而非以培養專業的書法家為旨歸。當然我們十分歡迎受教育人員能達到書法家的專業水準,然而,現存問題是:本科、碩士、博士的課程設置沒有科學性和系統性,無法做到有效銜接,“因此設課必須服從高等教育中學科建設的需要,不能因人設課,會什么上什么,以免造成長期的教學缺憾”。[16]

表2: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書法篆刻方向”專業課程設置
四、“書法學”學科建設的生態環境急需修復與完善
當今社會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方式、社會結構、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中國保守的農業社會使文化傳承輕而易舉,那時外來文化的侵略因傳媒的有限而顯得力不從心,而今的強勢文化侵略愈演愈烈,科技時代使人接受各種新潮文化不費吹灰之力。誠然,今天中國人受教育的面廣了、學歷高了,但精通傳統文化者卻越來越少。作為日常生活書寫常態的書法生存環境已經一去不復返,書法文化生態遭到嚴重破壞。這是其一。
其二,書法人才培養追求短時性與功利性。從生源而言,當下書法后備軍的文化基礎極其薄弱,從藝似乎只是升學的一條捷徑,而非興趣使然,更別說作為終生追求的事業了,這與前人的心態和動機已有天壤之別。就培養目標而言,也過分功利化和實用化,以就業率為目的,以參賽獲獎為指標,追求短期利益,忙于辦展與交易,急功而近利,心浮而氣躁。當然,這也是文化生態遭受破壞的惡果。因為中國文化傳承的豐厚土壤正逐漸變得貧瘠。以前藝術家創作藝術品雖不同程度地參與藝術市場,卻以自娛為主,況且那時的藝術市場是比較稚嫩的,而今卻是藝術商品化時期。以前從事“精英文化藝術”者雖沾染商品習氣,但大都是學養深厚的飽學之士,對藝術的追求依舊是他們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乃至全部。就書法傳媒而言,追名逐利者多多,或虛假宣傳,或索取高額費用,失去了媒體應有的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這不僅為書法研究者帶來了巨大經濟和精神壓力,導致不少研究者放棄了學術研究,而且助長了不正之風。
其三,缺少公平合理的評價和制約機制。在人事或職稱考核中,由于對研究者、從業者進行指標量化,比如要在核心、權威期刊發表多少學術論文或參加多少“國展”,等等,導致了重短效而輕縱深性可持續發展的“惡果”。為達目的往往不擇手段,在這種生態下,書法界出現了各占山頭、分疆劃域甚至相互打壓的各路“英雄好漢”。寬松、平等、和諧的批評環境也似乎成了奢求,研究者為在業界生存,多唱贊歌而少批評,甚至一味鼓吹。目前,尚未有書法批評茁壯成長的良田沃土和陽光雨露,其累累碩果的采摘還時機未到。
無疑,“書法學”學科建設必須有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才能得以健康持續發展,任重而道遠。
注釋:
[1][2]陳振濂.關于當代中國書學研究的現狀、問題和愿景[J].中國書法,2018(2):143.
[3]陳振濂.書法學[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
[4][8][10][11]劉宗超.全國書學研究狀態的集中展示——全國第十一屆書學討論會評審綜述[J].中國書法,2018(2):147.
[5]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簡明版)[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5080-5081.
[6]葉鵬飛.當代書學研究隊伍重新檢閱——全國第十一屆書學討論會評委筆談:理論與史論仍差距懸殊[J].中國書法,2018(2):151.
[7]王偉林.當代書學研究隊伍重新檢閱——全國第十一屆書學討論會評委筆談:讓書法批評熱起來[J].中國書法,2018(2):153.
[9]姜壽田.當代書學研究隊伍重新檢閱——全國第十一屆書學討論會評委筆談:倡導書學研究的多元化[J].中國書法,2018(2):153.
[12]劉宗超.全國書學研究狀態的集中展示——全國第十一屆書學討論會評審綜述[J].中國書法,2018(2):148.
[13]倪文東,陳思,高文興,楊杰,李偉.當代中國高等書法教育現狀的調研與思考[J].中國書法,2016(2):4.
[14]金丹.折射當代書學研究的現狀[J].中國書法,2018(2):156.
[15]劉川,李冰林.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中國高等書法教育現狀[J].中國書法,2016(12):38.
[16]叢文俊.書法研究與學科建設[J].中國書畫,2005(9):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