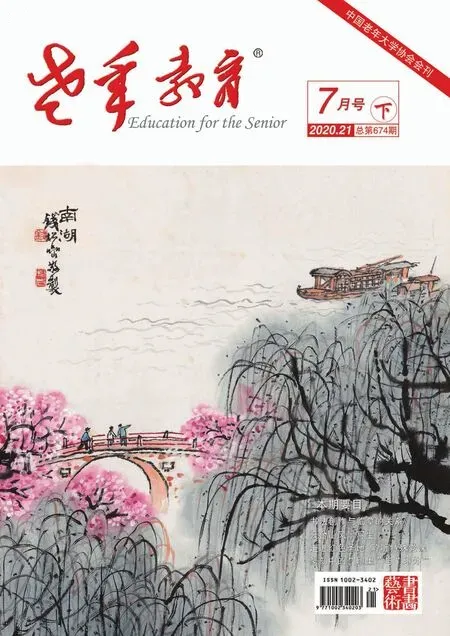篆刻中的“印里”與“印外”
□韓天衡

《百歲進軍》 王個簃
畫畫有寫生之方式,書法、篆刻是無法寫生的。學習篆刻這門藝術,除了臨摹學習,幾乎再無第二條途徑。有些大藝術家,也是在有相當深厚的積累和感悟之后才具備了“屋漏痕”“折釵股”“萬物皆入書、入印”的超跨度的變通能力。對初學者而言,只能“印內求印”,印宗秦漢、隋、唐、明清流派印,在基礎期必須經過這些學習訓練。
浙派創始人丁敬認為,周、秦、兩漢、魏晉、隋、唐、元、明、清,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特色,并把這些時期的印學了個遍。至鄧石如開始有了“印外求印”的觀念,以篆書入印。他的印是有起、落筆的,借鑒了碑刻書法的特點。趙之謙所處的時代,出土了很多前人未見過的既古又新的文字。趙是非常敏銳而且擅化的人,善于將新出土的材料直接引入刻印,所以五百多年的明清篆刻史,像趙之謙這樣的“百變金剛”僅此一個。
一個真正的篆刻家,絕對有自己的一套獨創的新理念,不見著述、不講出來不代表他沒有,這是我們研究篆刻的人必須要敏銳感覺并注意的。之后的吳昌碩,從出土的封泥之中體會到了瓦甓之美、斑駁之妙。封泥印不是平面的,而是有起伏的,富有輕重節奏感,線條亦不是光溜平滑的,而是有浮雕般的質感。吳昌碩領悟到了這點,他高明的做印技巧是前無古人的。古人制印,是將刻好的印放在一個小盒子里面,吩咐書童搖晃,以此達到做舊目的。而吳昌碩是理性的,帶著很高的藝術內涵去制印,其印在平面紙上鈐蓋出來即具有浮雕般的質感。

《看盡江湖萬千峰》 韓天衡
印里與印外是一個辯證關系。學印者首先要在“印里”好好學習,日后再到“印外”好好參悟。路不是已經被前人走完了,而是要靠自己去開拓。我年輕時是一個喜歡胡思亂想的人,19歲那年當海軍到溫州,從船夫搖櫓過程中發現自在入水淺,遂得篆刻中深入不如淺刻。此外,真正優質的長線條是由若干曲線組成的,比如用圓規畫出的圓是缺乏趣味的,這與書法中的提按起伏同理。好的篆刻家要有很強的變通能力,需努力去發揮藝術的想象力。
篆刻中有疏密的關系。我在20世紀80年代喜歡看古巴女排和中國女排比賽,女排比賽兩強相遇,根據球路,則有站位換位和大密大疏且出人意外節奏的變化,這不僅是看球,而是去關注全場瞬間千變的章法布局,我認為對刻印的布局大有裨益。
古人講“計白當黑”“積點成線”。雖然這些話經典,但我們更應該從生活中去真正感悟活生生的、有滋有味的章法布局和線條揮運。比如拔河,繩子放在地上并不見力量。但拔河時兩隊都拉著這繩子,此時繩子一會朝左、一會朝右,這富有張力和阻力、有生命活力的繩子,就等同于篆刻里最優質的線條。
所以,學印者更應該從潛移默化的生活中去感悟、去發現。在具有一定基礎之后,這些便能演化成藝術中非常重要的自我而獨到的東西。

《可貴者膽》 韓天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