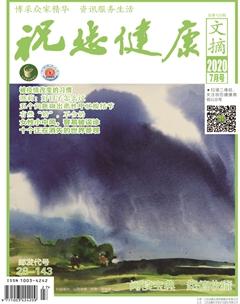進城抹澡
聶學劍
家鄉土話把洗澡叫“抹(mā)澡”。現在琢磨起來,它是那么準確傳神,一個“抹”字形象地表達了“清潔”的意思。時隔30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記得第一次進城抹澡的情景。
小學三年級寒假通知書發下來,語數雙百。望著父親喜笑顏開的臉,我趕緊提醒他:“不是說要帶我進城抹澡嗎?”父親當即決定,第二天就兌現承諾!
那天晚上,我激動得半宿沒有睡踏實。剛剛進入夢鄉,就被父親輕輕地搖醒。窗外還是漆黑一團,可父親說,雞叫三遍了,再不趕路,澡堂子里的熱水就被糟蹋壞了。我趕緊爬出被窩。父親拉著架子車,沿著柏油馬路的路肩一陣“急行軍”。趕到位于縣城中心十字路口的東風浴池時,居然已是車水馬龍。鄉下趕來洗澡準備過年的人們,早已把自行車、架子車挨挨擠擠地擺放得無處立足。勉強找個空檔存好架子車,花五分錢換個油光可鑒的竹牌兒攥在手心里,我就拽著父親的衣襟走進浴池。
推開一間寬闊的門臉,一股溫暖的氣流襲來。賣票的阿姨例行公事地提醒我們,男池在樓上。我興奮得心里怦怦跳,心想:城里人就是厲害,居然能把一池熱水引到樓上去。掀開厚厚的門簾,收票的伯伯引導我們找個空床鋪脫衣服。還好來得早,要不然就沒地方了。父親和我都脫得赤條條的,從一字排開的鐵絲上扯了兩條統一制式的毛巾,就淌進霧氣騰騰的浴池里,渾身的寒氣頓時散去,真舒服啊。
半個鐘頭過去了。我渾身上下被父親抹得干干凈凈。父親先幫我穿上備好的干凈衣服,然后自己再穿。我自告奮勇地幫他收拾換掉的臟衣服,順便把帶來的香皂、梳子之類的東西也一并裝進包里。
當我們走出浴池,上交竹牌,拉出自家的架子車走到半華里外的一家早餐鋪時,父親把包重新整理了一下。“咦,你怎么把人家浴池的毛巾也裝進來了?”那毛巾的尾部分明印著“東風浴池”的字樣,父親詫異地望著我,一臉不解。我紅著臉不說話。我記得收拾衣服時,曾自作聰明地把那條濕漉漉的毛巾一并裝了。當時我僥幸地想,花錢買了澡票,毛巾應該能帶走的吧。
父親一下子火了:“你是存心偷拿人家的吧!”我驚恐萬分,只想找個地縫鉆進去。父親的怒氣很快引來路人觀望,當時的我不敢抬頭,覺得仿佛整條街的人都圍過來了。我扯過那條毛巾,不由分說地折返回去,向著浴池的方向狂奔。當我如釋重負地一級級走下浴池樓梯時,一眼瞥見父親也折回來了,他就在賣票的過道里等著我。父親牽住我的手,他的手是那么粗糙,卻那么溫暖,疼惜和贊許的目光充滿慈愛。
至今我仍然說不清,當時是有意還是無意地企圖將那條毛巾據為己有。可那個冬天的清晨,我一身輕爽,心里格外豁亮,覺得整個世界都那么光明。因為第一次進城抹澡,父親用一條毛巾把我的身心都擦拭得干干凈凈。后來我考到省城讀書,從此一直生活在城市,保持著每天洗澡的好習慣。每次站在鏡子前,握著柔軟的毛巾揩拭身上的水珠時,總會想起第一次抹澡的情景,那條迅即被歸還的毛巾成了我最心驚、也最溫馨的記憶。把每一寸肌膚都擦拭得干干凈凈——這是我對抹澡最深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