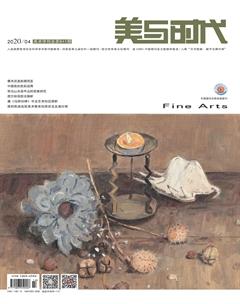飲真茹強蓄素守中
王國棟
摘 要:“墨分五色”是中國傳統繪畫理論的重要概念。文章通過對“墨分五色”追根溯源,探究其植根于中國哲學文化的厚重內蘊,并簡概爬梳其理論流變,以此為基點敘述中國畫的獨特審美趣味與思維認識方式。基于中國文化強大的包容性,不但“墨分五色”的中國水墨畫具有可持續性的向內發展能力和向外拓展空間,煥爛求備的中國工筆畫和彩墨畫,在植根傳統的基礎上也具有對異域藝術強大的吸納能力。故,中國畫的“水墨”和“色彩”兩大支脈不是要“一枝獨秀”,而是要“雙葩競春”。“飲真茹強,蓄素守中”,這體現的正是中國哲學文化的高妙之處。
關鍵詞:墨分五色;中國畫;哲學體系
“墨分五色”屬于墨法范疇,語出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之《論畫體工用拓寫》一篇:“夫陰陽陶蒸,萬象錯布,玄化亡言,神工獨運。草木敷榮,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飄飏,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綷。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此段闡述大意為:天地陰陽沖蕩變化,則萬物錯雜分布,自然造化,鬼斧神工得之。傳統繪畫重在得物象之意,而墨色深淺之變可兼青、赤、黃、白、黑五色,足可表現繽紛之世界,無須勞“色”徒言其表,故重在得意也。倘計較于物之皮相,則物象之意失之。
文士哲人對于“五色”的解釋說法不一,古人之理解大致分兩義:宋代以前多指濃淡不同的墨所對應的五色,即“青、赤、黃、白、黑”;宋代以后,則指墨調水后濃淡深淺的變化,即焦、濃、重、淡、清。另也有“濃、淡、干、濕、黑”(加白合稱“六彩”)之說。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所言“運墨而五色具”,指通過墨色之變足可表現四時和物象之異。繪青山綠草、紅花白雪等對象不必借助空青、丹碌、鉛粉之色,觀者同樣可感受到色彩斑斕的世界。古人曾運用墨色的深淺以對應五色:焦如黑,濃如青,重如赤,淡如黃,清如白。實際上這是將色的明度與墨的明度做一個對接。古代科舉考試曾用淡墨題寫中榜人的姓名,被稱為“黃榜”,這似乎也暗合了“淡如黃”的對應關系。
“墨分五色”的概念生成,與中國傳統宇宙觀的“五行”思想相關。“五行說”將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與白、青、黑、赤、黃的五色對應關聯。五行是萬物產生的本源元素。五色是各種色彩的本源之色,是一切色彩的基本元素。“五行”除了“五色”對應,又衍生出“五行配伍”這一涵蓋天地萬物的陰陽五行體系,如五行配五季(春、夏、長夏、秋、冬),五行配五方(東、南、西、北、中),五行配五臟(脾、肺、腎、肝、心),五行配五聲(宮、商、角、徵、羽)等。
清人沈宗騫《芥舟學畫編》有論曰:“五色原于五行,謂之正色,而五行相錯雜以成者謂之間色,皆天地自然之文章。”據《考工記》載:“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彩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后素功。”另,五色、五方與五季也有錯綜復雜的關系:東方謂之青(青龍),為木主春;南方謂之赤(朱雀),為火主夏;西方謂之白(白虎),為金主秋;北方謂之黑(玄武),為水主冬;中央謂之黃(黃龍),為土主長夏。這些概念是五色與自然物象的一種聯系與概括,與中國早期的哲學體系、宇宙意識有關,與道家文化推崇的自然觀相契合。《易經》中有“一陰一陽謂之道”的宇宙觀,莊子有“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之論。中國的道家思想講陰陽,老子“道法自然”的命題構建了一個以“道”為中心的哲學體系。莊子認為,“道”是宇宙運行的至高法則,所謂“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這些觀點和概念對中國的藝術創作理念與審美認知影響深遠。
佛教傳入中土后,成為中國傳統書畫藝術創作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被奉為南宗之祖的王維,深諳佛理,以禪趣入詩、入畫,并首次提出“水墨為上”的藝術主張,引領了文人寫意畫的新風尚。千百年來,水墨畫也發展為中國繪畫史上與丹青雙峰并峙的另一大宗派,至今仍有廣泛和深刻影響。老子有“知其白,守其黑”之言,國畫有“計白當黑”之論。王維《山水訣》言:“夫畫道之中,水墨為上。”他認為水墨最宜“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而非丹青粉黛。由此可知,中國繪畫早有“重墨輕色”之文化理論基礎。
中國文化尚意,尤其是宋以后的山水畫創作,亦有不少體現出文人畫家玄遠幽渺的佛禪意趣。自北宋蘇軾倡導“文人畫”始,“水墨渲淡”風貌延續至今,尚自然、尚意的繪畫被尊為上品、逸品、神品,一時被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水墨可以表現宇宙的大化生機,反映中國畫家追求生命內蘊的精神,也更為契合文人畫家空靈淡遠的審美旨趣。直至近現代對筆墨拓展大有貢獻的黃賓虹提出的“五筆七墨”概念,即平、留、圓、重、變之筆法,濃、淡、潑、破、積、焦、宿之墨法,也直接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與沾溉。
對于“墨分五色”的重視和闡釋,歷代畫論畫理多有記載。如清代吳歷在《墨井畫跋》中認為書畫要“渾然天成,五墨齊備”。清唐岱《繪事發微·墨法》曰:“墨色之中,分為六彩。何為六彩?黑、白、干、濕、濃、淡是也。六者缺一,山之氣韻不全矣。”清華琳在《南宗抉秘》載:“墨有五色,黑、濃、濕、干、淡,五者缺一不可。五者備則紙上光怪陸離,斑斕奪目,較之著色畫尤為奇恣。得此五墨之法,畫之能事盡矣。”此外,《周易》中論“賁”也進一步佐證了“重墨輕色”的思想。系辭曰:“上九,白賁,無咎。”“賁,飾也”(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意為文章貌,華美光彩貌。“白賁”則指裝飾樸素無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而《易經·雜卦》中“賁,無色也”更是直接體現出對自然、素樸審美趨向的認同,并催生了孔子“繪事后素”的哲思闡發,也無意引導了由一統天下“色線同體”的重彩人物、重彩花鳥、青綠山水繪畫,分流出愈來愈多尚雅重意、“墨分五色”的水墨畫。劉熙載在《藝概》中言:“‘白賁占于《賁》之上爻,乃知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古人對“白賁”境界的崇尚,傳達出“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的理念,乃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思想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