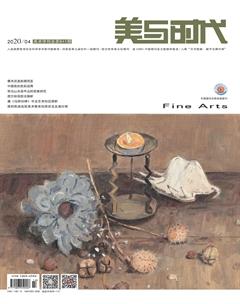元代畫家中倪瓚“簡”與王蒙“繁”之比較
曹蘭婷
摘 要:“元四家”作為元代畫壇的重要代表,曾在山水畫史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與影響,也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元人山水畫對中國古代山水畫發展發揮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元四家”的山水畫藝術風格各異,主要是他們藝術探索和審美觀念造成的,這也是值得關注與玩味的話題。例如,在“元四家”中,倪瓚的蕭散簡遠與王蒙的繁密厚重形成畫風上的鮮明對比。倪瓚作品所刻畫的是“疏而不簡”“簡而不漏”的疏體山水;王蒙則描繪出的是“蒼茫渾厚”“秀潤靜謐”的密體山水。二人“一簡一繁”的繪畫藝術效果與他們的創作技法、內心世界、審美追求和人生閱歷等密切相關,值得深度探討。
關鍵詞:倪瓚;王蒙;疏體;密體;山水畫;元代;藝術風格
元代山水畫是古代中國抒情寫意山水畫的高峰,也是中國山水繪畫史上又一個燦爛時期。由于元代社會的特殊性,元代繪畫呈現出特殊的面貌,孕育出承前啟后又風格鮮明的藝術風貌。在這一時期,山水畫的創作主體主要是江南的文士階層,并涌現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大家。元代山水畫中,影響較大和被后世尊崇的主要是趙孟頫和“元四家”。正如蔣勛先生所言:“元朝四大家,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截然相反的對比,他們或發展繁復,或發展精簡,他們敦厚或峭薄,孤高或平易,從容或激情,各自把性格發展到了極致,成為藝術的風格。”由此可見,“元四家”畫風形成的原因還是與畫家所處社會環境、生活閱歷、師法傳承等方面的因素緊密相聯,這也是分析他們畫風異同的突破口。而本文所關注的兩位畫家也是這樣,倪瓚的疏簡風格,主要是由其精神狀態與內心修養所決定,同時,也受到他個人高度潔癖的性格影響。王蒙的繁密風格,與他顯赫的家學淵源、縝密細膩的心思、積極入世的情懷密切相關。他們都身處于亂世之中(元末社會動蕩、地方政權不定),但二人在亂世之中所持的生活態度和藝術追求也明顯不同。本文從兩位畫家的個性特征、繪畫創作技法、繪畫審美觀念等方面,嘗試比較二人藝術風格之異處。
一、圖式的構成比較
倪瓚與王蒙二人雖生活在同一時期,但他們常年所處的社會地位與生活環境還是不同的,這就導致了他們筆下山水面貌與表現形式的差異。就創作內容而言,倪瓚的作品大多描繪的是太湖和松江附近的江南水鄉,多為三段式構圖(一河兩岸,一兩個小土坡,三五株枯樹)。倪瓚尤善于留白,因此品賞其畫,首先需要體識他畫面上的空白部分(有時空白部分可占畫面的二分之一),這是倪瓚的特色,也是他在山水畫史上的貢獻。這種畫面表現方式的基本特點是:空,卻有靈氣往來;簡,又含有秀潤之姿。他的山水畫具有空靈、清凈、古雅之美,這在他的《漁莊秋霽圖》和《六君子圖》等作品中足以領略。正如正如著名美術史論家陳傳席先生所言:“總之,倪云林的畫以簡勝,表現出一種極其清幽、潔凈、靜謐和恬淡的美,給人一種凄苦、悲涼、索寞的感覺。在倪云林之前,山水畫能表現出這樣一種美的境界者是沒有的。”
相比較而言,王蒙的作品就大有不同了,他的作品中多刻畫江南溪山林木之景色。畫面中描繪高聳山峰、草木豐茂,給人一種生命力旺盛與樸茂之感。較云林最大的獨特之處,是王蒙畫得密、畫得滿。這在他的作品《青卞隱居圖》中能展現出來,該畫全局幾乎極少空白之處,但仍然使觀者感到畫面很舒暢清新,沒有一絲的閉塞煩悶之意,給人一種充實之感。“如果倪瓚企圖把世界剝落簡化到不能再簡,給我們看赤裸裸山水的本質,那么,王蒙則是繁密堆疊到了極致,給我們看氤氳著豐沛生命巨力的宇宙山川。”他們的作品同樣是為了表達自己內心的情緒,但二人的表現方式都帶有深切的主觀意愿。“一簡一繁”中體現出二人不同的藝術審美意象,也體現出他們藝術境界之異。
二、二人創作技法之異
在繪畫技法上二人也各有千秋。倪瓚的創作經歷分為三個時期:早期、后期和晚期。早期為“我初學揮染,見物皆畫似”般的注重形似,后期則是典型的一河兩岸式面貌,晚期更歸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的平淡質樸。在用筆上倪瓚創折帶皴法,常用干筆渴墨皴擦,山石則用渴筆側鋒,他的折帶皴最有特點。皴法的運用也是他疏體山水成熟的關鍵。《漁莊秋霽圖》中全畫皆以筆墨表現,不著一色,給人一種清凈、蕭疏之意。畫面內容就是以極簡率意的筆墨皴擦建構而成的畫面空間從而形成特有的荒寒境界。這種極簡渴墨的筆墨手法在明末清初的山水大家漸江筆下表現得淋漓盡致,漸江的一生尤醉心于倪云林,他自己也常在畫中題字“仿倪云林”,更甚之在詩中云:“欠伸忽見枯林動,又記倪迂舊日圖”。由此可見漸江對云林是推崇仰慕的。相對于倪瓚的山水作品,他可能更崇敬其超凡脫俗的精神風貌與通透出塵的生活態度。
王蒙則以其擅長的解索皴和牛毛皴法表現南方山水的山石樹木,他的皴法是從董源的披麻皴中化出的。在《青卞隱居圖》中就能夠看出其獨特的筆墨技法,點線形態清晰分明,畫面效果疏密有致,用筆純熟,層次豐富,變化無窮。王蒙的作品多為密體山水且總能夠帶給觀者無窮的力量感,連倪瓚都曾在他的作品中題著:“叔明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董其昌也曾題辭曰:“筆精墨妙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王蒙以豐富多變的筆勢表現出林嵐郁茂、氣勢蒼茫的意境,望之郁然深秀,其畫法和表現出的精神狀態,是元代以前所不曾見的。可見他的畫面是多么的豐實飽滿。一幅畫,以簡疏可以取美,以密繁也同樣可以制勝。筆墨中的空,有時可當作一種“充實”;筆墨中的實,有時也可當作一種“空靈”。這里不得不提的是:雖然二人在繪畫技法上各有主張,各有懷抱,但對于在山水風格師承前人這一方面,他們都對董源和巨然這一派南方山水畫風是推崇的。
三、二人的內心世界分析
倪瓚和王蒙同為“元四家”中的重要畫家,但二人面對世俗之事的態度卻大相徑庭。倪瓚持出世態度,在倪瓚少年家道興盛之時,他可能也曾想過入世,但經歷的家道中落、社會變革,看到的人世百態,深識的人情冷暖,直接影響到他晚年那種強烈出世的思想。他抱著“不事富貴事作詩”的清高態度,努力擺脫世事對他的干擾,致力于做一個清凈無為、與世無爭的自由者。倪瓚作畫不求形似,也不求顏色似,僅是為了抒發胸中的逸氣,用以自娛。在他的畫面上更多表現出的是“空”與“靜”,這些所折射的正是他心境的純潔干凈、一塵不染。無論是在畫中還是畫外,他都不愿被任何塵世喧囂所沾染或煩擾,力避塵俗,守住自己的一方“凈土”,守住畫家的精神棲居之所,以便“與天地精神往來”,這些顯然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對倪云林影響,是他在亂世中參悟人生、以畫為寄的結果。
受到儒家積極進取思想的影響,王蒙卻主張積極入世,愿意在仕途有所作為,也善于審時度勢。王蒙生于家學淵厚的世家大族中(他的外祖父是元代大畫家趙孟頫,外祖母是管道升),在繪畫風格上深受其外祖父趙孟頫“古意”思想的影響,在學習作畫方面從小就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藝術功底自然也是扎實雄厚。也正因此,他時常對身份地位抱有幻想,元末時局動蕩不安,農民起義時時爆發。他卻過多地考慮個人利益,忽而入世忽而歸隱,官而隱,隱而官。“為了個人興趣也為了個人的得失,機關算盡,有時得到好處,但最終‘誤了卿卿性命。王蒙的思想氣質同樣反映在他的畫上。他的畫繁密多變,拖泥帶水,面貌不一,不像倪云林畫那樣單純和簡練明潔。”《青卞隱居圖》就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挺勁有力的線條、緊密細致的筆法、筆力雄健的皴法營造出生動靈活的畫面氛圍。在王蒙山巒重疊、草木豐茂的山水畫作品中,總是寄托著畫家隱逸山林的理想,但他的內心又有著強烈的入世愿想,由此可見他的內心是矛盾的。也正是在這種苦悶、糾結的精神狀態下,王蒙創造出了后世所謂的密體山水,點線之間的繁密相交,也可謂是一種“胸中逸氣”的抒發。當知倪畫和王蒙所畫,在形式感上,明顯地產生了“黑白互變”的并美效果。其實,畫家個人經歷與藝術追求對于風格形成影響是直接的,因此,無論描繪的是何種畫面效果,它都能夠展現一位畫家豐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不失為一種藝術美與風格美。
四、小結
“元四家”的繪畫被后世之人所推崇,他們各具風格,獨樹一幟。“一簡一繁”更是元代時期山水畫史上的重要特色,而這在倪云林與王蒙的畫風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就美術史意義來看,無論是倪瓚的疏體山水,還是王蒙的密體山水,都對后世的山水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明清之際,畫壇上有諸多畫家學習倪瓚、王蒙的畫,但學得成功者微乎其微,這也是值得反思的。事實上,二人的獨特藝術風格中無不蘊含著二人的審美態度與人生追求,突顯著時代特色與畫家的主體意識,而這是筆墨之外的,更是精神層面的。對比分析二人藝術風格的不同之處,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兩位畫家及其作品,同時對元代時期文人畫的發展有更深入的掌握,同時,也為作品分析與畫家個案研究做積極的嘗試。
參考文獻:
[1]蔣勛.美的沉思[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4.
[2]陳傳席.中國山水畫史[M].修訂版.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3]王伯敏.中國繪畫通史:上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作者單位:
安徽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