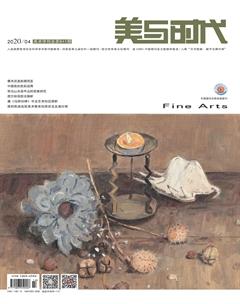霍州媧皇廟壁畫中女侍男裝形象分析
郭璐
摘 要:山西寺觀壁畫中的人物形象、服飾、造型、構圖、色彩都有一定的傳承性。自唐代出現的女侍男裝形象,為什么還會出現在清代的霍州媧皇廟壁畫中?清代霍州媧皇廟壁畫中的女侍男裝形象是不是真的來源于唐代?文章基于這兩個問題,從霍州媧皇廟壁畫中女侍男裝侍女的形象、服裝、色彩、構圖四個點出發進行論證,并與唐代墓室壁畫中的女侍男裝形象進行對比分析。
關鍵詞:壁畫;霍州媧皇廟;女侍男裝形象
山西寺觀壁畫歷史悠久,自唐初始,歷經五代、宋、元、遼、明、清,到民國結束,期間歷經近兩千年。民國時因為戰亂及外族入侵,壁畫發展開始停滯,所以清代成為山西寺觀壁畫燦爛篇章的收筆之際,研究清代寺觀壁畫也是對山西寺觀壁畫藝術的發展進行一個完美的總結。
一、霍州媧皇廟壁畫概述
霍州媧皇廟位于山西省臨汾市霍州市大張鎮賈村,初建不詳,于明代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重修,后毀,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重修。廟內現存《重修媧皇廟圣母碑記碑》中記載:“媧皇圣母廟始建年代不詳,萬歷三十八年失火重建,清乾隆二年重修。”寺廟坐北朝南,占地約兩千三百平方米,現存戲臺、鐘樓、圣母殿、左右垛殿,總共六座清代建筑,現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5月25日,被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寺廟內現存壁畫主要位于主殿圣母殿中,東西壁及左右山墻,總面積約七十四平方米。
西壁,名《開天立極圖》,壁畫約二十六平方米,描繪圣母補天成功召見各路神王納賀之場景。畫中共有女性人物二十三位,圣母主神一位,女裝侍女十五位,飛天侍女一位,女侍男裝形象六位。其中,六位女侍男裝形象分別為站立主神圣母女媧身旁兩位,大殿右側配殿內三位,大殿左側配殿內一位。
東壁,名《萬世母儀圖》,壁畫約二十五平方米,位于圣母殿的東墻壁上。相對于西墻壁上的《開天立極圖》,東壁上的壁畫有一定的破損。一處破損位于端坐于正殿的媧皇女媧身上,缺失部分長一米左右,最寬部分約五十厘米。還有一處破損在站立于左側的侍女大臣處,缺失部位長三米左右,最寬部分約三十厘米。畫面中部牌匾“萬(萬)世母儀(儀)”,“母”字處有明顯的修補痕跡。畫面主要描繪媧皇圣母在宮殿里召見大臣處理政務的場景。壁畫中共有女性人物十位,圣母主神一位,女裝侍女六位,女侍男裝侍女三位。女侍男裝侍女位于壁畫中左側配殿書房內。
北壁東次間,名《后宮尚食圖》,壁畫面積約十一平方米,位于圣母像后右側殿壁上。畫面右上部分帷帳處有長三十厘米、最寬約四十厘米的壁畫脫落,裸露出墻皮。壁畫描繪了后宮侍女準備膳食的場景。畫面中共有五位女裝侍女,無女侍男裝形象。
北壁西次間,名《膳房備宴圖》,壁畫面積約十一平方米,位置為圣母像后左側殿壁上,整幅壁畫保護完好,構圖完整,描繪后宮侍女正在備宴的場景。畫面中共有五位女裝侍女,無女侍男裝形象。
綜上所述,霍州媧皇廟壁畫中女侍男裝侍女主要位于東、西壁上,東壁為三位,西壁為六位,共九位。結合壁畫上的畫工題記,廟內壁畫東壁上方留題“汾西縣畫工郭重、王恒、武尚志書畫,油匠陳玉順、陳玉昌”,西壁南部上方題記“汾西縣畫工……,乾隆二年歲……”,得知該寺廟的壁畫創作時間為清乾隆二年。
二、壁畫中女侍男裝人物形象分析
圣母殿壁畫中的女官形象,具有典型的唐代女侍男裝裝扮特點。唐代是我國古代封建王朝中發展最為強大的時代之一,經濟繁榮,國力昌盛,文化交融,萬國來朝。文化的融合離不開人口的流動,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這里交融,“女侍男裝”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舊唐書·輿服志》記載,唐玄宗時宮中婦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即宮內宮外,貴族民間,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式皮靴,女子著裝男性化了。于唐高祖李淵第十五子李鳳墓中出土的《捧物男裝女侍圖》,以及新城長公主墓出土的《捧卷軸侍女圖》,兩幅畫與霍州媧皇廟主殿東、西壁畫中的男裝侍女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此我們只討論其人物形象,在后文中會對其裝扮及服飾進行深入分析。
書房中的女侍男裝形象,頭部呈現橢圓形,人物面部、手指、五官等部位的線條用赭石細線勾勒,線條柔和纖細。人物的細節部分也特別出彩,畫工在勾勒眼睛時,上眼皮處線條用黑色墨線勾勒,連眼睫毛也清晰可見,下眼皮用赭石色細線勾勒,這種畫法使人物眼睛更加立體,更加傳神。
目前,關于圣母殿壁畫中的女官形象存疑,在縣志及各種文獻資料中均無提及壁畫中的這九位女侍男裝身份,僅在壁畫藝術博物館編著、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山西古代寺觀壁畫珍品典藏(清代卷)》中介紹霍州媧皇廟壁畫《萬世母儀圖》右偏殿時提及“描繪女官正在起草文書”。再加上筆者發現,圖中女官從面部及形態的刻畫上都與侍女形象相同,且女官耳朵上佩戴的耳飾與壁畫中侍女的耳飾為同一種,故此推斷壁畫中的女官為女官侍女。
在動態上,女官侍女呈現三種姿態,伏案疾書、捧卷欲行以及站立傳達。三種形象,動態起伏不大,同樣是以肢體動態表現人物。
三、壁畫中女侍男裝形象服飾分析
據考證,畫中侍女所帶幞頭形制為軟腳幞頭,所以在服飾及頭飾上我們無法推斷男侍女侍的區別。但是經過仔細比對發現,十四位侍者中有十位耳朵上都帶有耳飾,而西壁左下角的四位此裝扮者,帝王形象身后兩位手持扇及帷帳的侍者,以及帝王形象身前兩位侍者均無耳飾。《宋史·輿服五》言:“非命婦之家,毋得以真珠裝綴首飾、衣服,及項珠、纓絡、耳墜、頭(須巾)、抹子之類。凡帳幔、繳壁、承塵、柱衣、額道、項帕、覆旌、床裙,毋得用純錦遍繡。 ”從這里可以看出,宋代婦女是有佩戴耳飾的,只是只有身份地位較高的女性才有此權利。佩戴耳飾真正流行起來是在明清兩代。通過對文獻資料研究發現,中原男子自古沒有佩戴耳飾的習慣,少數民族及蕃將有佩戴金環耳飾的習慣。故此推斷,壁畫中佩戴耳飾的為女侍,未佩戴者為男侍。以下是對九位女侍男裝人物的服飾分析。
西壁壁畫配殿為捧盤女侍,其服為交領窄袖長袍,衣衽及袖口為黑色鑲邊,服裝未見有配飾,紅色大帶束之腰間,衣衽為右衽。
站立圣母旁服飾侍女與捧笏板侍女都頭戴金鳳花幞頭,內著白色中衣或衫,外著圓領窄袖長袍,通體無裝飾紋樣。下身內搭長裙或褲,顏色為橙色、紅色。左侍者腰系黃色大帶及紅帶白銙樣式的革帶,右侍者腰系紅帶白銙樣式的革帶。
左邊配殿書房捧畫卷的女侍者,頭戴幞頭,內搭曲領中衣,外著青色圓領長衫,白色抱肚,黃色大帶束之,衣領鑲邊為紅色。
紅衣侍女,頭戴幞頭,幞頭邊被大樹從中間遮擋未見金色裝飾,紅衣窄袖長衫,腰間有大帶及黃色革帶。
持筆侍女,半身像,下身遮擋,頭戴金鳳花簪頭,內搭曲領中衫,外穿圓領窄袖長衫,領口及衣袖口處有藍色鑲邊。
東壁壁畫左配殿中三名侍女與西壁右配殿中三名侍女,從服裝到腰部配飾以及頭飾、服制都一樣,只有顏色不一樣,故此不做分析。
綜上所述,壁畫中女侍男裝侍女都頭戴金鳳花黑巾幞頭,內搭曲領中衫,外穿圓領長衫,除顏色不同外,在服裝及頭部裝飾上都呈現出宋代的服飾特點。
四、壁畫中女侍男裝形象顏色分析
東壁畫書房內三位女侍男裝形象都站在書房中間,結合宋代服飾制度,再加上左右兩位侍女形象上有遮擋,而中間侍女全身立像,故此推斷中間紅衣侍女身份較高。雖然圓領長衫在漢朝時就已出現,但是在漢時多為內穿,而唐宋官員以圓領服飾為主。此處紅衣侍女在腰帶上沒有按唐制(唐代四品深緋,為深紅色,五品淺緋,為淺紅色,并金帶),以而是束以藍色大帶和革帶,故此推斷兩位侍女在服飾顏色上遵循宋制。
著綠色侍女服的女侍男裝形象有四位。其中,東西壁書房各一位,圣母女媧身旁站立兩位。書房中的兩位都為淺綠色,圣母身旁兩位為深綠色,內著拖地長裙,只能看到紅色翹頭,所以鞋制為履。
兩位手持筆正在書寫的侍女,一位服飾為青色,一位偏向粉色,但是仔細觀察會發現,粉裝侍女壁畫有顏色脫落痕跡,故不加以深考。
從女官服飾顏色中我們可以看出,她們都頭戴黑色幞頭,服飾顏色為純色,下身及鞋子都被遮擋,無從考證。但是結合《輿服志》中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女侍男裝形象在服飾顏色上遵循了顏色的等級制度,可以據此辨等級,分尊卑。
五、壁畫中女侍男裝形象構圖分析
壁畫中女侍男裝形象構圖特點是奇偶聚散。
在以人物畫為主的畫作中,奇偶聚散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突出人物主體形象,賦予畫面場景變化,構成畫中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的節奏的重要手段之一。
東壁畫書房中,一顆大樹把畫面分割成了兩個空間,大樹的左邊,紅衣侍女與捧卷侍女構成了偶,大樹右邊獨立侍女則為奇。
西壁畫中的書房中,有三位女侍男裝侍女,即紅衣圓領長衫侍女、手抱畫卷侍女、持筆侍女。紅衣侍女被樹木從中遮擋,可與持筆侍女為聚,手抱畫卷侍女單獨一人則為散,也可與持筆侍女為偶。
西壁壁畫正殿站立圣母,左右各有兩位女侍男裝侍女,看似為偶數,但是畫匠通過人物前后遮擋關系,持扇侍女就被圣母遮擋住,兩人與捧笏板的侍女就構成了聚散關系,這三人還能分別同站立侍女與另一侍女構成奇偶關系。簡單的四位人物,通過聚散與奇偶的組合就構成了繁復的變化。
在清代寺觀壁畫中為什么出現女侍男裝形象,筆者結合上文中女侍男裝藝術形式及霍州媧皇廟的祭祀主神進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結論:第一,霍州媧皇廟祭祀主神主要以圣母女媧形象為主,所以壁畫內需要出現女官。第二,女侍男裝形象在晉南寺觀壁畫發展中一脈相傳。唐代稷山青龍寺壁畫、元代永樂宮壁畫、明代洪洞水神廟壁畫中都有女侍男裝形象的出現,在地域上都屬于山西晉南地區傳承體系。媧皇廟中的女侍男裝形象在技法和人物形式上受到了永樂宮壁畫的影響,服飾上與洪洞水神廟壁畫中的人物形象相似。
參考文獻:
[1]柴澤俊.山西寺觀壁畫[M].太原:山西文物出版社,1997.
[2]李淞.山西寺觀壁畫新證[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作者單位:
山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