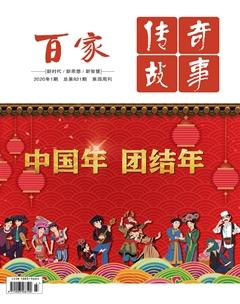淺析粟特人在柔然
摘要:粟特人早在公元5世紀初,就已然活躍在了漠北游牧民族之中。其憑借較高的政治素養成為柔然可汗身邊的智囊,并常在中原王朝與漠北游牧民族之間往來,充任使節,促進雙方交流。
關鍵詞:粟特;柔然;吐谷渾
公元5世紀初,柔然汗國繼匈奴、鮮卑之后,成為蒙古草原又一個強大的游牧政權。而最遲到了社侖末年,已經建立了從東面和北面向西域擴張的基地,表明了掠奪和壟斷絲路的意向。在這一時期,粟特人更是絲綢之路上的常見商隊之一。這就為兩者之間產生聯系提供了可能。從粟特本土向東,幾乎每一個大的城鎮或者是位于重要的交通干道上的一些小城鎮,都有粟特人的身影。關于粟特人在柔然汗國的影響和作用,因文獻記載極為有限且零散,相較于之后的突厥、回鶻而言也并未出土以柔然語記載的文獻或碑銘,以至于史料也更為片面。回鶻汗國中粟特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突厥學家認為這是對突厥汗國模式的繼承。當然突厥汗國的這種模式即使不是全部,也必定是部分地繼承自柔然,正如其國家制度的建立也是效法柔然一樣,在突厥、回鶻中對粟特人的任用正是繼承于柔然的傳統。魏義天認為公元6-8世紀的突厥、粟特融合因突厥聯盟而得以進行,而這種融合不過是粟特人與其他游牧民族聯系的更新。盡管如此,除了以后者證前者外,我們仍然可以從不多的史料之中找尋到一些粟特人的痕跡,盡管這樣很容易有“泛粟特化”之嫌。但這并不能否定柔然中粟特人的存在。
一、生活在柔然內部的粟特人
漠北地區的粟特人與柔然上層的交往,在傳世史料中不僅記載零散且往往隱藏于其他政治事件之中,故不十分引人注目。但通過仔細梳理仍然可略窺其端倪。
《魏書·柔然傳》首次提到的柔然汗國境內的粟特人是豆崘可汗時期的大臣。史載:“豆崘性殘暴好殺、其臣侯翳垔、石洛侯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國通和,勿侵中國。豆崘怒,污石洛侯謀反,殺之,夷其三族。”此處明言冠有粟特“石”姓的石洛侯為柔然大臣。據史書所載,石洛侯被殺的原因為豆崘可汗殘暴好殺,因怒污石洛侯謀反而誅其三族。對于柔然歷史的記載,抑或是對于游牧民族的記載,中原王朝歷來會有一定的貶義色彩在內。石洛侯被夷三族也更多是因為他所提出的建議與柔然一直以來的國策相違背。柔然自社侖時被拓跋珪驅至漠北,與北魏便成世仇,雙方戰爭持續不斷。柔然不承認北魏統治,反而自信受天命,應歷數,為建立帝王之業而奮斗。也正因此,石洛侯的建議才會被認為是謀反。值得注意的是,在之后興起的突厥汗國中,任突厥官職的粟特人不在少數。此處石洛侯的身份是柔然的大臣。與我們一直以來所認知的粟特人在其他政權中,尤其是游牧政權中的政治身份別無二致。而夷其三族則表明石洛侯并非孤身進入柔然地區任職,粟特人的家族存在形態或為其后突厥汗國胡人部落的前身。且除了石家之外,仍有其他粟特家族居于漠北,并在柔然汗國滅亡之后又成為突厥汗國的新寵。此外,同為提出建議的侯翳垔,則未見受到任何懲罰。此或是因石洛侯作為粟特人在柔然汗國中地位不高所致。
在柔然就任莫賀弗的虞弘,關于其的族屬,學界討論頗多,但他顯然與粟特胡人關系密切,才被北周政府任命為檢校薩保府的官員。就其經歷來看,根據《虞弘墓志》記載,虞弘子承父職,13歲就奉柔然可汗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渾等。之后出使北齊,雖然出使北齊時間,墓志未載,但從“弗令返國”可以推知,此時應為公元555年,柔然汗國滅亡之時。而此時的東魏北齊,胡人剛進入該地區不久,胡化的因素也較少。因此,虞弘與粟特人產生聯系應為其在柔然汗國時期。此或為柔然汗國中粟特人存在的間接證據之一。從虞弘的經歷可以看出,柔然汗國與之后的突厥汗國、回鶻汗國一樣,亦有任外族為官的現象。這就表明了柔然可汗有任粟特人為官的可能性。此外,在這一時期,吐谷渾、西魏北周、東魏北齊等諸多政權中都有粟特人的存在。從粟特人的利益角度出發,作為絲綢之路上一方勢力存在的柔然汗國,有粟特人入仕其中也不足為奇。
二、來往于柔然與中原王朝之間的粟特人
與上述石洛侯約屬于同一時代且見于中原史書的還有安吐根,《北史》《資治通鑒》均有記載。《北史·安吐根傳》記載:“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啟本蕃情狀,神武(高歡)得為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后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為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為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干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
安吐根自稱商胡,又家于酒泉,雖以目前我們發現的史料來看,確實不能直接判斷他是粟特人,但他先以經商為業,并且家于中古時期粟特聚落常見所在地之一的酒泉,而之后西魏末出使突厥的安諾槃陀,身份與安吐根一樣是酒泉胡,說明他是粟特人的可能性較高。根據記載,他先被北魏派遣出使柔然,出使之后,恰逢北魏分裂為東西二魏。安吐根一行就此被留居漠北,后受柔然可汗派遣,回到了東魏。值得注意的是,安吐根曾祖就已入魏,至安吐根時,其家族已然在中原地區生活了四代,其家族的主要經營活動或許均在中原境內,所以在選擇投靠對象時以中原政權為主。因此將自己在柔然所探聽的消息告知北齊,而獲得厚賞。同時,因為他對柔然的情況較為了解,并且有著粟特人的身份。因此成為東魏北齊與柔然之間的外交大使。在之后柔然與東魏北齊的兩次和親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而《北史》中的“本蕃”一詞,或是由于柔然境內粟特人頗多,因此,使得時人對于安吐根的認知出現了錯誤。將本是粟特胡人的安吐根誤認為柔然人。
三、結語
綜上可知,柔然汗國中的粟特人,較之其后的突厥時代的同一群體而言,活躍度較低,對漠北社會的融入度也較低。其身影據史載也僅現于柔然汗國的政治活動之中,并且只是作為謀臣而存在。當然,作為商人的粟特人,一定對柔然汗國的經濟(商業)有所貢獻。隨著柔然汗國的滅亡,這些粟特人就進入了新的旅程,即突厥化的融合進程。
作者簡介:王靜宜(1994.11),女,苗族,陜西西安人,西北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