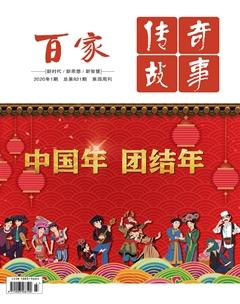淺談韓國電影發展歷程及思考
張鈺曼
摘要:近幾年來,韓國電影因其獨特的民族文化、創新的故事模式和政策的有效保障迅速崛起,在國內、國際電影舞臺上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本文縱觀韓國電影發展的歷程及現狀,探尋其發展背后的原因,希冀對我國電影產業的發展起借鑒和促進意義。
關鍵詞:韓國電影;電影發展;電影思考
1919年,韓國第一部電影《義理的仇討》上映。不得不說,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在20世紀,戰爭和侵略不斷阻礙著韓國電影的發展,但也正是這樣曲折艱難的歷程,使韓國電影在夾縫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吮吸著苦難悄然的開放了。20世紀70年代,電影《生死諜變》拉開了韓國電影振興的序幕。這部電影改變了韓國及其他國家民眾對韓國電影的傳統看法,使韓國電影重新登上了世界舞臺。如今,韓國已然成為一個真正的電影強國,其獨具特色的民族電影和類型片在世界影壇上獨樹一幟。韓國電影的振興與背后的諸多因素是分不開的,我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分析。
一、獨特的民族文化
怨恨,是大韓民國的文化精髓。“我來自充滿恨之靈的國度——韓國。恨是憤怒;恨是怨恨;恨是辛酸;恨是悲痛;恨是心靈破碎和為解放而斗爭的原動力。”特定的內容造就了韓國人特殊的內心世界和心理感受,并成為韓國人的一種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是什么讓這個民族形成了這樣與眾不同的文化?我們翻開韓國的歷史,會發現這是一個頻頻遭受侵略的國家。高麗時代平均每1.09年被入侵一次,到朝鮮時代的平均1.44年,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南北分裂,頻遭入侵的歷史極大程度上改變和充斥著韓國民眾的意識、價值觀和文化。他們關注個體的生存狀況,追求人生意義,對傷痛極度敏感化。“恨”是其中心,是積壓在整個民族內心中的情緒。這種“恨”的情緒并非嘆息、放棄、眼淚,也不是敗者的牢騷,而是積壓在整個民族內心的情緒。無恨的人是沒有希望的人,然而恨每每只被界定為一種克服的意志,一種奮發向上的動力,禁止把它發展為怨恨和復仇。
“身土不二”、憂國憂民的責任意識也流淌在大韓民族的血液里。隨著韓國社會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的不斷民主化,一大批揭露現實生活的電影作品也隨之涌現。從《殺人回憶》《實尾島》到《素媛》《熔爐》《追擊者》……他們直擊社會痛點,關注邊緣人生活,完美呈現純潔與丑惡的人性,展現絕望中的掙扎。獨裁時期冷漠而又無所作為的政府,兒童性侵與性暴力,女性從身體到尊嚴的被踐踏……韓國電影批判現實。這種責任意識的背后凝聚著過往的歷史苦難,充斥著置死而后生的決絕。“身土不二。性修不二。真應不二。無非實相。實相無二。亦無不二。 是故舉體作依作正。”這句最早出自《大乘經》的佛偈,在大韓民族的精神中也變得偏執。不僅僅包含對國家的熱愛,更是一種容不下一點瑕疵的期盼。艾金森曾寫道:“看韓國電影就像在看著一種民族文化在和自己吵成一團,在這條路上每一天都在和污穢做斗爭。恐怕現在再也沒有一個有更劇烈沖突的、在拍有意義電影的國家了。”
二、政策的有效保障
電影產業是一個國家文化產業的核心之一,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代表。然而緊靠其自身的發展想要獲得質的飛躍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來促進其長遠發展。政府的支持是韓國電影發展的第一保障。文化立國的戰略方針促使其政府對電影行業提供了大量的優惠政策和電影拍攝的良好環境。在1962年之前,韓國是沒有電影法的,只能通過刑法及某些條文對電影進行控制。從樸正熙政府一開始出臺的對韓國電影以限制為主的法律,到1997年金大中時代韓國廢除審查制度確立電影分級,韓國電影在內憂外患的曲折發展后迎來爆發。1973年,政府立法明確規定每個影院每年播放本土影片的時間不得少于146天。這些明文出臺的強制性保障措施不僅有效地保護了本國電影的發展,更遏制了好萊塢對韓國電影市場的沖擊;成立電影振興委員會,為年輕的學生導演提供實驗資金,促進其成長學習。1993年,韓國發布了電影振興法,從此之后對電影的限定開始放松,一批新銳導演出現并活躍在舞臺上。1998年,韓國與美國簽署《韓美投資協作第三次實務協議》,表示要縮短本土電影播放時間到92天。這一決議引發了韓國電影界的不滿,直接導致電影人游行,也就是著名的“光頭運動”。1999年,國會頒布了《電影法修正案》,規定取消審查制,完全采用分級制度。分級制度的使用大大放松了對電影人的限制,不同類型的電影蓬勃發展,促進韓國的電影市場多元化,易和國際接軌。再加上法律的保護和扶持、從業者和韓國民眾上上下下對本土文化的注入與保護,這些都促進了韓國電影的發展。
三、素材的善于借鑒
對于韓國電影影響最大的、真正促使韓國電影發展的因素,還有韓國電影對外國優秀電影的借鑒。20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對歐美電影進行封鎖,導致了香港電影的大量輸入。正直黃金年代的香港電影無數優秀作品林立,新銳導演輩出,對韓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文藝片《投奔怒海》《女人四十》《阮玲玉》,黑幫片如古惑仔系列,動作片,喜劇片等等,而韓國電影也借鑒了大量香港電影的題材和拍攝手法,如李長鎬,林權澤,姜佑碩等一代導演都受到了影響。另一方面,韓國較早的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積極吸收外國發達的經濟建設經驗,而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國家的先進思想也逐漸被韓國民眾接受,電影中也更多地展現了自由的意識形態。《愛的色彩》中從傳統思想中逐漸被解放擁有了自由的女主人公也正是他們這一代人的真實寫照。
而好萊塢也逐漸以其強大的影響力影響了韓國電影的制作。如2006年上映的《雛菊》,香港導演劉偉強攜手韓國演員鄭宇成、全智賢、李成宰聯合打造的這部韓國黑幫電影,就是從導演到演員到拍攝畫面都呈現好萊塢色彩的一部影片。名導加名演員加上精心挑選的拍攝場景,英雄主義精神與凄美愛情交織成一曲悲歌。而這種借鑒了好萊塢的制片模式也大大降低了影片拍攝的風險,使得拍片方、制片方與市場的關系更加和諧。
另一方面的借鑒是韓國對其自身文化的。韓國電影的類型片在亞洲一直獨具一格,多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而成。除了大熱的、根據光州聾啞障礙人學校性侵事件改編的《熔爐》和根據少女性侵案改編的《素媛》外,還有如《軍艦島》《梨泰院殺人事件》等影片。《軍艦島》這個故事背景在二戰期間的軍艦島存在與否并不重要,但片中的粗野和殘酷卻一遍遍的對觀眾進行拷問使其反思。《梨泰院殺人事件》揭露的則是當時的殺人者被無罪釋放、韓國內部的腐敗和外國人在韓國享受更高待遇的問題,這在當時社會引發了多次大規模游行和抗議。包括《王者》《再審》《大將金昌洙》等很大一部分韓國電影,內核素材都是借鑒所能引發爭論的事件,再將其改編成懸疑片或其他類型電影。
長久發展以來,類型片已經在韓國產生了模板,已成為他們的電影特色。很多人認為韓國電影缺少原創,很多時候都在“借鑒”,但這個“借鑒”經過自己的消化吸收,變成自己本土的東西,使韓國電影總是能夠“借鑒”得恰到好處。韓國人與生俱來的喜感也體現在普通生活瑣事中,透露著對生活的嘲諷,一些看似是生活中的“小問題”在電影中被無限放大,再做出喜劇效果,使民族最質樸的情感需求在小人物身上加以展現。如果說中國有周星馳等無厘頭式的電影,那么韓國就是這種對生活無聲的嘲諷。韓國電影對政府的嘲諷和抗議也是絕無僅有,除了日常生活中對政府的游行抗議之外,也在電影中有所體現。如《恐怖直播》中大尺度對韓國政府的抗議,不僅在韓國本土,更是在世界上都引發了熱議和反響。
韓國電影對社會良知、人性的省思和拷問,使其處于電影業的領先地位。韓國電影人也在寬裕的政策下不斷厚積薄發,不斷培養出新的人才。雖然中國電影不會向韓國電影那樣百無禁忌,但面對韓國電影的繁榮,中國仍有很多可以借鑒的經驗。藝術創新能力低,題材單一,具有國內外影響力的電影制作人的嚴重匱乏,版權意識的薄弱等都是目前中國存在的問題。提高電影產品的占有率和競爭力,國家對電影產業的扶持,以及電影的分級制度都勢在必行。韓國有句口號:“韓國的就是世界的!”。希冀著中國電影也可在某天喊出這樣一句口號:“世界的就是中國的!”
參考文獻:
[1]劉國清 面對社會現實生活-韓國民眾神學評注[j]宗教學研究,1996(03)。
[2]李泫淑 《悲歌一曲》與韓國人傳統審美意識 [J]當代電影,1996,(4):78.
[3]Atkinson,Michael.Blood Feuds[M].village Voice,21 August :116.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