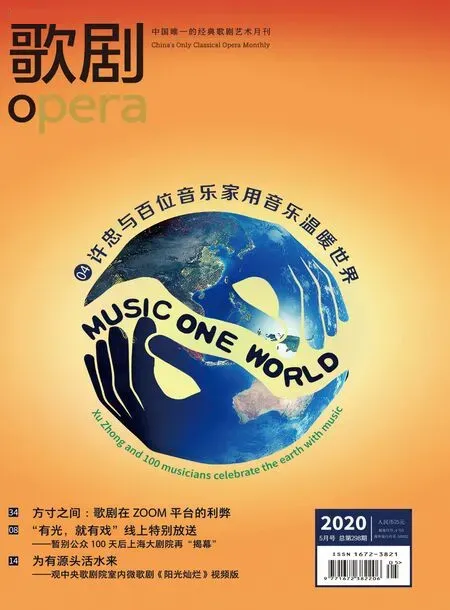2020四季劇團音樂劇藝術與產業一瞥(三):“內需型”觀眾市場形成的關鍵
慕



淺利慶太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重視戲劇與觀眾的關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觀眾平權”意識,當然這首先得益于日本音樂劇觀眾的涌現。“二戰”后僅僅20多年,日本就成為世界第二二大經濟體。“泡沫經濟時代”的日本,非常喜歡到美國的地盤“買買買”,甚至情緒高漲地表達“日本可以說‘不”的觀點。同時,還越來越注重精神和文化消費,對文化生活的娛樂性要求也越來越高,文化及相關產業開始互相滲透;日本人很快就加入了百老匯的觀劇大軍,在一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歐洲巨型音樂劇的熱潮,少對白、旋律動人、多視覺震撼的奇觀劇非常對非英語觀眾的胃口,與此同時,音樂劇觀眾的規模在日本本土也開始“井噴”。
如今,泡沫時代狂熱的“浮躁心理”從日本社會基本褪去,劇場生活本身也變得平常,特別像在音樂劇現場那些喜悅而克制的觀眾,掌聲雷動,卻依然能心平氣和地穩坐著。那么,日本“內需型”音樂劇觀眾市場形成的關鍵何在呢?這當然要從分析觀眾類群入手。
其一,“本土”觀眾是基石。長期駐場公演模式是音樂劇市場發達程度的試金石,意味著演出周期要從“天”或“周”的計量單位,實現以“年”為單位的轉型。按照國際演出慣例,就一個想要成為音樂劇之都的城市而言,要吸引當地人口的20%一30%前來觀劇,這個目標才能實現。紐約2018年約有1954萬左右的人口。根據百老匯聯盟的數據統計,2018一2019演出季,百老匯迎來了1480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雖然其中65%的觀眾都是游客,但我們不能忽略還有19.5%紐約市區的觀眾,和15.5%的市郊觀眾,這說明紐約約有518萬居民會買票看百老匯的戲,約占紐約市人口的26.5%。盡管這些數據每年會有上下浮動,卻基本長期穩定。而“巡演百老匯”當年演出季的觀劇人數為1850萬人次,約占美國總人口的5.7%,美國其他城市也很難做到音樂劇長期駐場公演模式,所以一般也是“定期輪換公演”。
淺利慶太的“戲劇平權觀”是成就四季劇團“奇跡”的主要原因,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在演員端,他主張給每個演員都有走上舞臺或扮演主角的機會;在觀眾端,其平權意義更為顯著,四季劇團每年在200余座城市推出3000場演出,其中一半在首都圈外。其音樂劇產業雖從東京起步,但淺利慶太在1980年代中期就致力于推行“打破文化集中東京”原則,這是非常有政治和經濟遠見的,與日本當前主張的“地方創生”理念十分契合。比如從超大城市東京到大城市大阪、名古屋、札幌、福岡等,再到中型城市仙臺、廣島、靜岡等,皆有音樂劇《貓》的足跡,這樣的產業拓展既能促進區域經濟活躍繁榮,也能讓更多非首都及首都圈的日本人享有藝術的權利。
劇場要的不是氣派,而是觀劇的效果;選址要的也不是特立獨行,而是能否滿足以公共交通站點為中心、10分鐘步行路程為半徑的便利要求。四季劇團多年維持全國觀眾人數達300萬左右,其中絕大部分都是音樂劇觀眾。根據琵雅公司提供的數據,2018年日本舞臺演出的觀眾為2602萬人,其中觀看音樂劇的829萬人所占比例最高;而2018年日本人口數量為1.26億人,意味著舞臺觀眾占到了人口比例的20%左右,其中音樂劇最高,占比6.6%,也說明日本這個“內需型”的音樂劇演出市場,最適合的也恰恰是四季劇團目前的模式,即“長期駐場”和“定期輪換”并行。可見,音樂劇制作人如何評估“本土”觀眾,十分重要。四季劇團的這種不僅限于東京的拓展音樂劇市場模式,才真正實現“日本上演通算”。
反觀中國,上海是目前最具音樂劇消費市場潛力的城市,其音樂劇演出場次占全國34%。據上海市演出行業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專業劇院共舉辦音樂劇演出292場,吸引觀眾28.7萬人次,在11個劇種中排名首位@。但是,即便像上海這樣演出市場化程度頗高的城市,甚至有了沉浸式戲劇《不眠之夜》這樣已經成功實現了長期駐場公演的劇目,但音樂劇演出仍處于部分劇目“定期輪換公演”階段。可見距我們打造出“音樂劇之都”的夢想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重中之重是用中外優秀劇目首先贏得至少5%左右本土觀眾的青睞,并逐步拓展至20%的本土觀眾,才能使音樂劇成為“內需型”演出,其后再考慮超越“內需”的問題。如果未來每年都有500萬左右的上海常住居民愿意走進音樂劇劇場,再加上那些反復走進劇場的劇迷以及來滬的游客,甚至打著“飛的”來上海觀劇的超級擁躉,這個目標還是有望達成的。
其二,把部分本土觀眾變成“回頭客”。在“專有劇場”實現高品質音樂劇的長期駐場演出,除了要贏得更多首次走進劇場的觀眾,實現本土觀眾的最大化以外,培育劇團或是某部劇的鐵桿劇迷,以精彩的作品和滿滿的“誠意”打動他們,吸引他們最先搶票和反復觀賞,也十分重要。在中國,普通的駐場旅游歌舞演出之所以往往品質不高,就在于它的觀眾群被定位于來來往往的游客上,而且是以低價銷售團體票為主。這樣的消費關系就是“一錘子買賣”,怎么可能做成真正的產業。音樂劇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旅游演出,“到此一游型”游客雖然有數量上的優勢,但如何把盡量多的觀眾轉變成“回頭客”,才是發達音樂劇市場的真正經驗。
2018-2019演出季,百老匯的觀眾人均觀看了4-5部作品,其中劇迷或粉絲至少觀看了15部戲,這部分群體雖只有觀眾的5%,卻以415萬張演出票帶動了28%的票房。而且,大多數觀眾都是一家人、情侶或友人的結伴而行。對于四季劇團而言,“回頭客”就是目前擁有19萬會員數的會員群體——“四季之會”,觀眾占比有6%。而且,四季劇團的團體票也不多。淺利慶太有一句話說得好:“四季之會”不只是一個話劇或音樂劇“愛好者組成的俱樂部,而應該成為擔負起使戲劇在地方扎下根的組織”②。與百老匯類似,在日本,音樂劇的受眾群體也以女性為主,只不過年齡分布上,中青年占多數。如何能真正走進受眾群體的內心,是組織豐富多彩的體驗活動的核心。當然,這一策略還得與劇團的整體定位相得益彰。畢竟“四季之會”這個奉行作品優先主義,而非明星優先的組織,是不會將會員俱樂部做成某某明星的“全國粉絲群”的。
其三,培育未來的觀眾。“二戰”后日本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獲益于教育。四季劇團的杰出,也恰恰在于淺利慶太不只是將音樂劇看作一門“生意”,吸引本土觀眾和資深劇迷都很重要,更關鍵的是培育未來的觀眾。四季劇團“合家歡型”音樂劇最適合的是小學六年級的孩子,加之淺利慶太的平權理念,也切實地讓全日本十二三歲的適齡兒童走進了“心靈劇場”。2008年命名的“心靈劇場”③,并不僅是一家實體的劇場,而是四季劇團從1964年就持續進行的“公益演出”名號。這些演出以學校為單位,貫穿日本全島,作為藝術鑒賞課的一部分,每年平均惠及50萬左右小學六年級學生,占日本同年齡段孩子總數的近一半左右。其中,不少孩子都是第一次走進劇場,體驗神奇的音樂劇世界。這些童年的美好記憶會植根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情感上也會對四季劇團建立某種信任的聯系,他們正是未來潛在觀眾群。
在運營上,“心靈劇場”的公益演出由劇團內部獨立核算的部門——非營利性的“四季財團”來負責,與“營利性”的演出制作管理區分開來。難怪至今四季劇團都只是內部人員持股而沒有成為上市企業,因為上市企業很難不受股東利益的影響,那每年近千場“公益演出”的理想還如何達成?服務觀眾,甚至服務于未來的觀眾,而非服務股東,更是四季劇團秉持的理念。的確,在音樂劇發達的西方市場,最有市場的音樂劇都會有“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校園版演出(更不要說許多盈利性音樂劇都有著“非營利”的創作工作坊前身)。
其四,防患于未然的觀眾隱憂意識。國際部小林聰部長在向我們介紹四季劇團的理念、現狀等意料之中的信息后,最后的落腳點讓人印象極為深刻,那就是“少子化、高齡化、人口集結都市”等現實隱憂都會實實在在地影響日本戲劇生態。實際上,就在日本泡沫經濟時期,日本就已顯出老齡化的端倪了。即便如今“東京都市圈”的人口數量超過3700萬人,是全球人口最多的都市圈,也依然改變不了未來人口減少的趨勢。
四季劇團與日本其他戲劇從業者一樣,都十分渴望“脫離內需型”的日本音樂劇市場,比如打破語言藩籬,推出更多“非語言類”的舞臺秀,吸引更多的訪日游客,或者是為他們準備多國語言字幕的高科技眼鏡等;但是音樂劇的魅力也會因“字幕”的干擾而失去一些沉浸的體驗,因此“字幕眼鏡"無疑是一個悖論性質的發明。不過,對于患有聽覺障礙的觀眾卻十分珍貴,目前這一技術已經出口至英國,也是定位于服務此類人群。
當然“脫離內需型”市場最根本的還在于從“做內容”入手,使原創劇目做到產業性質的“版權輸出”才行,如同迪士尼向四季劇團輸出《獅子王》,韓國音樂劇制作巨頭EMK向東寶輸出《弗蘭肯斯坦》一樣,它們都是真正具有“世界性”主題和表現手法的作品。總體看來,日本原創音樂劇目前還有一段路要走,不過應該還是有相當潛力的,比如日本演藝企業制作的2.5次元音樂劇就是極有“脫離內需型”實力的類型。近年,四季劇團也從1990年代初到訪中國作“文化交流式”演出,逐漸向中國兒童歌舞劇市場拓展。
談到觀眾隱憂意識,淺利慶太也沒有把演藝娛樂的競爭看得太重。雖然四季劇團誕生之初,電視已經開始在日本逐步普及,影視業似乎一直在與舞臺搶奪著觀眾和演員,但他認為“舞臺與電視是完全不通用的世界”④,所以四季劇團一直與喧囂的影視圈保持著距離,就連日本觀眾在劇場里安靜矜持地觀劇也成為一道特殊的風景。淺利慶太致力于通過戲劇為觀眾帶來生命的快樂;只要這種需求存在,四季劇團就有存在的意義。
近十年來,舞臺表演藝術因為傳播方式的變革再一次受到了挑戰,市場需求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在這個“全球在地化”(編者注:Glocalisation,是全球化與在地化兩詞的結合,意指個人、團體、公司、組織、單位與社群同時擁有“思考全球化,行動在地化”的意愿與能力)的時代,四季劇團要不要繼續獨善其身呢?比如西方音樂劇部分從業者正力圖將最新科技和社交網絡也帶到劇場文化中來,這當然不是允許觀眾在演出過程中拿手機拍照,上傳社交網站與朋友們分享,而是鼓勵觀眾在演員謝幕時盡情拍照,異時異地共賞地進行社交網絡分享,這種口碑的力量是多少官方宣傳效果所無法企及的,為什么有著觀眾隱憂意識的日本人仍然不愿意這樣做呢?中國觀眾雖然玩轉了“朋友圈”的觀演分享,但我們面臨著與日本從業者不同的期待和隱憂,畢竟“內需型”市場也是很不容易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