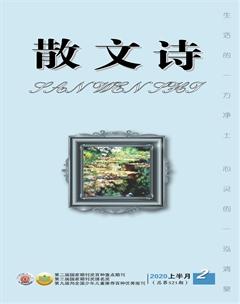窯鄉紀事
曉弦
刻板的磚事
在窯鄉,你會發現,京磚們都站立著,緊挨著身子,像坦誠相見的哥們;
到了城里,則被放倒著,平鋪直敘……這尋常的秩序。呆板的時間久了,難免會出現玩世不恭的塌陷。
這時,要將塌陷的那一塊,挪一下,看身下有否爆芽的春事。慢慢扒開,周邊受牽連的那些磚塊。用力刨除上面根莖般青筋暴突的心事,以及凝結在上面的陳年傷痂,像逡查那些不干凈的,閹人。
這不是人間的簡單游戲,而是一場不經意的工事——畫地為牢,抹上水泥,打上膠水,嚴防死守季節的茍延殘喘,保持規整的形制,以及用夢幻般的橡皮榔頭,輕輕叩平喘息的地平線。
沉默的瓦事
在江南,磚砌的煙囪,是稀罕的事物,上面總是頂著一塊青磚。
太刻板了!我的爺爺,這鄉村的泥水匠,用磚塊筑成一個煙囪后,就要放下泥刀沉靜片刻,像是為上帝做一場禱告,然后拿起身邊那張瓦片輕輕蓋上,像神諭,不讓我們去觸碰,那是為堅硬的生活,留出一個弧形的出口。
這細微的改變,為生活亮出好看的天窗,好讓月亮在路過村莊時,彎下腰來,通過它,撫摸到堂前的神龕,以及祖先粗糙的臉,并以絨毛般淡淡的光暈作回音,好讓走散的親人,輕輕地團聚在一起。
窯墩的圍城
遇見一個窯工,他說,窯烏龜!
這個磚一樣堅硬的名字,曾是太爺爺的名字,這自虐的稱謂,在窯鄉是多么的平常!
風吹雨打的日子,窯膛是烏亮的天堂,是太爺爺的最愛!即便夜涼如水,也拼死抗衡蟻穴潰堤般的坍塌。
這清末明初的磚瓦窯,成了最接地氣的文化遺產。太爺爺曾用九斗糙米盤來這個土窯,他說土窯是活氣生根的祖宗,又像一個從小就纏不住小腳的大腳女人。
她是我的太奶奶,劈柴、燒飯,拾掇生活的碎瓦亂磚,螞蟻般搬運著生活的勞頓——用時間的籌碼計數,把每張磚瓦,當作火焰般優雅的兒女。日復一日,把長滿萋萋雜草的窯墩,變作森嚴壁壘的圍城。
幽默的窯工
進入窯鄉,感覺每個來采風的人,都疾速地進入了白色的時光隧道。寧愿把眼前見的干窯誤作千窯。
千窯!多么響亮而宏闊的名字。要是你逆著倒流的時光,隨便掀開哪一座磚窯的大氈帽,里面,都埋有一顆涂抹著煙火色的巨大的心臟啊!
這樣的大場景,這樣的大氣派,源自一塊塊京磚。打量,或者凝視,會像一個歲月長鏡里的黑顯屏,逸出窯鄉淳樸而綿柔的民風。裝窯,封窯,等候神祇般的吆喝。用新收的柴禾燃起第一縷火焰,迎候一摞摞帶著浩蕩皇氣的訂單,將庸常生活煨出嘉禾稻米的香來。
遼闊水鄉,多情的水鎮,稻秸升起的火,是世上最好的火,適合這里所有用善來命名的水。最好的火,遇到上善的水,木訥的泥巴會把自己叫醒。在京磚們或輕或重的磕碰聲里,再孤寂的瓦當也會滴瀝出三月的春情。
當一窯墩的磚瓦被煅燒,被封窯,像是俊逸的秀才在等待金榜題名。又像是足月的孕婦在等待黎明那縷殷紅。而這時的干窯,便是一座希望之城。
這時的男窯工喜歡把女人比作瓦,這時的女窯工喜歡把男人比作磚,這時成疊的瓦,臣服于男人粗礪的手,像精美的手風琴,在空中舒展柔美的琴扇。
難怪他們愿意互相戲謔為窯烏龜,免得被堅硬的生活的棱角磕破頭皮,免得被日常死寂般的單調灼傷內心。所以,理想的窯工,半是男人,半是女人,就像高聳的煙囪,與那密閉的窯膛。
這么神諭般的事物,只有在水鄉,才可鑄就黎明般高遠而迷幻的風景。神奇的教堂
進得幽深的窯來,一眼認出,用耐火磚圍砌成的窯壁,是某個反芻動物的胃。
粗陋淺顯的火膛,是尋常日子的賁門,進食多了,難免會腸梗阻和脹氣痛,產生生活的憂傷,與惆悵。
而聳立窯外的煙囪,是節并不柔軟的十二指腸。
此刻,當我通過窯頂蒙塵的天窗,向窯膛探望,發現——這真是個黑色的教堂,那些沉默著搬運磚瓦的窯工,全是耶穌的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