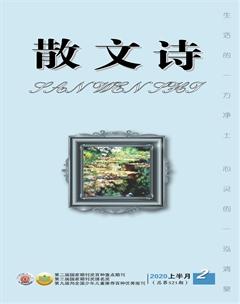草說
楊運菊
不管水有多淺,地有多薄。給一口空氣和陽光,榮,不忘染綠原野;枯,不忘反哺大地。
.冷卻到荒漠禿嶺,回歸到草木本心。把香艷留給玫瑰,把潔白留給青蓮,把碩大留給皇天后土里的詩行。做低注解的草,背誦《傷寒雜病論》。
草叢間蟲鳴出沒。
鳴聲可抒情,亦可哀怨,寂寥的旁白是草一生的宿命。
寰宇之遼闊,聲音總被覆蓋。
有草的地方總有風生。
風生可水起,亦可水落。可湮沒馬蹄,亦可現出牛羊。
每一棵草都不肯把風聲走漏。
草無需和大樹比高。
大樹有大樹的高堂,草有草的明鏡。高堂有高堂的語錄,月光如鏡,到處都是草的子民。
廳堂里的標語像穿堂里的風,仔細琢磨,漏洞百出。而草天生具有穿墻術,穿過紙糊的燈籠,爛泥和墻。當水落樹根出,“草在結他們的種子”,即使無人采集和春種秋收。
他們像自由跳躍的貓,飛檐走壁,書寫春夏秋冬。
春天襯托紅花,夏天裝點綠葉,秋天啊,陪枯藤老樹昏鴉走一程。
快下雪吧,讓寒冷來得再透徹一些,床邊的接骨草,雪地里的稻草人,睜著眼睛說瞎話。
他們像不規則的翅膀,不按套路飛翔,蝙蝠的超聲波摁住氣流。他們像蒲公英的約定,吐一口氣就是一三五、二四六的接頭暗號。
他們飛落到哪里,種族就繁衍到哪里,根就扎在哪里。他們觸摸彼此的呼吸,共同跳動一個心臟和脈搏。
他們著一色的服裝。沒有王子和公主,沒有少爺和小姐。他們擁有同一個名字叫渺小,渺小到遼闊,遼闊到虛無。在虛無里前仆后繼,像風推著沙走,走散,歸于塵埃落定。
落定的塵埃,再好的翻身術,也翻不過大漠和廟宇。再好的針線,也縫補不了靈魂的出口和人口。
生之微末,死之寂然。
在向上生長中,傷口潰爛,潰爛的還有忠誠的表白。表白給高山湖泊丘陵溝壑,表白給沼澤濕地森林罐隙。
他們囤積口糧和空氣,避開機器的圍困、房屋的擁擠、霧霾的籠罩。
他們承受地球引力帶來的衰老。火山燒不死、洪水淹不沒、狂風吹不倒。
他們沒有選擇的選擇——風餐露宿。
他們唯一的選擇——順從綠意,就像螞蟻鐘情于黑色。
一點黑襯托無限白,一團黑平分秋色。
一片黑,就像天下的烏鴉,其實烏鴉有黑色、有白色,同族是喜鵲,被某種聲音一攪和,天下烏鴉就一般黑了。
他們精通算術,學會觸類旁通。就像蚯蚓,學會在泥土里彎身,就像溪水在激流處拐彎。彎身不等同于卑躬屈膝,拐彎也不約等于左右逢源。
他們給自己翻身打勝仗的機會,在巖石里布陣,在瓦當上宿營。
三十六計——假設、分行和偏愛,僅這一支技法流派,多少英雄走向末路。
好在春風吹又生。他們重振旗鼓,再塑山河。他們“吃一塹,長一智”,抱團成長。
山河有山河的活法。活出挺拔的模樣、流淌的姿勢。風雨雷電自己去摔打吧!而草活得灑脫自如,倒下也要站成草的模樣,守護大麥和雨水。
大麥有大麥的哀傷,雨水有雨水的落寞。它們懂得金屬的光澤,懂得果實也有出賣主人的招數。遭人唾棄的稗子,提心吊膽,也不忘補給天下空蕩蕩的糧倉。
他們不需仰視這個世界,低頭是為了內省。遠方,即在腳下的青石板上。
在月光灑遍的地方,他們傾聽高山流水之音,解讀霓虹晚霞之意。
他們像漫天的星星,有姣好的眉。
視線紡出的織物——大地堅實的毯——
覆蓋貧瘠、喑啞和流沙。
他們不懂哲學。他們想請哲學垂下睫毛,回答他們心中一個永恒的哲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