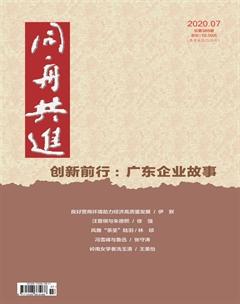風雅“茶圣”陸羽
林碩

智積與“茶禪一味”
陸羽乃唐代復州竟陵(今湖北省天門市)人士,歷經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以“茶圣”之名著稱于世,影響力獨步古今。
對于陸羽的記載,最完整、最詳實、最權威者首推《陸文學自傳》。斯文乃陸羽親自執筆,落款時間為“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由是可知,此篇寫就之際,歲在唐上元二年(761),肅宗李亨執政時期;是年,陸羽29歲,隱逸于苕溪(今浙江省湖州市)山林之間。文章題名系后人所加,因陸氏曾在代宗朝詔拜“太子文學”,故以“陸文學”稱之。陸羽能從輾轉飄零的孤雁,成為天子的座上賓,再到名滿天下的“茶圣”,與其早年經歷息息相關。
按照《陸文學自傳》所述:陸羽“三歲惸露”(惸讀qióng,“惸露”含憂患、煢獨、孑然一身之意——編者注),淪為孤兒,頓失憑依,所幸在竟陵西湖之濱得遇龍蓋寺(今湖北天門西塔寺)方丈智積禪師,收養撫育。陸羽能成為一代“茶圣”,與恩師智積的教誨密不可分。禪師平素不僅精研佛法,且深諳茶道,曾于御前盛贊陸羽茶藝精湛,上演了“智積品茗識陸羽”的佳話,傳誦至今。
到陸羽9歲之時,智積便“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對他寄予厚望。讓禪師意外的是,自幼失孤的陸羽,心中始終懷有孝道。雖然身在莊嚴佛門,卻心系“儒者之孝”,愿習“孔氏之文”,結果是雙方各持己見。若干年后,陸羽回憶彼時情景,寫道:“(積公)執釋典不屈,予執儒典不屈”,相持不下。為了考察陸羽,智積禪師命其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墻,還在西湖之濱牧牛一百二十蹄,以試其心。繁重的勞動并未讓陸羽改變初衷:缺少紙筆,他便以竹畫牛背練字;偶得張衡的《南都賦》,自己縱然不識其字,仍模仿學堂的青衿小兒,正襟危坐,假裝誦讀。最終,智積禪師被陸羽的向學之心打動,決定“從爾所欲”,聽之任之。
少年陸羽在佛門凈土的生活經歷,尤其是智積禪師將釋教“茶禪一味”的義理傾囊相授,對其畢生的茶道修行產生了重要影響。
所謂“茶禪一味”,可追溯到中國禪宗始祖菩提達摩。南朝中期,南天竺(今印度南部)高僧達摩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賚衣缽浮海而來”,在廣州南海郡的珠江岸邊登陸。如今在廣州市荔灣區下九路西來正街,尚有一通“西來古岸”的石碑,另有“西來庵(今華林寺)”矗立在側。
達摩抵華后,因其與篤信佛教的梁武帝蕭衍相談不契,遂離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一葦渡江”,來到北魏境內的少林寺,在嵩山五乳峰盤膝靜坐。在面壁參禪的歲月里,倦意時時侵擾。為了掃除困意,達摩割下眼瞼以保持清醒。不意,眼瞼落地后竟生根發芽,長成茶樹。此后,達摩每逢疲憊之時,便摘食其葉,驅趕倦意,提神醒腦。這便是日本學者認同的茶葉起源——達摩禪定說。實際上,中國漢代結集而成的《神農本草經》中,業已出現“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記載。因此,茶葉起源于達摩的說法并不成立,但釋教與茶道結有不解之緣卻是不爭的事實。
以茶參禪、以禪修身,最終達到妙悟之境地,乃是“茶禪一味”的重要體現。唐代寺院都設有茶寮作為僧眾精研佛理、品茗交流的場所,陸羽的恩師智積禪師本人便是茶道大家。是故,成長在寺廟環境中的陸羽,對此感悟頗深,也將禪宗恬淡清凈的思想融入到茶道之中。
唐玄宗天寶之世,安祿山禍亂中原。陸鴻漸只身遠赴浙江結廬隱居,在山溪、苕花之間,辨水煮茶,不問塵事,“自曙達暮,至日黑盡興”,對前人的飲茶方式進行歸納。最初,人們直接使用“生葉”混煮羹飲,制作方式如同烹粥,即“烹茶法”。對此,晚唐文學家皮日休認為“與夫瀹(讀yuè,意為煮——編者注)蔬而啜者無異也”。直到陸羽出現,情況為之一變,他對前秦至唐代的茶事進行了梳理、勘誤,“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制定了飲茶的各項細則,并編纂了歷史上第一部茶文化百科全書——《茶經》。
在陸羽看來,對茶葉進行加工煎煮,需先將茶餅烤炙、碾細,繼而投入水中,整個過程需遵循“三沸原則”。“初沸”在水沸如魚目之時,加以鹽、姜等佐料,調而飲之。這種飲用方式被稱為“調飲法”,屬于“烹茶法”之遺意。而“二沸”則在“涌泉連珠”之際,舀出一瓢水備用,繼而投入茶末。待到翻波鼓浪之刻,表示“三沸”來臨,將備用之水倒入止沸,便大功告成,可以分酌茶湯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陸羽之前,《爾雅》以及《神農本草經》等典籍中并無“茶”字,均作“荼”字。至陸羽寫就《茶經》,改“荼”為“茶”,始被認可。盡管后世對陸羽所著《茶經》奉為圭臬,但其“茶圣”地位的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主要與李季卿、唐代宗以及智積禪師等人有關。
“茶圣”盛名傳御前
唐寶應元年(762),代宗李豫繼位,次年,安史之亂宣告平定。唐廣德二年(764),上諭派遣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李季卿巡撫河南、江淮等地,整肅朝綱,尋訪賢才。
李季卿久仰陸羽之名,相邀一敘,坐而論茶,言道:“陸君善茶,蓋天下聞”,而揚子江的“南零水”亦甚殊絕,有“天下第一水”之稱。今日陸君與“南零水”二妙相逢,可謂千載一遇。于是,李季卿命人去取南零之水。及還,但見陸羽以勺揚水,道:“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者。”取水人抗辯:取水之時,“棹舟深入”,數百人可以作證,怎能說是臨岸之水?陸羽并不與他爭論,使人傾倒盆水,至半遽止,以勺揚之觀瞧,認定此刻盆中之水系“南零者矣”。取水人蹶然大駭,支支吾吾地說出原委:由于水波蕩漾,取來之水已經舟蕩覆半。為免責罰,遂挹岸水倒入盆中,企圖濫竽充數。
當是時,李季卿及舉座賓客驚為神人,眼見陸羽對烹茶之水有如此研究,當即請教水之優劣。鴻漸遂將水品20種娓娓道來:“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第一;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李氏如獲至寶,命人一字不漏地記下。事見張又新的《煎茶水記》,而溫庭筠所撰《采茶錄》亦有所載。
然而,在封演所著的《封氏見聞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版本的“李、陸之會”,結果與《煎茶水記》大相徑庭。據封氏所述:李公途經臨淮之際,有名為常伯熊者,搶先前一步前往獻茶。此人不但將陸羽的《茶經》倒背如流,欺世盜名,更“別出心裁”,衣著富麗堂皇,手執各式名貴茶具,迷惑世人,卻博得了李季卿贊賞。待到陸羽前來,李公見其身穿粗布衣裳,與頭戴烏紗、身披黃衫的常氏形成鮮明對比,竟不屑一顧,指使小廝用30文錢打發陸羽。
筆者認為,張又新的記載準確性更高。須知修縣(今河北省衡水市景縣)封氏在南北朝時期乃河北鉅族,至隋唐仍為朝廷肱股之臣,家學淵深,名重一時,絕非平庸之輩。問題的關鍵在于,《封氏見聞錄》是封演對唐代及前代文人士大夫軼事的小說匯編。既然是筆記小說,其間就難免夾雜道聽途說之辭,真實度大打折扣。另外,溫庭筠在《采茶錄》中亦記述李季卿素知陸羽大名,二者“有傾蓋之歡”,印證了張又新所言非虛。
除了“李、陸之會”,唐代宗亦曾召陸羽至駕前侍茶。如此寶貴的機會,有賴于從小撫養陸羽長大的智積禪師引薦。代宗李豫與德宗李適,父子二人皆以愛茶著稱,前者更設立了歷史上第一座“貢茶院”,專供皇室品茗之用。
相傳,唐代宗素仰智積之名,召其入宮共論茶道,并遣大內御用茶師,甄選上好茶葉煎出香茗奉上。豈料,禪師只吃了一口,便將茶擱置,不再飲用。代宗知其事出有因,詢問其故。答曰:老僧平日所飲之茶,皆是小徒陸羽煎制。陛下若飲過陸羽之茶,必定如老朽一般,感覺眼前這盞茶索然無味。代宗聞聽此言,將信將疑,遂向禪師求得陸羽下落,得知鴻漸在苕溪隱居,即刻派左右飛馬前往杼山,傳旨召見。
陸羽隨來使入宮覲見天子,奉上自己精心煎制的清明茶——顧渚紫筍。代宗飲后龍顏大悅,命人將香茗送與別居他室的智積,試探其反應。禪師捧杯在手,細嗅其香,將茶一飲而盡,飲罷,淡淡地說了一句:“漸兒何在?”代宗聞聽贊嘆不已。智積禪師撫掌大笑:“唯漸兒可煮此茶”。由是,陸羽在御前盤桓許久。皇帝一邊品嘗顧渚紫筍,一邊聽“茶圣”講述烹茶之法、鑒茶之道。
唐代宗設立了史上第一座貢茶院,亦是受陸羽的影響,才會把院址選定在顧渚紫筍的產地——浙江省長興縣顧渚山旁,最上等的紫筍茶被用于祭祀宗廟。閱遍煎茶名士,嘗盡天下香茗的一國之君,能被陸羽的茶藝所折服,可見鴻漸對茶道的精研程度,在代宗朝即已傲視群雄。
“智積品茗識陸羽”的典故流傳甚廣,一方面折射出陸羽技藝爐火純青,遠超宮中茶師;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與恩師智積并未因少年之時的“儒釋分歧”反目,仍保持著密切聯系,正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否則,禪師也不會為陸羽創造御前獻茶之機;而陸羽亦在《陸文學自傳》尊稱智積為“積公”,敬重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縱然師父將陸羽引薦給代宗,但他仍心系歸隱林泉,選擇離開長安返回山溪之間,繼續采茶、煎茶,探究茶之真諦。正如其在《茶歌》詩中所寫“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
陸羽真容與“陸、李之情”
通過梳理史料,辨析真偽,原本散見于不同文獻中的陸羽事跡逐漸清晰起來,唯獨陸羽的外貌特征不甚明朗。據《陸文學自傳》所載,陸羽自述“有仲宣、孟陽之貌陋”。“仲宣”即后漢三國時期的王粲,名冠“建安七子”,竟因丑陋被荊州牧劉表嫌棄,有志難舒。“孟陽”則是“三張”之一——張載的表字。晉書·張載傳》中記載其人因相貌丑悴,外出遭到頑童群起攻之,留下了“投石滿載”的典故。不過,王粲、張載雖相貌平平,卻俱以其才華留名青史。陸羽以仲宣、孟陽自比,果真是認定自己相貌奇丑,抑或是慨嘆自己的才華不遜于王、張二公,也未可知。
欲廓清這樁“歷史懸案”,還要將《陸文學自傳》中的描寫與出土文物相互印證。中國國家博物館庋藏有一尊五代時期的陸羽白瓷像,其時距陸羽去世不過百余年,為后人探尋“茶圣”真容提供了寶貴的考古依據。這尊白釉黑彩陸羽瓷像系坐姿,高約10厘米。陸羽為束發戴冠形象,面部五官清晰。眉梢下垂,眼睛較小,鼻梁有些塌陷。瓷人身穿交領連綴衣,腰間有襞積。足穿系帶布襪,呈盤腿趺坐狀。雙手于胸前微曲,展開一卷《茶經》。如此面容,雖未到奇丑無比的境地,卻也無半分俊朗之感,基本符合“仲宣”“孟陽”之貌。據傳,此尊陸羽像出土于河北唐縣,同批出土的明器還有茶臼、茶瓶(點茶用具)、渣斗(盛放茶滓)、茶鍑以及煎茶所用風爐。“茶圣”像作為陪葬品出現,足見最遲殘唐五代之際,民間業已出現了“茶圣”崇拜。
不過,“茶圣”始終是凡人,亦有七情六欲,其與“大才女”李季蘭的故事,至今為人津津樂道。李季蘭,本名李冶,表字季蘭,以字行之,與薛濤、魚玄機齊名。因李氏桑梓烏程,與陸羽結廬之地相去不遠,二人以文相交,時常往來,故《唐才子傳》記載她與陸羽“意甚相得”。不僅如此,在李季蘭的代表作中,尚有一首詩是以陸羽為題所作,名為《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昔去繁霜月,今來苦霧時。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強勸陶家酒,還吟謝客詩。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詩中的“欲語淚先垂”“此外更何之”等句,營造出一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若非相知之人,斷難感悟,足見鴻漸、季蘭相交至深。
然而,陸、李之情卻被動蕩的政局打斷。唐德宗建中年間,朝廷波折再起。天子為涇源亂軍所迫,出逃奉天(今陜西省乾縣),釀成“奉天之難”。叛軍占據長安后,擁立朱沘為帝,改國號為“大秦”。彼時的李季蘭恰在長安城中,被迫為朱氏“獻詩稱賀”,以求自保。德宗回鑾之后,追論季蘭之罪,將其亂棍擊殺,令人唏噓。
或許是出于對陸、李之情的惋惜,坊間流傳一種說法:二人幼年就在竟陵相識。持此論者唯一的依據是:陸羽又字“季疵”,與季蘭的表字相似,據此斷定陸羽幼時曾被李季蘭家收為養子,彼此有青梅竹馬之誼。然而,這種推斷缺乏史料支持,無論在《陸文學自傳》或其它文獻中,均未載其事。況且,表字相似之人,比比皆是,籍此斷定親緣關系,實不可取。李季蘭與陸羽是在湖州相交相知,并在“茶圣”恬淡風雅的一生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陸羽在世之時,已有“茶仙”之譽,“始作俑者”是其多年摯友、唐代杰出詩人、位列“大歷十才子”之一的耿湋。耿氏對于精研茶道、舉止風雅的陸羽甚為服膺,在《連句多暇贈陸三山人》詩中盛贊他“一生為墨客,幾世作茶仙”。以此為發端,陸羽乃“茶中仙人”的美譽流布開來。
及陸羽登遐極樂,其故交周愿偶至龍蓋寺,盤桓西塔之下,緬懷鴻漸,稱頌其為一代“茶圣”。唐元和十一年(816),周愿被唐憲宗李純委以竟陵刺史之任,成為陸羽桑梓的父母官。因二人曾在“南海連率”——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李復幕府中贊襄共事,以兄弟相稱。目睹西塔猶在,斯人已逝,周愿提筆寫下《牧守竟陵因游西塔著三感說》,追憶鴻漸昔日點滴:“方口諤諤,坐能諧謔,世無奈何,文行如軻”,可謂“百氏之典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游”,實為“圣人也”。
待到宋代,“蘇門六學士”之一的陳師道又指出陸羽編纂《茶經》,“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受惠無窮,“誠有功于茶者也”“又有功于人者也”。甚至連北方的回鶻可汗亦久慕“茶圣”大名,專程派使者前往朝廷求購《茶經》,愿以千匹駿馬相易。對缺少良馬的唐政府而言,自是求之不得,即刻遣人搜訪善本。作為陸羽同鄉兼擁躉的皮日休知悉此事,遂將家藏善本奉上,令回鶻人滿意而歸。自此以后,茶經》之名更盛,無遠弗屆。
在耿、周、陳等人的贊許聲中,陸羽逐漸由精研茶理的“茶仙”升格為恩澤百世的“茶圣”,供奉、崇拜陸氏之風俗亦逐漸興起。最初,民間的“茶圣”信仰主要流傳在茶商群體之中。茶商、茶肆的主人們往往會在茶灶旁擺放陸羽像,以求財源廣進、日進斗金。祭祀之時,將茶水恭敬地呈放在“茶圣”像面前,附以干鮮果品。
然而,若生意不甚順利,茶商們便采取另一種祭祀方式——以沸水自上而下地沖淋“茶圣”像。此種獨特手法,外人很難理解,甚至誤以為這是在懲罰陸羽不靈驗。其實,這種類似“醍醐灌頂”的祭祀儀式,與陸羽早年的佛門經歷有關。鴻漸在編著《茶經》時,潛移默化地將釋教思想融入茶道之中,更將茶水的功效與醍醐相提并論,認為“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相抗衡也”,因而,后人在祭祀陸羽之時,采用醍醐灌頂之法,實濫觴于此。是故,信眾以“沸水澆灌茶圣像”屬于祭祀行為,是出于虔誠與恭敬,希望借助沸水激發其靈性,澤被一方。
(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