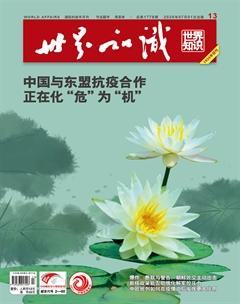優勢還是均衡:美國對華戰略的妄思
胡欣

當前美國國內的對華共識,已毫不掩飾地向冷戰式的遏制與對抗快速滑落。特朗普癲狂式的執政風格雖然對這一趨勢起到了加速作用,但歸根到底,是中美兩個大國走到了角色深刻轉型、規則破中求立、力量態勢生變、戰略認知起伏的重要時期。從美國的角度看,對華采取戰爭手段顯然是最差的選擇,因為它或許能停滯中國的民族復興,但代價也必然巨大,甚至導致美國失去維系70多年的霸權優勢。在思考如何以相對小的代價阻撓中國的崛起時,制衡策略成為重要考量。
太平洋的確很大,大到歷史上從未有哪個大國真正在這一區域內操控均勢。19世紀之前,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主要局限于亞歐大陸東側,即便彼時的日本,其戰略也基本上是“由海向陸”的跟隨或侵略。直到日本真正崛起為世界強國后,在軍國主義野心驅動下,試圖獨霸西太平洋及太平洋中部。最終,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依托強大軍力扭轉局勢。
此后,美國的太平洋優勢地位如日中天,尋求均勢對其而言可謂一種“謙卑的妥協”。直到上世紀70年代,美國被迫拉攏中國制衡蘇聯,西太平洋地區形成了局部的大三角關系。冷戰結束后,美國尋求適度戰略收縮,“離岸平衡”的觀點一度興起,核心是要美國從地區矛盾沖突中解脫出來,擺脫“世界警長”的負擔,借助必要的武力威懾、同盟合作和外交手段,對其他大國進行力量平衡。這一策略之所以對中國未能奏效,在于中國發展速度之快令美國始料不及。中國影響力的增長讓美國原本設想的“二元劃分”變得模糊,不僅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積極開展全面合作,美國的傳統盟友也從對華合作中獲得重要收益,這無疑淡化了制衡中國的力量基礎和戰略共識。
中國并不以硬核“恐怖軍力”立身。中國最讓美國擔憂的,是在制度學習和創新方面的活力。而在全球體系中,中國的影響力已遠遠超過美國的上一個對手蘇聯。“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等都是中國從體系中學習、在體系中改革的范例成果,無論美國如何對其污名化,都無法阻止更多國家的期待與參與,這也表明中國在國際體系的演進中已掌握一定話語權,甚至正在掌握局部規則的制定權,這給美國試圖以最小成本維持戰后體系運行的初衷帶來不小的挑戰。
正是在這樣的顧慮下,美國的印太戰略開始浮現。從本質上講,印太戰略是一個更大地緣范圍的平衡戰略,是在“重返亞洲”流于形式后的另一場賭博。它在與日、澳兩大盟國支柱的基礎上,引入印度這股新勢力,構建海陸兩翼圍堵中國的新布局。美國決策高層不會接受中國這樣的“意識形態異己”與自己平起平坐,至少在當前依然保持對華總體優勢的時候。不過,即便美日印澳四國結成了反華陣線,該地區許多國家并不會輕易選擇陣營,東南亞國家就對成為美國的反華馬前卒極為警惕。亞洲國家大多對西方列強的各種手腕懷有戒心,而中國始終堅持和平主義的政策取向,也促成不少國家選擇與中國求同存異、共同發展。失去了西太平洋地區廣大國家的支持,美國的反華戰略就很難找到對中國周邊安全謀略布局進行滲透瓦解的突破口。
要想策動更多亞太國家加入美國對中國的制衡,美國必須能夠替代中國向這些國家提供以共同發展為特點的公共產品,而不是“美國優先”式的索取。全面對抗色彩的制衡也意味著亞太國家要明確地選邊站隊,形成相對固化的戰略同盟,而這對于那些通過大國平衡外交贏得收益的國家是很難做出的抉擇。中國并不想在西太平洋地區走上大國軍事對抗的老路,但美國執意用零和游戲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發展,將瓦解中國的競爭力作為解決雙方矛盾分歧的根本方式,這種思維才最有可能將中美推入“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