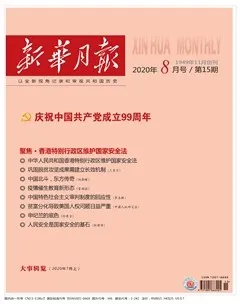講述海外新疆人的故事
趙嫣
“這是一部海外華人奮斗史。”庫(kù)爾班江·賽買提對(duì)記者說(shuō)。
他的新作《我從中國(guó)來(lái)——海外新疆人》剛剛面世不久,厚厚的一本書,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封面上,作者庫(kù)爾班江微微頷首,眼神坦蕩。
這是庫(kù)爾班江“我從新疆來(lái)三部曲”(《我從新疆來(lái)》《我到新疆去》《我從中國(guó)來(lái)》)的最后一部作品。作者自2016年7月起,歷時(shí)3年,走訪了20多個(gè)國(guó)家,采訪、記錄了200多位在海外生活的新疆人的故事,最終挑選出其中70多個(gè)故事編寫成書。
“海外華人奮斗史”
《我從中國(guó)來(lái)——海外新疆人》一書的開篇講述了一對(duì)老人的故事。陳世義老人已經(jīng)90多歲,壯年時(shí)期在新疆博樂(lè)度過(guò)了20多年的時(shí)光,60多歲的時(shí)候跟著兒子舉家來(lái)到美國(guó),繼續(xù)學(xué)業(yè),81歲時(shí)拿到了博士學(xué)位。老人的太太70多歲時(shí)開始在當(dāng)?shù)氐姆稍幑ぷ鳎恢钡?6歲才退休。老人把自己的退休金全部捐給了博樂(lè)四中,希望為新疆作點(diǎn)貢獻(xiàn)。老人說(shuō):“我們來(lái)美國(guó)20多年了,但還是一顆中國(guó)心。”
在美國(guó)做石油勘探工作的艾拜都拉說(shuō):“一個(gè)人看得越多、學(xué)得越多、知道得越多,那么他的眼界、見識(shí)、處世之道就會(huì)跟別人有很大區(qū)別,這種人在北上廣有很多,在阿圖什、伊犁、和田同樣有很多。那些不滿足于眼前的茍且,想出去看看更廣闊的世界并為此努力的人不在少數(shù)。”
從小看著天山長(zhǎng)大的女孩月亮是一名箜篌演奏者。2012年,她把鋼琴賣掉,買了一張飛往紐約的機(jī)票。幾年來(lái),她曾在聯(lián)合國(guó)總部、林肯音樂(lè)中心等地為外國(guó)觀眾彈奏箜篌。每當(dāng)想家的時(shí)候,她會(huì)坐在陽(yáng)臺(tái)上唱很多新疆歌曲。她說(shuō),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讓箜篌再度流行。
一篇篇看下來(lái),每個(gè)故事都簡(jiǎn)單樸實(shí),卻富有能量和沖擊力。他們都是普普通通的新疆兒女,身上有著敢想、敢做、能闖、能吃苦的拼搏精神,最終在海外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白巖松在《我從中國(guó)來(lái)——海外新疆人》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溝通與了解,永遠(yuǎn)是這個(gè)世界上最好的橋……這本書中的訪談對(duì)象都是在國(guó)外,但恰恰在他們的故事當(dāng)中,新疆又一次變得非常清晰和讓人想念。”
抹掉標(biāo)簽
5年的時(shí)間里,庫(kù)爾班江實(shí)現(xiàn)了自己對(duì)于完成3本書、3部紀(jì)錄片的承諾。
他說(shuō),《我到新疆去》這本書想表達(dá)的是,新疆沒(méi)有所謂“外地人”,這里是所有人共同的家園。講述所有熱愛(ài)新疆的人的故事,是因?yàn)樗麄冏寧?kù)爾班江更加了解自己的家鄉(xiāng),而新疆的發(fā)展也離不開在新疆生活的這一群人,這是40多個(gè)民族的故事。
對(duì)于自己的第三本書《我從中國(guó)來(lái)——海外新疆人》,庫(kù)爾班江說(shuō),他希望從新疆人的角度講述中國(guó)人走向世界的故事。書中的主人公屬于漢族、維吾爾族、回族等9個(gè)民族。但在庫(kù)爾班江的故事中,所有人的姓氏都沒(méi)有出現(xiàn),他說(shuō)希望以這樣的方式去掉民族的標(biāo)簽。
這本書中故事的主人公來(lái)自各行各業(yè),有聯(lián)合國(guó)的工作人員、運(yùn)動(dòng)員、醫(yī)生、教授、作家、商人等等。庫(kù)爾班江希望通過(guò)他們來(lái)講述中國(guó)人在世界各個(gè)角落為人類發(fā)展作出的貢獻(xiàn),而不希望強(qiáng)調(diào)任何單一的民族,“如果一定要加上一個(gè)標(biāo)簽的話,那就是:他們是新疆人,更是中國(guó)人。”
庫(kù)爾班江正在拍攝中的第三部紀(jì)錄片《新疆滋味》,講述的依然是融合的故事——通過(guò)美食的視角。他說(shuō),美食的融合,是最為吸引人的,也是為大家所公認(rèn)的民族融合的例證。
新疆有一道有名的菜——大盤雞,這道做法繁多、口味鮮明、帶有濃郁邊疆特色的菜肴至少融合了4個(gè)地域或民族的智慧:雞肉的炒法來(lái)自湖南辣子雞,土豆和俄羅斯有關(guān),皮帶面是哈薩克族提供的,大盤則帶有鮮明的維吾爾族特色。
庫(kù)爾班江希望用潛移默化的方式講述融合,在他看來(lái),這種融合早已滲入到新疆“內(nèi)高班”學(xué)生的日日夜夜中,早已體現(xiàn)在被很多地方民眾喜愛(ài)的一粥一飯中,早已刻畫在那些在世界各個(gè)角落里作出貢獻(xiàn)、收獲成功、勤奮努力的新疆人的身影上。
用今天的故事講明天的愿望
庫(kù)爾班江在《我從中國(guó)來(lái)——海外新疆人》一書的扉頁(yè)上寫道:“越努力越幸運(yùn),越勇敢越能有改變!”與其說(shuō)這句話是送給讀者的,不如說(shuō)是送給他自己聽的。
寫作這樣一本書,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單槍匹馬在世界范圍內(nèi)尋找采訪對(duì)象、長(zhǎng)途奔波所面臨的種種未知、獨(dú)立支撐所有資金來(lái)源的拮據(jù)和困窘……所有難題,庫(kù)爾班江并未細(xì)說(shuō),他只是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困難不是問(wèn)題,總能解決。”他說(shuō),雖然每個(gè)階段都有難題,但辦法總是有的,“只要初心未改,出發(fā)點(diǎn)沒(méi)有偏離,所有人都會(huì)用一切方式幫助你。這么多年來(lái),很多人看到了我的堅(jiān)持。”
“永遠(yuǎn)要把學(xué)習(xí)放到第一位,不僅是專業(yè)學(xué)習(xí),還有在社會(huì)和生活上的學(xué)習(xí)。如何融入一個(gè)國(guó)家和一種文化,這也需要學(xué)習(xí)。”這是《我從中國(guó)來(lái)——海外新疆人》書中一位主人公的話,也是作者庫(kù)爾班江的心聲。
對(duì)于教育、對(duì)于學(xué)習(xí)、對(duì)于成長(zhǎng),庫(kù)爾班江似乎極為在意,這和他的經(jīng)歷、父親對(duì)他從小的教育息息相關(guān)。
庫(kù)爾班江出生、成長(zhǎng)在新疆和田,他的父親是阿圖什人。阿圖什,即為古國(guó)疏勒的國(guó)都。疏勒地處天山山脈、帕米爾高原、塔里木盆地的中間地帶,扼守險(xiǎn)要,西連費(fèi)爾干納盆地,通向撒馬爾罕,是古絲綢之路上駝隊(duì)的必經(jīng)之路。阿圖什是迎接來(lái)自中亞地區(qū)駝隊(duì)的第一個(gè)驛站,更是送走來(lái)往使節(jié)、商人和朝圣者的最后綠洲,這里隨之貿(mào)易興起、商賈云集。
庫(kù)爾班江告訴記者,很多阿圖什男孩子自小隨駝隊(duì)經(jīng)商,代代相傳,阿圖什人重視教育,重視商業(yè),以至于被稱為“中國(guó)的猶太人”。他的父親認(rèn)為,家里孩子都要上大學(xué),并希望把孩子都送出新疆,去看世界。
從2006年開始的兩三年時(shí)間里,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校園里有一個(gè)戴著耳機(jī)、“流竄”于各個(gè)課堂的“蹭課大王”被很多學(xué)生和老師熟知,那就是庫(kù)爾班江。不要學(xué)位、不求學(xué)歷,他拿著厚厚一摞整個(gè)學(xué)校的課程表,給自己安排了滿滿當(dāng)當(dāng)?shù)那髮W(xué)日程,度過(guò)了永坐第一排的另類大學(xué)生涯。幾年下來(lái),他和很多老師成了熟悉的朋友。
大學(xué)之后,庫(kù)爾班江拿起攝像機(jī),參與拍攝了多部央視紀(jì)錄片。后來(lái)紅遍大江南北的《舌尖上的中國(guó)》中關(guān)于切糕等新疆美食的部分,正是出自庫(kù)爾班江。“只要有機(jī)會(huì),我就要去講,去展現(xiàn)和新疆有關(guān)的東西。”他說(shuō),關(guān)于新疆的作品,多年來(lái)都從民族風(fēng)情著手講故事,形成了一個(gè)套路,而他正是想打破這種套路,換一個(gè)方式講新疆,換一個(gè)方式展示這片土地上的人和故事,也進(jìn)而促進(jìn)溝通、深化了解。
庫(kù)爾班江說(shuō),“我講中國(guó)今天的故事,是在表達(dá)我對(duì)明天的愿望。”他希望將這本書的所有版稅收入注入“‘我從新疆來(lái)大學(xué)生圓夢(mèng)計(jì)劃”基金,用以資助從新疆來(lái)的學(xué)生們完成大學(xué)學(xué)業(yè)。
(摘自《環(huán)球》2020年第9期。作者為該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