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新冠聽專家談談傳染病
采寫/方冰青本刊記者 攝影/謝軍


專家名片:陳恩富 碩士研究生,主任醫師,浙江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中華預防醫學會免疫規劃分會委員,浙江省預防醫學會理事、媒介生物學與控制專委會主任委員、流行病學專委會副主任委員。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平靜的生活被疫情打破,公眾忽然意識到傳染病的風險從未消失。新中國的傳染病預防控制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的傳染病風險?面對已知和未知的傳染病,普通人又該如何保護自己?為此,本刊記者專門采訪了浙江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陳恩富主任醫師。
新中國的歷史也是與傳染病斗爭的歷史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被定義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以來,國人與傳染病的斗爭從未停止。“比如說鼠疫,解放前后,我國的鼠疫非常嚴重,尤其是東北地區。”陳恩富介紹,控制及消除鼠疫也成為當時防疫工作者的主要目標,“在浙江,還曾經專門有一支‘鼠防大隊’開展鼠疫防治工作。”50、60 年代,血吸蟲病肆虐,遍及上海、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12個省市,患者約一千萬人,約一億人受到感染威脅。1958年6月30日,聽聞江西余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消息,毛澤東主席欣然寫下兩首著名的七律詩《送瘟神》,以表達心中的激動和感慨。這個時期,麻疹、霍亂等也流行甚廣,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戰亂、經濟和衛生水平還不發達,造成了傳染病的大流行。1949年開始貫徹的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和1952年開始的愛國衛生運動,為改善生產生活環境、控制傳染病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88年的上海甲肝大流行至今還在許多人的記憶里,而21世紀以來,2003年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和2009年的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也曾經對生產生活產生過重大影響。陳恩富表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在傳染病預防過程中出現了多種疫苗,治療環節中出現了抗生素之后,一些嚴重威脅兒童生命健康的傳染病得到了控制,嬰幼兒的死亡率大大下降,人均壽命顯著提高。“因此20世紀80年代,我國提出了衛生工作重點從傳染病向慢性病的轉移,但與此同時,一些新發傳染病也在不斷出現并造成了新的威脅,最典型的就是艾滋病,因此,我們目前的衛生工作還是強調傳染病和慢性病并重。”
在預防傳染性疾病中,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及其前身衛生防疫站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國在成立之初就積極推廣衛生防疫建設,“防疫站”成為許多人耳熟能詳的名字,當時,預防和控制傳染病就是防疫站最重要的職責。“20世紀70、80 年代,‘防疫站’前加上了‘衛生’兩個字,同時為適應當時需求,工作職責進一步擴大,增加了對食品衛生、職業病等相關疾病影響因素的管理。20世紀90年代,疾控機構與衛生監督機構分離,疾控中心成為專門提供疾病預防控制技術和服務的單位。”陳恩富說道。
傳染病多有季節性同途徑傳染病有相似預防措施
此次疫情中,新冠肺炎被列為乙類傳染病,按照甲類傳染病進行管理。那么,對某一種傳染病進行分類的依據是什么?陳恩富解釋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簡稱《傳染病防治法》)對傳染病采取分類管理的原則,根據傳染病流行和危害的程度來分類,流行范圍越廣,病死率越高,流行速度越快,在分類中就越靠前。我國目前的甲類傳染病共2種,分別是鼠疫和霍亂,都是曾經發生過多次世界大流行的烈性傳染病。常見的乙類傳染病則包括傷寒、艾滋病、流行性腦膜炎等26種。有人質疑艾滋病患病人數龐大,為什么被劃分到乙類傳染病而不是甲類傳染病,這是因為它主要通過性行為、血液和母嬰傳播,傳播速度并沒有甲類那么快。至于丙類傳染病則是一些多發病,包括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等等。”
除了按照《傳染病防治法》中的分類,傳染病還可以從專業技術角度分類。“首先是病源的角度,包括細菌性傳染病、病毒性傳染病和其他病原體性傳染病。其次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傳播途徑的角度,可以將傳染病分為呼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蟲媒傳染病、性傳播傳染病、接觸性傳染病等。要強調的是,某一種傳染病可能不止有一種傳播途徑。此外,還可以從有無防控措施來區分,如果有相應的疫苗就可以提前預防。”
那么,不同途徑的傳染病又該分別如何預防呢?有沒有一些通用的預防措施呢?陳恩富表示,經典的傳染病理論認為,預防控制一種傳染病可以從控制(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播鏈和保護易感人群三個環節入手。例如預防腸道傳染病,可以從切斷傳播途徑入手,避免“病從口入”,就應當做到保持飲食、飲水的衛生,同時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例如勤洗手、不吃生冷食物等。而呼吸道傳染病,想要切斷它的傳播鏈相對比較困難,所以一般是從傳染源管理(隔離)和保護易感人群的角度著手,因此許多疫苗也是針對預防呼吸道傳染病的,例如麻疹、百日咳、白喉等疫苗。另外,預防蟲媒傳染病例如登革熱等,我們就可以通過控制蟲媒密度來控制疾病。”
此外,大部分的傳染病都有季節性,在不同季節可提前采取有針對性的預防措施。“呼吸道傳染病,一般在冬春季節高發,蟲媒傳染病主要在夏季高發。在腸道傳染病中,細菌性的腸道傳染病在夏季高發,而一些病毒性的腸道傳染病如諾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容易在冬春季高發,這是因為細菌和病毒的活性恰好相反,細菌更容易在溫暖的環境中繁殖,而病毒一般來說不耐熱。另外還有一些傳染病沒有季節性之分,例如血液傳染病和性接觸傳染病,包括乙肝、艾滋病等等。”
疫苗是預防控制傳染病最有效最經濟的手段之一,這一點是公認的。但在不少人印象中,疫苗接種的對象是兒童,成年人則不需要接種。陳恩富表示,這種觀念的形成和我國預防接種的特定歷史背景有關。“在60、70年代,疫苗接種主要面向兒童,所以至今還有不少人認為只有小孩才能打疫苗,其實這是狹隘的理解。20世紀70、80年代,我國剛開始實行計劃免疫時,講的是4個疫苗防6種(傳染)病,而目前我國已有的疫苗可以預防20多種傳染病。許多疫苗都是面向全人群的,易感人群尤其應該接種。例如流感的易感人群就包括老年人、有慢性基礎疾病的人、醫務人員等。流行性肺炎最主要的易感人群也是老年人,時下不少女性關心的HPV疫苗,接種對象的年齡上限也很高。而目前最受大家關注的新冠肺炎疫苗,如果研制成功,最先應該接種的也是易感人群,比如老年人。因此,大家應該轉變意識,疫苗是面向全人群而不僅僅是兒童的,有條件、有需要的可以及時接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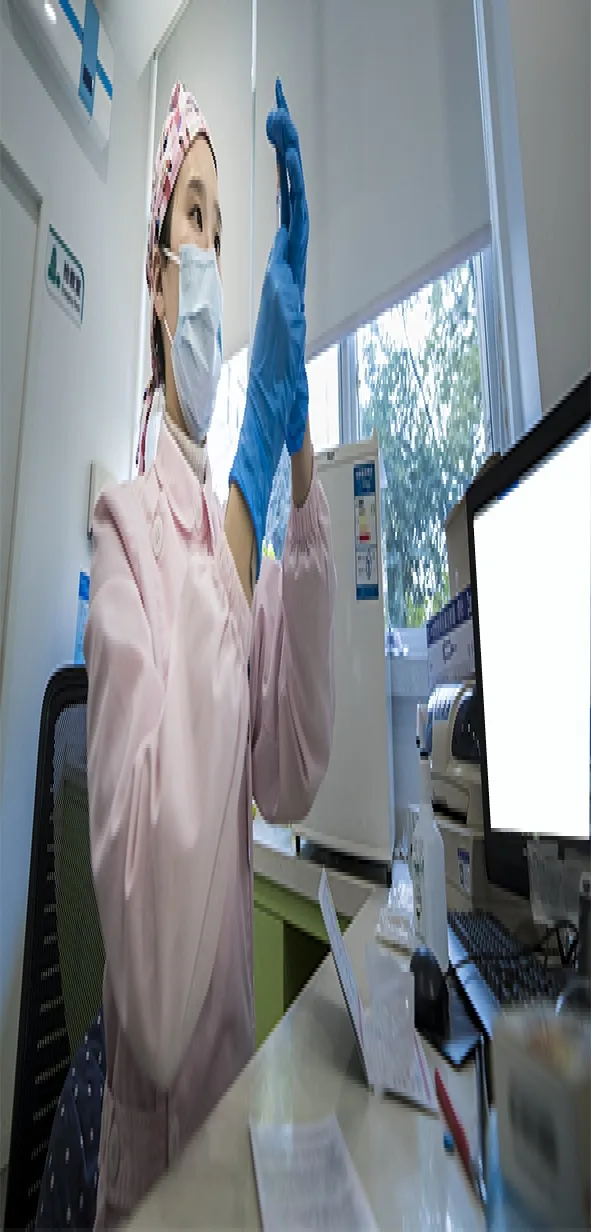
傳染病也在全球化做好個人預防很重要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和區域之間的聯系日趨緊密。全球化為許多國家帶來了經濟利益和巨大的歷史機遇,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傳染病傳播風險。我國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成為世界重要的生產制造大國,面臨的輸入性傳染病風險也不斷上升。
“原本只局限于某一個區域的傳染病可能隨著旅游、經貿等活動,傳播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傳染病。例如2014年,埃博拉病毒導致的疫情就從西非傳到了東非;2016年,寨卡病毒從非洲傳到了太平洋島國,接著到了南美洲,最后走向了全球,浙江省也出現過輸入性病例。有一句話這么說:傳染病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只有一個航班的距離。在一些重大的傳染病疫情中,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幸免,如1981年首次被發現的艾滋病,如今已經遍及全球。因此國際合作就變得十分重要,這也是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在倡導的。”陳恩富說道。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來應對輸入性疫情、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呢?“為預防和控制輸入性傳染病,我國政府建立了3道防線。首先,及時關注世界上重大傳染病的發生,重視入境檢疫。與此同時,有一些傳染病的感染者可能在入境時處于潛伏期,在入境檢疫時沒有被發現,此時就需要啟動第二道防線,這就是一套全面的傳染病識別系統,一方面包括傳染病的快速確診、抗原和抗體的檢測、病原體的培養、分離乃至溯源等,另一方面就是醫院內的監測識別系統。而第三道防線,是一套及時的應急處置、控制管理的系統。”這三道防線缺一不可,牢牢守護著國民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勤洗手”“戴口罩”等出現在宣傳標語上的預防要點深入人心,也受到了許多人的重視。但隨著國內的疫情漸趨平穩,這些疫情期間形成的習慣能否繼續保持,成為日常行為呢?陳恩富強調,個人的傳染病和衛生知識儲備、行為習慣方式對預防傳染病至關重要。
首先,具備基本的傳染病和衛生知識,能幫助我們對傳染病形成科學認識,既不會麻木不仁、無動于衷,也不至于過度恐慌、茫然失措,可以理性看待傳染病,采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其次,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能幫助減少病原侵入人體。拿最常見的洗手來說,“一個簡單的動作,就能夠預防呼吸道疾病、腸道傳染病和某些接觸性的傳染病。”而這幾個月以來大家日常佩戴的口罩不僅能幫助預防新冠病毒肺炎,還能夠防流感和過敏。“未來口罩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化的防護措施。人們在前往人流密集、空氣流通較差的地方,如醫院、車站等,都可以隨身攜帶和佩戴。”此外,分餐制、使用公筷等也有助于預防腸道傳染病;性行為時使用安全套可以幫助預防性傳播疾病。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具備健康知識素養,養成健康文明的生活習慣,才能為個人構筑起牢固的健康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