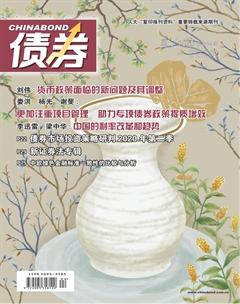利率“換錨”的影響與應對建議
譚海鳴



摘要:根據相關政策安排,2020年3—8月,我國存量浮動利率貸款陸續開展定價基準轉換(即“換錨”)工作。本文基于對美國利率“換錨”過程中的宏觀變化、銀行業變革及微觀主體選擇等進行分析和經驗總結,探討了我國利率“換錨”的過程、背景及銀行業的應對之策,最后為按揭貸款借款人提供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 定價基準轉換? 利差? 資產負債結構
為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高利率傳導效率,推動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2019年8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19年第15號公告,決定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為進一步深化LPR改革,推進存量浮動利率貸款定價基準平穩轉換,12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19年第30號公告,明確“自2020年3月1日起,金融機構應與存量浮動利率貸款客戶就定價基準轉換條款進行協商,將原合同約定的利率定價方式轉換為以LPR為定價基準加點形成(加點可為負值),加點數值在合同剩余期限內固定不變;也可轉換為固定利率”。
根據上述政策安排,2020年3—8月,相關部門將對存量浮動利率貸款陸續開展定價基準轉換(即“換錨”)工作。其中,存量房貸利率如何選擇備受關注。市場上眾多分析認為,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經濟增速趨于放緩,通脹水平也相對溫和,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將呈下行態勢,因此借款人應轉為LPR加點利率。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換錨”的影響最終要通過存貸利差(或稱凈息差)來衡量。當前市場的主流觀點是,銀行利差將隨著LPR下行而收窄。本文基于國際經驗,分析和查證國內銀行業數據,從而為借款人和銀行從業人士進行決策提供參考。
三種“利率錨”
市場化利率主要有三種定價方式:內部基準定價、最優貸款利率加點和市場利率加點。在美國,這三種方法對應的基準利率分別為:銀行內部基準利率(Proprietary Rate)、最優貸款利率(Prime Rate,PR)和倫敦同業拆借利率(LIBOR)/美國國債利率。其中,銀行內部基準定價利率一般通過成本加成法確定,具體包括資金成本、運營成本、頭寸成本和目標利潤率等。PR是由若干報價銀行綜合政策利率和內部成本加成而確定的集合報價。
利率“換錨”的美國經驗
(一)美國利率“換錨”的過程
1.美國利率市場化是一個逐步放開管制的過程
1970—1980年,美國放開部分定期存款利率上限。1980—1986年,美國國會正式公布為期6年逐步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的計劃,并鼓勵存款品種創新。直至2011年,美聯儲才最終取消了對活期存款禁付利息的規定。
2.從“PR利率錨”到“市場利率錨”
從美國經驗來看,PR在設立初期是商業銀行貸款定價的重要參考利率。隨著利率并軌的推進及商業銀行定價能力的提升,“PR利率錨”的作用逐步淡化,最終過渡至完全的“市場利率錨”。在1933年推出時,美國PR由30家銀行報價。20世紀70年代,PR開始盯住90天期商業票據利率。自1994年起,PR固定為“聯邦基金利率+300BP”。現在PR主要被用于中小企業貸款和個人客戶消費貸款定價,大型企業客戶貸款多使用LIBOR和聯邦基金利率作為定價基準。
(二)美國利率“換錨”以來的宏觀變化
利率市場化并不必然意味著利差下行,利差主要受資金供求影響。雖然20世紀80年代至今,美國銀行業的利差總體上是趨于下降的,但是這并不完全是利率市場化的結果。在1986年利率基本市場化之后,美國商業銀行的平均利差先升后降,到1994年達到4.62%的高點,隨后逐步下行至2015年2.98%的低點,之后有所反彈。美國銀行業利差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是經濟增長帶來的資金需求,以及貨幣總量增長帶來的資金供給。當“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的差值較高時,資金供不應求,利差就相對較高,如1994年和2010年(見圖1);反之,利差相對較低,如2001年和2008年。因此,幾十年來美國銀行業利差趨于下降,主要是經濟增長變緩、貨幣發行量增多的結果。即隨著經濟總量的上升,經濟增速趨于下降,此外在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貨幣發行速度受外生沖擊而呈階梯式上升態勢,二者均有壓低利差的作用。
(三)“換錨”之下的美國銀行業資產負債結構變化
1.資產結構經歷了倒“V”形變化,2008年前趨利而動,2008年后注重風險
在1980年利率市場化啟動初期,美國銀行業生息資產的比重為83.8%,2007年上升到88.5%,但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銀行業對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比率要求的提高,2018年生息資產的比重又下降到80%左右。在生息資產中,貸款和投資類資產的比例也呈現倒“V”形變化,但是同業資產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趨勢。相應地,現金類資產的比例則呈現“V”形走勢,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降至2.6%的水平,但危機后又持續上升,2018年已經達到11.6%的水平(見表1)。
貸款作為生息資產的主要部分,其內部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表現出“房貸化”偏好。其中,不動產抵押貸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貸款)的占比在震蕩中上升,從1981年的30%左右上升至2006年的60%左右,然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降至56%,隨后又反彈到2009—2010年的最高水平62%,之后又慢慢回落到2019年的54%左右,呈現出“M”形走勢。出現這一走勢的原因,主要是隨著房地產價格的波動,不動產貸款利率與工商貸款利率的利差呈現出明顯的“M”形波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房地產市場日益繁榮,不動產貸款利率上升速度快于工商貸款利率上升速度;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兩者利差急劇下降,之后伴隨量化寬松而短暫反彈;在2010年見頂后,兩者利差又震蕩下行(見圖2)。
2.負債結構呈現明顯的“付息化”趨勢
付息負債比例從1980年的70.6%,逐步上升到2018年的84.9%。其中,付息存款的比例在2011年允許對活期存款付息后上升了超過10個百分點。另外,隨著金融監管日趨嚴格,美國銀行業的總權益比例也持續上升,到2018年已經達到11.1%(見表2)。
美國銀行業存款結構的變化呈現明顯的“儲蓄化”特征。1982年以前,活期存款和儲蓄存款占比呈下降趨勢,定期存款占比呈上升趨勢,尤其是小額定期存款占比到1982年一度上升至66.8%的高點(見圖3)。然而,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化,尤其是隨著付息支票賬戶(NOW)和貨幣市場存款賬戶(MMDA)的推出,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占比快速下降,儲蓄存款占比持續上升,2019年底已經達到64%。
(四)美國銀行業應對“換錨”的舉措
經過多年的競合,美國商業銀行已經形成三種類型:投行型、綜合型和零售型(互聯網型)。以銀行的利息收入占比為橫軸、凈息差(存貸利差)為縱軸繪制坐標(即“凈息差—利息收入占比”空間坐標系),美國主要的上市銀行大致沿著向右上方傾斜的趨勢線性分布,利息收入占比越高的銀行,其凈息差越高(見圖4)。其中,以道富銀行、紐約梅隆銀行和北方信托為代表的投行型銀行,凈息差最低,利息收入占比也最低;以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富國銀行為代表的綜合型銀行,凈息差和利息收入占比都居中。以第一資本金融公司和西太平洋銀行為代表的本地零售型(互聯網型)銀行,凈息差和利息收入占比最高。
(五)微觀主體的“尋錨之道”:預期和收支匹配
1.利率選擇的“適應性預期效應”
Campell(2006)的研究展示了1985—2002年美國固定利率按揭貸款(FRM)和浮動利率按揭貸款(ARM)的比例情況。在1985年、1987年、1995年和2000年,當30年期固定利率較高且與1年期浮動利率的利差較高時,固定利率按揭貸款比例較低。在其他絕大多數時候,固定利率按揭貸款比例都為70%以上(見圖5)。這體現了一種“適應性預期”,即人們認為當前的利率水平會長期持續下去,因此往往根據當下的利率做決定,而不是基于整個還款期間的利率水平來決策。美國民眾偏愛固定利率貸款,也與按揭再融資非常便利有關系。本文研究發現,95%選擇再融資的借款人都能在4年內達到降低按揭利率的效果,因此如果美國民眾發現之前的固定利率貸款定價偏高,他們中很多人會選擇再融資來降低利率。
2.利率選擇的收支匹配原則
Blacklow等(2010)利用2006—2009年澳大利亞11萬個房屋按揭借款人數據研究了微觀主體的利率選擇。自1989年12月澳大利亞按揭貸款利率創出17.5%的歷史最高值后,就一路震蕩向下,到樣本期開始的2006年1月已經降至7.32%。由于澳大利亞的再融資不如美國便利,借款人更加關注利率中長期向下的走勢,一般都會選擇浮動利率。然而,短周期內澳大利亞處于加息周期,樣本期48個月內有42個月處于利率上行期,這令選擇FRM的借款人比選擇ARM的借款人平均多支付25BP的利率。盡管如此,仍有28%的人選擇FRM。進一步對比發現,家庭凈資產和收入較低的借款人,更傾向于為降低支出風險而選擇FRM。樣本期內選擇FRM的借款人凈資產比選擇ARM的借款人平均低18.3%(10.1萬澳元),月收支凈結余平均低40.6%(1066澳元)。
中國利率“換錨”的過程、背景及應對
(一)中國利率“換錨”的過程
1.中國利率市場化是一個漸進過程
自1993年至今,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歷時27年,其間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5—2016年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等多次考驗,總體上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大額、后小額,先貸款、后存款”的原則,一直在漸進、有序地推進。
2.此次“換錨”的特色是分類施策
根據貸款類型的不同,此次“換錨”有兩種處理方法。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貫徹“房住不炒”的要求,新發放部分要求首套房貸款利率大于或等于相應期限LPR,二套房貸款利率大于或等于相應期限LPR+60BP;存量部分轉換前后實際承擔的利率水平不變。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外的其他貸款利率則由借貸雙方商定。
3.貸款利率期限溢價上升
自2019年8月20日新的LPR形成機制正式運行以來,截至2020年2月20日,1年期LPR已經下調了20BP(其中2020年以來下調10BP),但5年期LPR只下調了10BP(其中2020年以來下調5BP),5年期與1年期LPR的期限溢價上升了10BP。由于工商業貸款和居民消費貸款更多掛鉤1年期LPR,房貸大多掛鉤5年期LPR,因此期限溢價的上升,一方面是對通脹預期提高作出的反應,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分類調控的思路。
4.存款利率市場化穩妥推進
2020年2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相關負責人就《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發布后相關焦點問題接受專訪時表示,存款基準利率是我國利率體系的“壓艙石”,將長期保留。3月,根據《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加強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將對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檔計息等不規范存款“創新”產品進行清理,并將結構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納入自律管理范圍。
(二)中國利率“換錨”的背景
1.中國銀行業利差水平在全球并不高,并且同樣呈下降趨勢
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銀行業利差為2.9%(2018年),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5.4%(2017年)、美國的3.3%(2018年)和印度的3.1%(2017年)。之所以中國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反應如此強烈,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全球主要大國,信貸供不應求。
此外,當前中國銀行業利差水平也呈下降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口徑,2000年和2010年,中國銀行業利差分別為3.6%和3.1%,到2018年降至2.9%。據銀保監會發布的數據,2019年中國銀行業利差為2.2%,比2010年降低了0.3個百分點。
2.近十年來中國銀行業的資產負債結構變化與國際大勢趨同
中國銀行業貸款結構也同樣出現了“房貸化”傾向。包含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和房地產開發貸款在內的房地產貸款占全部人民幣貸款余額的比重,已從2011年的32.6%上升到2019年的48.6%。同期,工商貸款1的占比從55.3%降低到32.2%。
我國銀行業存款結構雖然沒有出現明顯的“儲蓄化”趨勢,但是定期存款占比也出現了“先升后降”的過程。這與美國20世紀80年代利率市場化進程中的經歷類似,背后是金融創新的增加及存款計息方式的多元化。2014年以來,單位定期存款占比的下降,以及單位活期存款和個人儲蓄存款占比的上升(見圖6),在一定程度上就與越來越多的銀行與支付機構、基金管理公司合作推出各種“寶”類現金管理產品有關。這類現金管理產品支取靈活且利率不低于普通定期存款。
(三)中國銀行業應對“換錨”的舉措:根據自身特征專業化發展
在利率市場化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正在朝專業化方向發展。中國主要上市銀行在“凈息差—利息收入占比”空間坐標系中的分布,也一樣呈現向右上方傾斜的線性分布(見圖7)。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及建設銀行的兩項指標居中,與美國主流銀行相似。民生銀行、光大銀行等對公業務占比高,凈息差相對較低。郵儲銀行、蘇農商行2等銀行零售業務占比高,凈息差在行業中最高。其中,比較特殊的是常熟銀行,這是一家以本地零售業務為主的銀行,凈息差在全行業遙遙領先,與美國西太平洋銀行可以比肩。中國也有可以比肩美國第一資本金融公司的銀行,就是尚未上市的微眾銀行,其2017年凈息差高達7%。另外,平安銀行、招商銀行等正在大力推進“零售+金融科技”戰略,其表現明顯異于大部分銀行。
(四)中國按揭貸款借款人:并非只有LPR一個選擇
當前我國利率下行趨勢比較明顯,但是借款人也需要仔細考慮自身資產負債狀況和收支情況,做好資金匹配和期限匹配。對于收入相對較低而又不穩定、還款壓力較大的借款人,可以考慮選擇固定利率。另外,如果將來5年期LPR下行較多,按固定利率還款不劃算,借款人也可以選擇提前還款。
注:
1.此處工商貸款數據是用對企業和機關團體的貸款減去房地產開發貸款計算得來。
2.蘇農商行是蘇州農村商業銀行的簡稱。
作者:招商銀行研究院副總經理
責任編輯:羅邦敏? 鹿寧寧
參考文獻
[1] John Y. Campbell. Household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61(4):1553-1604.
[2] Paul Blacklow et.al.. Fixed versus floating rate - borrower characteristics and mortgage choice in Australia[R]. 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2010,No.3957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