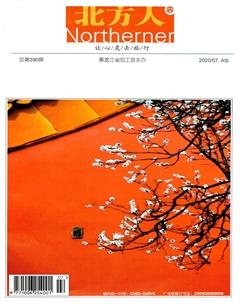高高在上的科學
馬宇平

高是沒有止境的。為了到更高的地方,吳天一身上數得清的骨折就有14處,最嚴重的一次,車從山上翻下去,他左邊4根肋骨、肩胛骨都摔斷了,髕骨粉碎性骨折,腓骨脛骨也斷了。但是106天后,他又騎著馬出發了。
對于這位研究高原病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來說,這些山路是他做研究的必經之路。他所在的青海高原醫學科學研究所在西寧,他不熟悉西寧的街道,卻知道青海很多縣、鄉的確切海拔。同事們都知道吳天一有個“毛病”——“到了州上問哪個縣海拔最高,到了縣上問哪個鄉最高,到了鄉里問哪個村最高”,幾乎沒有例外。
爬阿尼瑪卿山時,吳天一56歲。他和同事們將腰間的繩索連接在紅色登山繩上,貼著陡峭巖壁向前走。他排在隊伍的最前端。
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中日聯合醫學學術考察隊在阿尼瑪卿山開展考察。日本隊員在海拔5000米做了10天實驗后,大多發生明顯的高原反應。日方隊長酒井秋男告訴吳天一,自己的隊伍將集體下撤,而作為中方隊長的吳天一決定,帶領中方隊員向更高海拔攀登。
更高的海拔帶來更多的研究成果。如今,全世界都按吳天一和團隊提出來的“青海標準”診斷慢性高山病。這是醫學領域第一個由中國學者提出并命名的診斷標準。
他在公眾中的知名度不夠高,但他們長年在缺氧環境中取得的科研成果讓很多踏上青藏高原的人受益。吳天一主編的3本高原病科普書籍,成了青藏鐵路列車上的常見讀物。
可吳天一還想到更高的地方去。今年84歲的他計劃再去趟珠峰,他一直惦念著在那里建個“特高海拔高山醫學實驗站”。上一次去時,他81歲。
除爬山外,吳天一還經常鉆進西寧研究所里的高低壓氧艙做實驗。這是中國第一個大型高低壓綜合氧艙,低壓氧艙將他“送達”海拔四五千米的缺氧環境進行實驗,高壓氧艙能救治危重病人。
這個高低壓氧艙是吳天一參與設計的,他也是第一個進艙實驗的人。他的耳鼓膜在壓力變化中多次被擊穿。最近一次是2011年,76歲的吳天一在一個國際合作項目中,堅持和國外同行一起早上7時30分進艙,晚上10時30分出艙,一次模擬海拔快速下降中,他的耳鼓膜又被擊穿。現在,他的耳鼓膜因為疤痕變厚,來訪者說話響亮點兒他才能聽清。
“我們一輩子跟天打交道的人,應該是要有付出的,才能做出成績來,這一點沒有什么后悔的。”吳天一說。
1958年,他和妻子響應號召,與山東、河南、安徽等地的大批青年共同支援青海建設。身體強壯的年輕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區開墾,出現了心慌、胸悶、頭疼等反應。當時人們對高原病缺乏認識,診斷和治療手段也相對落后,得了高原病的年輕人要么被迫離開青海,要么忍受著疾病的折磨。畢業于中國醫科大學的吳天一看到這些,決定開始研究高原醫學領域。
1963年和1965年,吳天一在我國首次綜述報告了高原肺水腫和成人高原心臟病。他也是我國第一個報告高原紅細胞增多癥的專家。
上個世紀80年代起,研究所開始組織“高原醫學遠征軍”,科研隊前往高海拔、以藏族為主要群體的縣域,進行以高原心、肺功能為中心的現場研究。
2001年,青藏鐵路二期工程開工,吳天一擔任青藏鐵路二期建設的高原生理研究組組長,保證了這條線路上的14萬余名筑路工人無一人因為高原病死亡。
這里最低氣溫達零下40多攝氏度,氧氣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人走在工地上,偶爾走快一點兒就頭痛欲裂,需要大口大口喘氣。有人回憶,當時連施工用的卡車都需要“吸氧”——司機每天要用氧氣瓶對著卡車的空氣濾清器噴氧。
“我當時提出來,不能像建青藏公路時那樣,用卡車把那個氧氣罐拉上去又拉下來,那個不夠用的,必須要建制氧站。”吳天一說。在他的建議下,青藏鐵路施工沿線,共建起23個制氧站、25個高壓艙站、若干高壓袋。在高壓氧艙里,“人就相當于到了海平面”。除此之外,吳天一提出了“高壓艙、高壓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轉、低轉、再低轉”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同時建立三級醫療機構,平均每10千米一個醫院。
他甚至想到了員工起夜時可能發生的危險。“別小看晚上去廁所,很多人就可能倒在這‘一泡尿上。”吳天一解釋,“人夜里跑出去上廁所,很可能懶得穿好外套,但外面氣溫在零下30-40攝氏度,一旦感冒發生高原肺水腫就可能致死。”在他的建議下,青藏鐵路使用了帶有取暖設備的衛生車,晚上與住宿室對接,在冬天保障工人夜間去廁所不感冒,夏天防止環境污染。
上世紀90年代初那次阿尼瑪卿山考察,吳天一帶領的中國科研隊在登山的同時,也拿自己做實驗。海拔5000米以上,他們每上升50米,就對自己的心肺功能和對氧氣的利用率等進行記錄,檢測應激狀態下人的生理反應。海拔5620米處,他們建立了特高海拔高山實驗室,獲得大量高山生理資料。
加上前期準備,吳天一在阿尼瑪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做了5年高山生理研究。他的雙眼因雪地反射和強紫外線患上了白內障,不得不植入晶體治療。
即便如此,吳天一仍把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山脈稱為“人間科學的天堂”。他和隊員們開拓了“藏族適應生理學”研究,在這里第一次提出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獲得“最佳高原適應性”的論點,為人類低氧適應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生物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