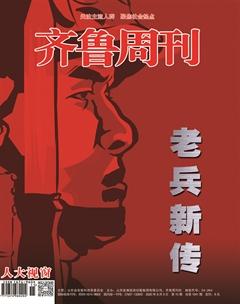仇世森:在泥土里追逐無塵陽光
由衛娟

▲《遠古》青銅2005 年。
在心靈深處,在城市的C位
仇世森家的客廳里,幾座雕塑吸引了記者的目光。
《無塵陽光》是一位西藏的老年僧人,靜靜地在陽光下轉動念珠。他好像已經在此念禱了千年,還會如此不停地念禱到永遠。陽光照在眼皮上的溫暖、無聲念禱帶來的身心安然,讓人不由自主地被他的祥和境界吸引,浮躁的心靈也隨之慢慢平和。仇世森有過多次赴藏的經歷。在西藏未通火車的年代,公交車攜帶風塵呼嘯而過讓人瞬間模糊了視線。但就在那樣的風塵里,老年僧人的安然,如同高原上明凈的陽光一樣,流淌著安撫靈魂、凈化內心的能量,讓仇世森的創作欲望噴薄而出。
在仇世森看來,西藏簡直是一座流動的雕塑殿堂。那里的僧人和牧人,面容的滄桑與安然、衣著的質感、舉止的虔誠,時時刻刻處處吸引著他的目光。他曾圍著一位轉經筒的牧民360度欣賞,恨不得手頭就有陶泥馬上就能創作,顧不上同行者的等待。他在寺廟里盯著牧人們布施,入迷地觀察他們的神情和舉止。貧困的牧民常常拿著一元錢布施,然后自己找零,再繼續布施。仇世森模仿著他們的布施方式、揣摩著牧人的虔誠心意,甚至被游客舉報給了保安。
正是對藏人的細致觀察、深入體悟,讓他的西藏系列作品擁有了獨特的神韻和打動人心的力量。他抓取的是一個個體的一個瞬間,卻展示了一個群體的生活場景和生命狀態,營造了超越地域、民族、宗教的令人沉醉的藝術空間。
或許正是這種能量,讓他的城市雕塑系列既蘊含地域文化底蘊,又有靈動可喜的風格。泉城路、芙蓉街、大明湖是最能體現濟南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民俗特色的區域,承載了這個城市的記憶和情感。仇世森的雕塑作品《老殘聽曲》就在泉城路與芙蓉街的交匯處,占據“金街”的黃金位置,也是“齊魯第一街”當之無愧的C位。路過的市民和游客頻繁地打卡和拍照,讓這組雕塑成為濟南最有知名度的藝術地標。
《老殘聽曲》典出《老殘游記》,是老殘行至濟南游于鵲華橋、歷下亭、千佛山、大明湖后,至小布政司街明湖居,聽黑妮白妮說大鼓如癡如醉。白妮一足在前,一足在后,持兩片“梨花簡”正在傾情演唱;石桌旁坐著低眉細聽的”老殘”,站在一旁的小伙計一邊倒茶一邊扭頭聽書,不意茶水溢出。桌上隨意的幾朵蓮蓬是濟南特有的茶點,白妞挺括的演出服飾與老殘的隨意行裝形成了鮮明對比,老殘的風塵仆仆、垂目傾聽、敲擊節拍與小伙計的扭頭、失手則交代了人物的不同身份和閱歷。老濟南的歷史韻味何在?石桌旁有空凳、桌上有空杯子,游客隨意一坐,即入畫中,可與老殘同飲,與小伙計共醉。
濟南人都知道,舜井街曾是手機一條街。街口上,《打手機的人》,一手扶墻單足站立打手機,則留存了這段記憶。步行在泉城路上,從東到西,累了想找個長椅休息一下,卻發現有一對《爺倆》已經捷足先登。父親人困馬乏,兒子則呼呼大睡,是節假日步行街常見的一景,也是藝術家的生活積累。坐在這椅子一端的游客往往忍不住要伸出手去幫忙攔一下娃娃,心里生起一種對男人帶孩子的感慨,以至于孩子身上被摸得錚亮。
仇世森的城市雕塑往往有一種讓人不由自主參與其中的魔力。大明湖的《磕拐》旁,常見老少游客也曲腿作戲留影。《滑板》則讓人產生一種趕緊避讓的沖動,好似下一秒就會呼嘯而來。《釣魚》則是大明湖新區惟一一組水上游覽的雕塑,他實地考察了兩次才確定了這一相對隱蔽安靜的釣魚之處。
“城市雕塑正如我們史書上的插圖,記載了不同時代的歷史和文明”,展示了城市的文化水準和精神風貌,緩解緊張浮躁并帶來樂趣和生機。于此, 仇世森在城市公共空間的雕塑作品,點明了泉城的城市性格,界定了城市文脈,并漸漸成為文明的代言和城市記憶的見證。
細節上的真實動人、靈魂上的同理共鳴
黑格爾認為:雕刻與建筑一樣,是“就建筑單純的感性物質的東西按照它的物質的占空間大形式來塑造形象。”“雕刻則把精神本身(這種自覺的目的性和獨立自足性)表現于在本質上適宜于表現精神個性的肉體形象,而且使精神和肉體這兩方面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呈現于觀照者的眼前。”

▲《橙色記憶》復合材料1998 年。
仇世森的雕塑,常給人以無限的遐想,讓觀者在有限的空間里,連接藝術家的思緒,觸發自身的經驗,引發出精神上的無限空間。
汶川地震期間,仇世森密切關注震區動態,一直處于和震區同胞同頻共振中。那些廢墟中挖出的書包、遺址前痛不欲生的身影……讓他久久不能平靜。接到創作任務后,積累的悲歡、發酵的情感一觸而發,《呼喚》在短短幾個小時即出小稿、泥樣。學生震驚于他的速度,但他心里明白,這創作,其實從地震消息傳來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瘦弱的孩子拎著幾個書包,伸長了脖子不停地呼喚自己往日的小伙伴……拉長變形的脖子,是他內心焦急痛苦的體現,也是創作者的真情流露,亦是當年全國上下“今天,我們都是北川人”的真實寫照。此后,作為濟南軍區文藝工作者,他為北川擂鼓八一中學創作了高達9.5米的主題雕塑《自強·奮進》,重現了這一重大自然災害面前國人的精神高度和時代氣質。

雕塑家仇世森
有報道指出:“仇世森的作品,以動態的人物創作和場景的構圖方式,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常常表現出超越現實真相的一種‘像。也就是把生活的真實美升華為藝術的真實美.藝術中的真實美又高于生活中的真實美,用每一筆刻詮釋的不僅是眼見為實的真實,而是一種精神及靈魂上的真實。”

▲《轉經筒》青銅2008 年。

《呼喚》青銅2008 年。
《沒有金牌的冠軍》抓取了奧林匹克歷史上的經典一幕,仇世森精雕細刻了馬拉松選手的動作和表情,卻“風化”了兩位裁判的形象。跌倒了爬起來的賽手皮特里已經因“永不放棄”的奧林匹克精神名垂青史,但被其感染而援手的裁判和記者早已泯滅于歷史。在《唐韻》系列中,仕女皮膚的光潔、面容的精致呈現出瓷器一樣的質地,但衣裙和發型卻粗糙簡潔,兩者相映成趣,展示了藝術家融匯傳統與現代的審美取向。

《無塵陽光》青銅2005 年。

▲《精忠報國》青銅2006 年。
1998年抗洪,仇世森抓取了救生衣這一意象,創作的《橙色記憶》獲“抗洪精神贊”全國美展銀獎。長長的救生衣組成大堤,又似臂膀,帶著堅不可摧的精神,凝固了軍民一心“堤在人在”的誓言。
作品《遠古》也摒棄了他所擅長的人物神情和細節的真實生動,而是借鑒了巖畫的風格,展示了遠古人類的力與美。人物的面部和手足都符號化抽象化處理,手臂與弓箭合體,身上則鐫刻了遠古圖騰并保存塑痕強調滄桑,展示了仇世森在現代非寫實雕塑創作上的功底。《橙色記憶》《遠古》等現代作品與《精忠報國》《支部建在連上》等傳統風格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展示了仇世森在不同題材、不同材料、不同風格創作的寬度與廣度。
作為濟南軍區的文藝工作者,仇世森的作品不走“奇怪”的路徑,正能量滿滿卻不拘泥于傳統,浩然沛然、陽剛有力,卻富有情感打動人心。
仇氏藝術的真正傳承
1990年,仇世森創作了雕塑《父與子》,兒子倒立在父親如山一樣偉岸的身上快活無比。30多年后,他坦言,那就是他和父親的寫照,沒有很多細節,大愛無聲。
他的父親仇志海先生,生前曾為山東雕塑家協會主席,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被軍內外譽為“泥人仇”和“戰士雕塑家”。他的雕塑《春》《海螺女》《鄧世昌》《東方》等已成為名勝景觀和標志。仇志海雕塑名作《鞠躬盡瘁》抓取 了周總理清癯的臉龐和睿智的眼睛,展示了人民公仆的精神氣質。上世紀80年代,仇志海先生為發掘消失了四千多年的黑陶藝術,拿出自己所有的積蓄,帶領仇世森來到日照農村,棲土枕窯,歷時數年,挖掘復原了黑陶藝術。仇氏黑陶,“薄如絮、黑如墨、亮如漆,扣之金聲、撫之若膚、氣質高朗、返璞歸真、大巧若拙”,被學術界、藝術界評價為‘本世紀最輝煌的藝術成果之一”。時人評價:“諸多藝術品的陸續問世,這些黑色的精靈跨躍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斷代,帶著撼人心扉的全新姿態,使現代人驚嘆不已。”
“仇氏黑陶”被國家定為贈送外賓的國禮,仇志海、仇世森的黑陶藝術自1989年以來,先后獲得國務院文化部“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第38屆“世界發明博覽會尤里卡”金獎。1996年5月,仇志海又榮獲“軍隊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同年7月22日,他因藝術創作勞累過度,早逝于工作崗位上,終年60歲。
那些陪伴父親在荒郊野外燒窯試錯的經歷,雖然已經過去了數十年,但卻依然歷歷在目。當年的仇世森20多歲,跟著父親鉆山穿林去民間土窯取經,還常常對“仇志海的大公子”等稱謂心有不滿。當他已經成為山東雕塑界的一桿大旗后,他卻表示寧愿一直做父親這棵大樹下的青苔。

《老殘聽曲》青銅高180cm 2001 年仇世森(合作)。

▲《沒有金牌的冠軍》青銅2010 年。
小時候,父親做雕塑,仇世森就給父親打下手翻模。13歲的時候,有一次幫父親翻模,仇世森突然淡淡地表揚了一句,“贏得勝境在遠處”。那一天,仇世森就像上足了發條一樣,一連翻了13個魯迅像……仇世森工作后,最初并未選擇父親的藝術道路。但數年在工藝美術研究所面塑的學習,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系統的專業教育,加上幼年父親的不言之教,將他慢慢引入這條道路。父子的默契到了不必言說,一個眼神就彼此心領神會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