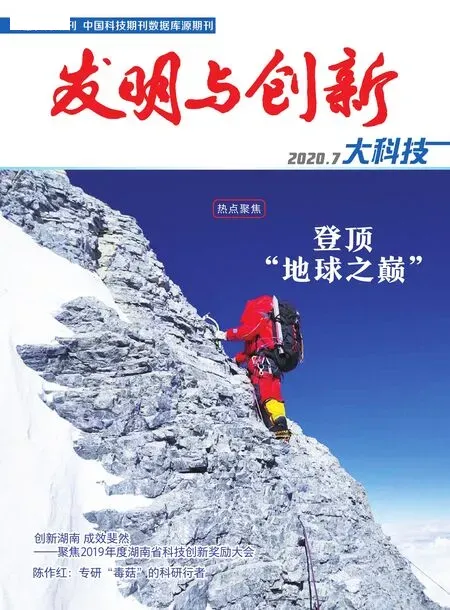我國商業航天尋求更大“推力”

圖/東方IC
隨著衛星互聯網被納入“新基建”范圍,商業航天產業再次受到關注。近年來,我國商業航天發展之路越走越寬,從火箭研制、發射,到衛星運維、服務,至少有數十家商業航天企業在探索中前行。在國外不少商業航天公司宣布裁員甚至申請破產的背景下,九天衛星、微納星空等國內商業航天初創公司近期卻宣布完成新一輪融資。有報告認為,2020 年我國低軌衛星通信發展將邁出實質性步伐,中國商業航天產業有望迎來“大年”。“中國商業航天起步比較晚,但發展勢頭迅猛。”這是哈爾濱工業大學航天學院教授、銀河航天合伙人張世杰等專家的共識。以商業衛星為例,目前國內的銀河航天、千乘探索、九天微星等企業,都已發射了相關衛星。結合當下應用熱點,實現跨界融合發展,是國內商業衛星發展的特色。但在發展中,商業航天法律體系有待完善、產業上下游配套不強、商業航天人才不足等,都是我國商業航天需要破除的難題。
商業航天企業不斷獲資本青睞
北京時間5 月31 日凌晨3 時22 分,SpaceX 的獵鷹9 號火箭和載人“龍飛船”(Crew Dragon)成功發射,其搭載的兩名NASA 宇航員將前往國際空間站執行任務。
這意味著人類首次商業載人航天發射成功,而SpaceX 也成為首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私人公司,這被稱為是全球商業載人航天產業的歷史性突破。
相比之下,我國的商業航天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尤其是2016 年國務院印發《“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發表《2016 中國的航天》白皮書,提出鼓勵引導民間資本參與航天科研生產、空間基礎設施建設等航天活動,大力發展商業航天,完善政府購買航天產品與服務機制等內容。
在此背景下,近幾年涌現了藍箭航天、銀河航天、星際榮耀、千乘探索等一大批商業航天企業,并不斷獲得資本青睞。
數據顯示,2015 年至2019 年,與商業航天相關的投融資約160 起,投資金額超過百億元。
而SpaceX 的成功,也讓國內的商業航天企業頗為振奮。
“看到SpaceX 的成功后,我們也認為需要通過自身的能力,去定義中國商業航天新的場景。”藍箭航天CEO 張昌武說,“我們面向的是全球商業發射市場。作為來自航天大國的新玩家,中國商業航天企業未來也必然會進入國際競爭體系,因此我們必須把目光放在全球商業發射市場需求上,加快大推力液體火箭的研制節奏,盡早向市場推出更具競爭力的產品。”
衛星應用向民用消費級擴展
“商業衛星的突破口是遙感。遙感已具備非常成熟的商業模式,傳統遙感應用場景廣闊。”2019 年8 月,千乘探索首顆衛星“千乘一號01 星”發射成功,衛星具備遙感通信雙功能。千乘探索CEO 苗建全表示,公司要造“業務衛星”,長期在軌為用戶提供遙感數據服務。
而在張世杰看來,“衛星的應用需求正在向民用消費級需求擴展。”比如,遙感衛星從測繪應用到為新聞采寫提供服務。“疫情期間,衛星遙感‘熱圖’可顯示復工復產情況,并為新聞采寫提供服務,讀者可以通過衛星圖片直觀了解復工復產的情況。”張世杰說道。
近日,嗶哩嗶哩網站(簡稱B 站)發布消息,將發射一顆名為“嗶哩嗶哩視頻衛星”的遙感衛星,衛星所獲的遙感視頻、圖片數據將用于B 站科普視頻。B 站公布的資料顯示,通過“嗶哩嗶哩視頻衛星”,B 站將在衛星拍攝的海量遙感視頻、圖片數據基礎上,定期更新科普視頻,內容包含科技、人文、歷史、地球、公益、教育等多個領域,并為B 站用戶定制拍攝任務,用衛星航拍地球。
“此外,低軌寬帶通信衛星的發展也正在解決越來越多人的上網難題。”張世杰說,未來隨著衛星的部署,不僅偏遠山區孩子上網難的問題或將得到徹底解決,在飛機、高鐵、游輪上順暢看視頻直播也將成為現實。
張世杰表示,近年來,以高頻段、多波束和頻率復用為技術特征的高通量衛星技術日漸成熟,將衛星通信速率提升了十倍以上,服務成本有了大幅下降,變革了傳統衛星通信領域。尤其是近地寬帶通信星座具有全覆蓋、帶寬大、時延小、成本低等優勢,逐步興起成為解決全球網絡覆蓋的新方案。
目前,中國“虹云工程”與“鴻雁”星座、美國SpaceX 的“星鏈”計劃與亞馬遜的“凱珀”項目等航天任務相繼提出,成為當前衛星通信商業化的核心方向。
跨界融合成商業衛星新趨勢
2010 年以后,寬帶互聯網的全面覆蓋,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快速普及和商業化迅猛發展,培養了數十億用網人口的數據型應用消費習慣。數據顯示,全球網民有43.88 億人,約占全球人口總數的57%,全球仍有30多億人尚未接入互聯網。
張世杰認為,衛星通信覆蓋范圍廣、部署快,不受地面環境影響,在全球未聯網地區具有不可取代性,以低軌寬帶通信衛星為代表的“衛星互聯網”的建設,將承擔連接另外30 多億人接入互聯網的重任。
從空客、波音等航空巨頭進入衛星制造,到摩托羅拉建造“銥星”星座,一直以來“跨界玩航天”現象并不罕見。近年來,更多的行業巨頭邁入商業航天領域,以互聯網跨界航天最具有典型性,亞馬遜、臉書、谷歌等互聯網企業都正在推出或研究低軌寬帶通信衛星計劃。2019 年,亞馬遜發布“凱珀”項目,計劃發射3236 顆寬帶通信衛星至近地軌道,為世界各地提供快速且低延遲的互聯網接入服務。
“究其原因,用戶規模是互聯網快速發展的不二法寶,互聯網跨界航天的背后是地面網絡已經無法覆蓋另外的30 多億用戶,這種跨界將直接解決用戶的問題,進一步推動航天商業化的發展。”張世杰說。
在“互聯網+航天”跨界融合方面,銀河航天公司于2020 年1 月發射了自己的低軌寬帶通信衛星。僅隔一個月,該衛星就完成通信能力測試,在國內第一次驗證低軌Q/V/Ka 等頻段通信。
而目前已擁有8 顆衛星的九天微星則計劃在未來3年內發射72 顆星,構建屬于自己的低軌物聯網星座。“商業航天,不僅是技術上要做好,更重要的是能夠產生價值,讓整個鏈條運轉起來,產生收益。”九天微星CEO 謝濤說。
商業航天發展仍待破題
商業航天的發展有賴于政策的開放和完善。近幾年來,我國各地政府也在積極引導商業航天產業建設,改善商業航天企業的發展環境。例如,武漢市自2017 年開始建設國家航天產業基地,是我國首個商業航天產業基地,該基地的目標是打造以商業航天、新材料、高端裝備為主的千億級產業集群。今年4 月22 日,位于山東煙臺海陽市的東方航天港產業項目正式開工,包括商業固體運載火箭煙臺產業基地項目、商業航天固體動力項目、國家高分專項衛星數據應用產業研究院項目、航天產業資本化運作項目、高頻遙感大數據生態產業項目等10 個航天類項目通過視頻云簽約與現場相結合的方式集中簽約。
隨著衛星互聯網納入“新基建”范疇,未來幾年中國的低軌衛星發射也將迎來高潮。另外根據國內各個衛星公司的此前規劃,多數都要在2023 年左右完成星座建設,2020 年至2023 年將會迎來衛星大批量生產、大規模發射的產業爆發期。
“希望未來隨著政策的進一步開放,加速推動我國商業航天的發展。”張世杰表示,商業航天發展還需要培養發展商業航天的人才技術儲備,這也是目前我國發展商業航天的瓶頸。
航天專家蔡軍表示,中國商業航天領域有年輕精干的團隊,既繼承了航天國家隊的傳統,又富有新時代的創新精神,在設計、開發等方面并不弱于國外。但進入商業航天領域的人才總體不足。
苗建全在創立千乘探索前,是某航天型號首飛時的01 指揮,在體制內工作9 年后離職。“航天科研人員離職創業,渠道是通暢的。但在人才流出過程中,仍有許多細節需要完善。”
相對來說,目前國內商業衛星等成本仍然較高,且上下游產業鏈配套方面不足。長期形成的體制性原因,使我國商業衛星的產品配套只能依靠國有航天企業,但面對市場時,國有航天企業動力不足。
“目前國內商業航天發展迅速,但缺乏實驗試驗裝置和測控資源,要促進國家單位資源向商業航天開放,同時也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積極鼓勵商業航天發展。”蔡軍說,商業航天發展給航天全產業鏈都帶來了機遇,要引導傳統航天產業向市場轉化,讓封閉的航天資源向市場開放,讓分散的航天應用集成到規模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