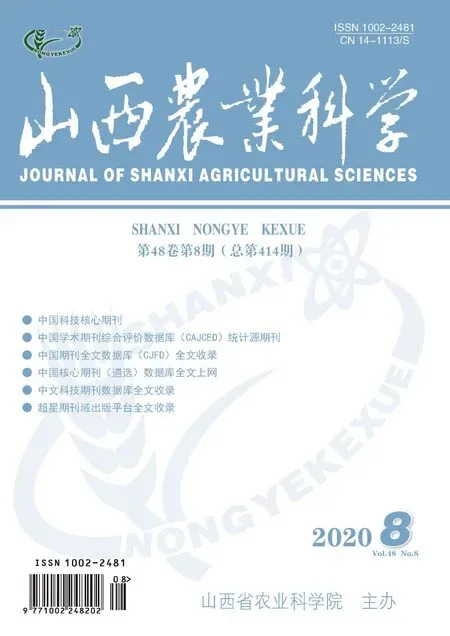1 株犢牛源多重耐藥大腸桿菌分離株的ESBLs 與AmpC β-內酰胺酶表型檢測
劉一飛,王志宇,劉華棟,馬 馨,張偉業,孫仰介,薛俊龍,劉澤民
(山西農業大學動物醫學學院,山西太原030032)
犢牛腹瀉是養牛場中頻發的常見疫病,急性腹瀉通常會導致犢牛產生系統性敗血癥,甚至死亡,而致病性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及其他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感染是造成犢牛腹瀉的最主要原因。近年來,由于抗生素類藥物在養殖業中的長期不規范使用,各種耐藥性大腸桿菌菌株在臨床檢驗過程中不斷被發現,而超廣譜β- 內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s,ESBLs) 和頭孢 菌素 酶(AmpC enzyme)的產生是臨床分離病原菌株呈現多重耐藥性(mult-drug resistance,MDR)的重要機制之一[1-2]。當前,產ESBLs 和AmpC 病原菌已在多種家畜中普遍流行。迄今為止,國內外已有較多涉及家禽、豬、牛及伴侶動物源產ESBLs 和AmpC 酶大腸桿菌的相關報道[3-5]。其中,ESBLs 主要由腸桿菌科(Enterobacteriaceae)耐藥質粒(R plasmid)介導的β- 內酰胺酶基因衍化而來,具有水解β- 內酰胺類抗生素如青霉素和氨基青霉素的活性,但不能水解頭霉素類和碳青霉烯類藥物。ESBLs 活性可被抑制劑如克拉維酸(clavulanate,CLA)顯著抑制。ESBLs的各基因型主要分為blaTEM、blaSHV、blaCTX-M等[6],其中,產blaTEM型β- 內酰胺酶大腸桿菌在我國家畜中流行最為普遍[7-8]。近幾年,國內有關腸桿菌科AmpC β- 內酰胺酶的報道日益增多[7,9]。AmpC 酶基因幾乎存在于所有腸桿菌科細菌中,通常是由染色體介導表達低水平的AmpC 酶,從而導致革蘭氏陰性桿菌對第3 代頭孢菌素產生耐藥性,該酶活性不能被CLA 所抑制,但可被氨基酸硼酸(3-Aminophenol boric acid,APB)和氟氯西林(flucloxacillin,INN)顯著抑制。而在大腸桿菌中,AmpC 酶主要由R 質粒介導產生,且無需誘導即可持續、大量表達[10]。
由于β- 內酰胺酶基因可經由R 質粒、轉座子和整合子等方式在細菌間散播[11],因此,有必要對產β- 內酰胺酶病原微生物進行實時檢測,以指導臨床上合理用藥。2019 年初,太原市某奶牛場一頭因罹患腹瀉死亡的犢牛被送至山西省農業科學院畜牧獸醫研究所預防獸醫研究室受檢。該奶牛場場主描述,使用多種抗生素治療該病犢后,病情皆無緩解。據此,推測該病犢可能是因耐藥性病原微生物感染而導致抗生素治療效果欠佳。在對病犢剖檢過程中發現,其病理特征呈現典型的腸型大腸桿菌病癥狀,并從病犢肝臟中分離到1 株多重耐藥性優勢大腸桿菌菌株。經查詢文獻得知,當前尚未有關于山西省牛源產β- 內酰胺酶大腸桿菌的相關研究報道。
本試驗將該犢牛源大腸桿菌分離株分別進行25 種藥物的敏感性試驗、ESBLs 和AmpC 酶表型篩選以及blaTEM基因型PCR 檢測,以了解該分離株的耐藥譜和β- 內酰胺酶基因的攜帶情況,旨在為該養牛場犢牛腹瀉的綜合治療推薦敏感藥物種類以及為有效防控耐藥菌株的傳播提供參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試驗動物 供試動物為山西省太原市某奶牛場送檢的因腹瀉致死的犢牛1 頭,剖檢可見病犢真胃存有凝乳塊,胃黏膜充血;肝臟蒼白有零星出血點;腸內容物混有血液和氣泡,小腸黏膜充血,腸系膜淋巴結腫大。病犢的病理剖檢呈現典型腸型大腸桿菌病癥狀。
1.1.2 主要試劑 普通營養瓊脂、麥康凱瓊脂、M-H 肉湯、M-H 瓊脂、LB 肉湯等均購自青島日水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質粒提取試劑盒、TaqPCR Mix、TaqDNA 聚合酶等均購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5 種抗菌藥物藥敏紙片均購自中國獸藥監察所;大腸桿菌質控菌株ATCC25922、腸桿菌科編碼生化鑒定管以及ESBLs 和AmpC 酶檢測試劑盒均購自杭州天和微生物試劑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臨床菌株的分離鑒定 無菌條件下取病犢肝臟進行低溫研磨,生理鹽水稀釋后取上清液接種于營養瓊脂平板,37 ℃培養12 h,反復接種將分離菌純化至單個菌落,肉眼觀察菌落形態。用接種環挑取圓形、濕潤、灰白色、凸起菌落劃線轉接于麥康凱瓊脂平板,37 ℃培養24 h。挑取麥康凱瓊脂平板上的單個純培養粉紅色菌落進行涂片、染色、鏡檢,將符合腸桿菌科細菌形態特征的純化單菌落分別接種于GYZ-15e 生化編碼鑒定管硫化氫、苯丙氨酸、葡萄糖酸鹽、靛基質、葡磷胨水、枸櫞酸鹽、尿素酶、胰蛋白胨半固體、葡萄糖、賴氨酸、鳥氨酸、棉子糖、山梨醇、側金盞花醇、木膠糖中,37 ℃培養18~24 h,觀察并記錄各生化反應結果。
1.2.2 大腸桿菌分離株的藥物敏感性試驗 其按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化委員會(CLSI)推薦的腸桿菌科細菌紙片法(K-B)藥敏試驗標準進行操作和判定。使用25 種常用藥物對該大腸桿菌分離株進行藥物敏感性試驗,將分離菌株接種M-H 肉湯,37 ℃培養4 h,在光度計中比對0.5 麥氏管,用生理鹽水將培養菌液稀釋到0.5 麥氏單位(1.5×108cfu/mL),用無菌棉棒蘸取菌懸液涂布于M-H 瓊脂平板,靜置10 min 后將藥敏紙片貼于培養基表面。以質控菌株ATCC25922 作為對照,測量各藥敏紙片的抑菌直徑,以確保藥敏結果的準確性。
1.2.3 大腸桿菌分離株的ESBLs 表型檢測 運用CLSI 推薦的雙紙片協同法(Double-disk synergy test,DDST)對分離菌株進行ESBLs 表型檢測。分離株菌懸液制備和涂布M-H 瓊脂平板方法同1.2.2,以質控菌株ATCC25922 對頭孢菌素和克拉維酸進行質控檢測。將頭孢他啶(CAZ,30 μg/片)與頭孢他啶 - 克拉維酸(CAZ-CLA,30/10 μg/片)、頭孢噻肟(CTX,30 μg/片)與頭孢噻肟- 克拉維酸(CTX-CLA,30/10 μg/片) 分別對稱貼于 M-H 瓊脂平板,37 ℃培養12 h。測量各藥敏紙片的抑菌圈直徑,將頭孢他啶- 克拉維酸(CAZ-CLA)抑菌圈直徑大于頭孢他啶(CAZ)5 mm 以上或者頭孢噻肟- 克拉維酸(CTX-CLA)抑菌圈直徑大于頭孢噻肟(CTX)5 mm以上判定為產ESBLs 陽性菌株。
1.2.4 大腸桿菌分離株的AmpC 酶表型檢測 目前,CLSI 還未推薦標準的AmpC 酶表型檢測方法。而根據美國臨床檢驗委員會(NCCLS,2000)執行標準設計的APB 阻抑物基法被認為是AmpC 酶表型檢測的常規方法[12]。該方法是將2 片頭孢他啶(CAZ 1、CAZ 2)間距18 mm 以上貼于M-H 瓊脂平板上,另將一片APB 阻抑物紙片貼在其中一片頭孢他啶(CAZ 1)附近 4~6 mm 處,分別標記為 CAZ 1、APB(圖 2),37 ℃培養 12 h。將 CAZ 1 朝向 APB 的融合抑菌圈直徑大于另一單獨頭孢他啶(標記為CAZ 2)5 mm 以上,且CAZ 1 抑菌環向APB 明顯擴大即判定為產AmpC 酶陽性菌株。分離株菌懸液制備和涂布M-H 瓊脂平板方法同1.2.2。
1.2.5 質粒介導的blaTEM基因型PCR 檢測 將分離菌株接種于LB 肉湯,置于37 ℃培養箱,以180 r/min 振蕩培養8 h,按照質粒提取試劑盒操作步驟提取菌株質粒DNA。ESBLsblaTEM基因型PCR 擴增上、下游引物序列分別為:5′- CATTTCCGTGTCGCC CTTATTC-3′和 5′- CGTTCATCCATAGTTGCCTGA C-3′,預計擴增片段長度為 800 bp[13]。PCR 反應體系為:10×Buffer 5 μL,dNTP 4 μL,上游引物 1 μL,下游引物 1 μL,TaqDNA 聚合酶 0.25 μL,質粒 DNA(20~50 ng/μL)2 μL,加 ddH2O 補足至 25 μL。PCR反應參數為:94 ℃預變性 5 min;94 ℃變性 45 s,54 ℃退火 45 s,72 ℃延伸 1 min,共 30 個循環;72 ℃延伸10 min。PCR 產物經1%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純化后送交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進行測序。
2 結果與分析
2.1 臨床分離株的形態特征和生化鑒定結果

表1 分離菌株生化特性鑒定結果
從病犢肝臟中分離到菌株經純化培養后,在麥 康凱瓊脂平板上生長為圓形、濕潤、光滑、中心隆起、直徑為1~2 mm 的粉紅色菌落(圖1-A);革蘭氏染色鏡檢顯示,分離菌株為革蘭氏陰性菌,短桿狀,兩端鈍圓,單個或成對排列(圖1-B)。生化反應結果顯示,該分離菌株與大腸埃希菌的生化特性一致,且經GYZ-15e 生化鑒定編碼冊查知,該分離菌株的鑒定編碼為06345。綜合分離菌株的形態特征觀察和生化鑒定結果,確認該分離菌株為大腸桿菌菌株。所有受試生化試劑和代謝結果如表1 所示。
2.2 大腸桿菌分離株的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

表2 大腸桿菌分離株藥敏試驗結果
藥敏試驗結果顯示,分離菌株對多黏菌素B、痢特靈、頭孢西丁敏感;對磷霉素、頭孢曲松中度敏感;而對青霉素、阿莫西林、氨芐青霉素、桿菌肽、利福平、阿米卡星、氨曲南、慶大霉素、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諾氟沙星、環丙沙星、新霉素、卡那霉素、鏈霉素、四環素、羅美沙星、頭孢哌酮、頭孢噻肟、頭孢他啶耐藥。結果表明,該大腸桿菌分離株為多重耐藥性菌株。分離菌株對25 種藥物的敏感性試驗結果如表2 所示。
2.3 大腸桿菌分離株ESBLs 和 AmpC 酶表型檢測結果
分離株ESBLs 表型檢測結果顯示,CAZ-CLA抑菌圈直徑為23 mm,CAZ 抑菌圈直徑為14 mm,二者差值為9 mm;CTX-CLA 抑菌圈直徑為23 mm,CTX 抑菌圈直徑為8 mm,二者差值為15 mm(圖2-A),2 組差值均大于5 mm,表明該大腸桿菌分離株為產ESBLs 陽性菌株。分離株AmpC 酶表型檢測結果顯示,CAZ 1 朝向APB 的融合抑菌圈直徑為24 mm,CAZ 2 抑菌圈直徑為14 mm,二者差值為 10 mm(圖2-B),大于5 mm,且抑菌環向APB 方向明顯擴大,表明APB 與CAZ 間產生協同效應,該大腸桿菌分離株為產AmpC 酶陽性菌株。依據β-內酰胺酶表型檢測結果,判定該分離菌株為兼產ESBLs 和AmpC 酶的陽性菌株。
2.4 質粒介導blaTEM 基因型測序結果分析
PCR 擴增結果表明,該分離菌株R 質粒中攜帶有blaTEM基因,進一步證實該分離菌株對β- 內酰胺類藥物產生耐藥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ESBLs 的表達所導致。分離菌株質粒介導的blaTEM基因部分擴增序列如圖3 所示。登錄NCBI 網站將blaTEM基因測序結果提交Blastn 進行序列同源性在線分析,結果表明,大腸桿菌分離菌株與大腸桿菌HA33 TEM家族blaTEM基因(GenBank 登錄號 MN128601.1)、大腸桿菌3E TEM 家族blaTEM基因(GenBank 登錄號MN096661.1)的同源性均為100%。
3 結論與討論
隨著抗生素類藥物在畜禽養殖中的廣泛使用,臨床分離到的耐藥菌株種類、數量逐步增多,且細菌耐藥性不斷加重,越來越多的條件致病菌尤其多重耐藥性大腸桿菌在畜禽群體間的普遍傳播被認為是導致犢牛腹瀉發病率和死亡率顯著升高的重要因素之一[14-15]。青霉素類抗生素和頭孢菌素類抗生素作為治療大腸桿菌病的常規藥物在某些養牛場可能被過度使用。因此,有必要對由大腸桿菌病引起的腹瀉牛群進行產β- 內酰胺酶大腸桿菌的臨床細菌學檢查。在本試驗中,從腹瀉犢牛肝臟中分離純化到1 株優勢大腸桿菌,該菌株僅對PB、FR和FOX 敏感,其耐藥譜數多達20 種,即P/AMX/AM/B/RA/AN/AZT/GM/OFL/LVF/NOR/CIP/N/K/S/TE/LMF/CFP/CTX/CAZ。藥敏試驗結果證實,該大腸桿菌分離株為多重耐藥性菌株,耐藥種類幾乎涵蓋青霉素類、頭孢菌素類、氨基糖苷類、氟喹諾酮類、利福平類等臨床常用藥物,且其耐藥譜比同時期新疆自治區牛源大腸桿菌優勢耐藥譜(氯霉素/四環素/鏈霉素)[15]和秦皇島地區牛源大腸桿菌優勢耐藥譜(林可霉素/慶大霉素/阿米卡星)[16]更為寬泛。本試驗受試大腸桿菌分離株的血清型鑒定和致病性試驗將在后續試驗中開展。
目前,已有多種表型篩選和分子技術應用于細菌β- 內酰胺酶的檢測。然而,由于可能出現假陽性結果,常規的紙片協同法檢測細菌β- 內酰胺酶表型僅可作為陽性菌株的初步篩選,β- 內酰胺酶的進一步確認還需結合分子檢測手段。例如,PCR 擴增和宏基因組測序[17]可檢測相關耐藥基因;膠體金免疫層析技術[18]和酶聯免疫吸附試驗[19]可供用于檢測抗生素鈍化酶。為保證試驗結果的準確性,本試驗受試大腸桿菌分離株的β- 內酰胺酶檢測采用了紙片協同法初篩和PCR 擴增2 種試驗方法進行相互驗證。其中,紙片協同法的初篩結果表明,該分離株兼產ESBLs 和AmpC 酶陽性菌株;且經PCR 從分離株R 質粒中成功擴增出blaTEM基因片段,由此證實該分離株確實為產ESBLs 陽性菌株。近期有研究表明,在青海和寧夏地區檢測到羊源產AmpC 酶大腸桿菌的流行基因型是以質粒介導的blaCIT和blaACC基因型為主[20]。本試驗曾對分離株R 質粒介導的AmpC 酶blaCIT和blaACC基因片段進行了PCR擴增,但是并未擴增出相應的目的片段,更多AmpC酶基因型的PCR 檢測將于后續試驗中進行。目前,有研究也常使用頭孢西丁紙片進行產AmpC 酶菌株的初篩,當頭孢西丁抑菌圈直徑小于17 mm 即被認為是產AmpC 酶陽性菌株[21]。本研究分離菌株的藥敏試驗結果顯示,該分離菌株對頭孢西丁敏感,且抑菌圈直徑為25 mm,大于17 mm 的臨界值點。因此,若以頭孢西丁抑菌圈直徑標準判斷,則該分離株應為不產AmpC 酶的陰性菌株,但這似乎與APB 阻抑物基法檢測的陽性結果相互矛盾。由于腸桿菌科細菌染色體上通常攜帶誘導型AmpC 酶基因,其表達受到一個弱啟動子和一個強效衰減子系統的嚴格調控,通常只在受到外界誘導的情況下才啟動低水平表達[22-23]。而由質粒介導的、水平基因轉移的和由染色體衍生出來的非染色體AmpC 酶基因無需誘導便可持續大量表達[10,23]。據此推測,該分離株的AmpC 酶基因可能定位于染色體DNA 上,只有少量AmpC 酶得以表達,不足以鈍化頭孢西丁的抑菌藥效,使得分離菌株對頭孢西丁表現敏感,但表達的少量AmpC 酶活性卻會受到APB 的強烈抑制。因而,運用CAZ 和APB 協同效應檢測AmpC酶具有更高的靈敏性和特異性。該推測結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何本試驗未從分離菌株R 質粒中擴增到AmpC 酶的blaCIT和blaACC基因片段。但R質粒上是否有其他AmpC 酶基因型的存在,仍需進一步檢測予以驗證。
由于長期受到抗生素的選擇壓力,耐藥細菌不斷出現并逐漸在健康家畜中傳播,人類亦存在因消費畜產品而被間接感染的風險[3]。因此,如何控制耐藥細菌的傳播已成為亟待解決的世界性問題。近年來,多項研究表明,中草藥可通過消除耐藥大腸桿菌的R 質粒、抑制外排泵系統、增加外膜通透性和抑制β- 內酰胺酶活性等方式阻滯耐藥大腸桿菌的產生和傳播[24-25]。提示將中草藥作為常規飼料添加劑會對多重耐藥菌株的傳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本試驗從腹瀉犢牛肝臟分離鑒定出1 株優勢大腸桿菌菌株。該菌株為多重耐藥菌株,對絕大多數常用抗生素藥物都產生耐藥性,其耐藥譜多達20 種,僅對多黏菌素B、痢特靈、頭孢西丁敏感,提示該奶牛場可能已成為多重耐藥致病菌的貯存庫,細菌耐藥形勢較為嚴重。該分離菌株為β- 內酰胺酶陽性菌株,且R 質粒中攜帶有blaTEM型ESBLs 基因。本研究是關于山西省牛源產β- 內酰胺酶大腸桿菌表型檢測的首次報道,試驗結果將為山西省養殖業開展大規模多重耐藥致病菌的流行病學調查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