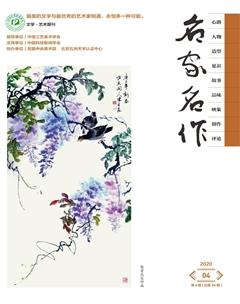電影《羅馬的房間》賞析
劉雨卉
歐洲繪畫藝術發展到文藝復興時期,光影的運用成為表達自身情感的藝術語言,同時透視技巧和對稱均勻的數理知識的加入,使得文藝復興時期的眾多作品沖破中世紀單一的線條描繪方式,畫面空間感和對稱感的構建使得繪畫作品立體而動感。在這部電影中,胡里奧采用結合了側射光和頂射的拍攝方式,使得電影本身更像是一幅油畫的“在創作”,整部影片也猶如文藝復興繪畫理論的再現,充滿了對稱之美。
在達·芬奇《最后的晚餐》中運用了極其嚴謹的透視結構,以耶穌為中心,畫面構成一個金字塔構圖,左右兩邊各自有著六個門徒;拉斐爾的《雅典學院》中整個建筑構造采用羅馬式拱頂建筑直接呈現出視覺上的對稱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身處畫面的中心構架了整個希臘世界,畫面左右在臺階下分別聚集著正在辯論的人群;米開朗琪羅的《創世紀》《最后的審判》等作品都呈現著相類似的對稱美。而在整部電影中所呈現的對稱美從電影一開頭娜塔莎和阿爾巴出現在圓形廣場時就開始展現,二人牽著手在廣場出現,陽臺上方空著的旗桿仿佛成了中軸線;娜塔莎和阿爾巴站在陽臺上時,二人畫面中間的旗桿再次成就了畫面的對稱感;當娜塔莎醒后決心悄然離去時不小心撕壞了阿爾巴的內褲,不由得笑出了聲,同樣是兩位主人公性別的對稱;包括影片結束二人的離開,頂射的視角再次出現,在畫面對稱的同時還與影片開頭形成了呼應對稱;二人站在浴室門口看著左邊象征女性權利的阿斯帕西婭,再看看右邊象征男權的阿爾貝蒂,一方面是性別的對稱,另一方面是男權女權的對稱,導演用這兩個相隔千年的歷史人物同時為娜塔莎的內心沖突做了一個暗喻,一方面是即將結婚的人生導師,猶如阿爾貝蒂一樣的全能大師;另一方面是預示追求自己內心的阿斯帕西婭,同時也是阿爾巴的象征,阿爾巴具有與阿斯帕西婭同樣的智慧,將自己發明的人力車以此命名,這樣一來便不難看出導演的意圖,男權與女權的拉扯,內心和現實的沖突,娜塔莎的內心借此獲得了外放。
導演在拍攝中對于光線的運用與繪畫技巧中光影的使用如出一轍。“光線對于空間的造型主要是通過側光、側逆光的光線形態,明暗間隔的處理手法來完成的。側光、側逆光的光線形態有利于通過明暗影調的變化表達物體的體積感,勾勒出物體的輪廓,呈現一種趣味的抽象概括,在空間中形成多層景物。 ”在繪畫中對于光線的使用分為聚集的光線、散射的光線和逆光順光三種,所謂聚集的光線即指將光線聚焦于畫面中的某一部分物體,其他物體的光則被相對弱化,如卡拉瓦喬的杰作《圣母之死》采用側光照射,圣母瑪利亞在光線的集中部分,周圍哭泣的人們則處在半明半暗之中,畫面主題昭然若揭。而胡里奧在影片結尾部分呈現的畫面與此一致:阿爾巴和娜塔莎并肩坐在房間外的露天陽臺,白色浴袍和初升的光線相映襯,鏡頭由屋內越過二人的背影探向剛露出的朝霞,轉而回到屋內,與床頭正對的文藝復興全能大師阿爾貝蒂正在畫面中講述著自己的理念,光線從油畫的右下角逐漸點亮了整幅畫面,完整的作品全貌呈現出來,緊接著畫面移動到床頭懸掛的阿斯帕西婭在雅典市集的壁畫,光線和鏡頭在阿斯帕西婭身上戛然而止,畫中多半的人處在陰影之中,仿佛注視著在這市集中出現的唯一女子,阿斯帕西婭的面容猶如圣母瑪利亞一般聚焦了所有的目光。
逆光的使用是在娜塔莎第二次向阿爾巴講述自己時,陰影下變成古銅色的胴體緩緩朝著床的那頭走去,光影追隨在她身后,隨著她遠去,隨著她轉身。逆光中隱藏的美人聲音緩緩,講述了雙胞胎中的姐姐發現妹妹和父親的不正當關系之后的落寞和排擠感,逆光環境下的幽暗、神秘和憂郁都浸入阿爾巴以及觀眾的心里。在第一次阿爾巴講述沙特阿拉伯的故事時,二人坐在阿爾貝蒂的油畫下,幽暗的燈光照在阿爾巴身上,仿佛獨自在舞臺表演獨幕劇的藝人,只有光束陪伴著的孤獨,身處席上的娜塔莎托著腮,半個身子藏在黑暗中正在聆聽。甚至包括兩人的纏綿悱惻,長鏡頭隨著燈光緩緩地從腳部向上移動,燭光般幽暗的畫面中兩具極美的身體交纏在一起,迷幻的呻吟在吉他伴奏聲中與空靈的歌喉融合,氛圍電子樂loving stranger的加入讓觀者不由得屏住了呼吸,為此驚嘆。
阿爾巴的所有物——復制品《米洛斯的維納斯》多次在影片中出現,同時在阿波羅神升起之時,娜塔莎用白色的浴袍模仿著維納斯的形態,同樣的金色長發,同樣美麗的乳房,同樣美麗的身形。在房間的天花板上抬眼望到的丘比特見證了房間內愛情的發生,伴隨著風神的出現,胡里奧用獨特的視角和藝術拍攝打破了世人對愛的偏見,創造了自己的“維納斯”。
參考文獻:
鄭亞茹.解讀“光”在油畫中的意蘊[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07.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