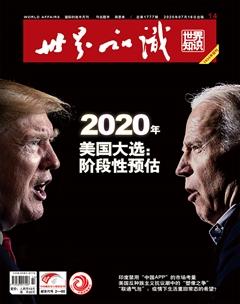美國反種族主義抗議潮中的“塑像之爭”
林玲

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再度掀起美國清除涉種族主義塑像與紀念標識的運動。圖為弗吉尼亞州首府里士滿市中心的南方邦聯將領羅伯特·李雕像。
2020年5月25日,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死。該事件引發了席卷全美的反種族主義抗議浪潮,其爆發規模、影響程度,已經超過了2014年因密蘇里州弗格森小鎮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事件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行動。在這一波反種族主義抗議聲浪中,再度出現“倒像”呼聲。隨著抗議行動的蔓延,“倒像”聲勢不斷高漲,美國多地的南部邦聯領導人和將士的塑像被相繼推倒或拆除,被民權人士視為蓄奴制與種族主義歷史產物的邦聯塑像再度成為抗議行動的矛頭所向。
邦聯塑像的由來與爭議
據美國民權團體“南方貧困問題與法律中心”統計,全美現有1500多處邦聯標志物,其中包括700多座邦聯紀念碑、塑像以及100多處以邦聯代表人物命名的街道、村鎮和公立學校建筑等,主要集中于南部各州。邦聯標志是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部邦聯的歷史產物,而南部邦聯的成因與南部的蓄奴制歷史密不可分。19世紀中期以來,南部蓄奴州與北方自由州之間一直存在著土地和物產資源的爭奪以及在蓄奴制問題上的政治理念沖突,長期積累的南北矛盾最終引發了政治危機。1861年,美國南部蓄奴州宣布退出美國聯邦,成立“美利堅邦聯”,由杰斐遜·戴維斯任邦聯總統,南北戰爭隨之爆發。1865年,南北戰爭以南部戰敗告終,聯邦政府廢除了南部奴隸制,南部邦聯也相應解體。而自19世紀末以來,隨著內戰后南北和解進程的加速,在以“邦聯之女聯合會”為代表的南部白人組織的推動下,南部各地相繼建造了南部邦聯領導人與將士的紀念碑和塑像,此后逐步擴展到一些北方州。對于推動邦聯紀念物建設的南部白人而言,這是一項偉大而神圣的建設事業,那些矗立于南部各地市中心和公共空間的邦聯紀念碑與塑像、飄揚于市政廣場的邦聯國旗寄托著他們對于南部邦聯的傷逝與懷念,也成為舊南部社會秩序的歷史見證。然而,對于眾多非裔美國人而言,邦聯紀念物則代表了蓄奴制與種族壓迫的歷史記憶,自20世紀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以來,邦聯塑像所在地往往成為民權人士抗議示威的集會地。每當美國社會出現大規模的黑白種族沖突,移除邦聯紀念物的呼聲就會應聲而起,一波波抗議聲浪的背后是不同族群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的沖撞。
2015年震驚全美的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黑人教堂槍擊案就曾引發了一輪“倒像”運動。當年6月17日,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持槍襲擊了查爾斯頓的伊曼鈕爾非裔衛理圣公會教堂,造成九人死亡,成為當地歷史上最嚴重的槍擊案。伊曼鈕爾教堂是美國最古老、最知名的黑人教堂之一,具有歷史文化象征意義,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小馬丁·路德·金就曾到訪過該教堂。槍擊事件致使2014年以來爆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行動持續升級,而事發后槍手手持南方邦聯國旗、宣揚種族仇恨照片的流傳更進一步激發了反種族主義抗議者要求移除邦聯標志物、推倒邦聯塑像的訴求。據“南方貧困問題與法律中心”2019年的統計,自查爾斯頓事件后,已有114個邦聯標志物被移除。然而,在拆除塑像風潮的背后是反種族主義者與右翼種族主義勢力的對峙,2017年弗吉尼亞州的夏洛特維爾沖突事件更加凸顯了族群矛盾的激化。2017年8月11日晚,在夏洛特維爾市議會決定移除市中心公園的邦聯統帥羅伯特·李將軍塑像之后,數百名反對拆除塑像的白人至上主義者聚集在塑像所在地,高舉帶有種族主義色彩與納粹標志的旗幟,與民權人士發生群體性沖突,一名白人極端分子開車沖向人群,造成1人死亡、19人受傷。夏洛特維爾事件后,美國各地不斷涌現移除邦聯紀念物的呼聲,呼吁重塑美國內戰史觀,還原歷史真實。
在許多非裔美國人和反種族主義者看來,在公共空間展示各種紀念邦聯將士的塑像和標志物,意味著捍衛蓄奴制的南部邦聯將士不僅被視作內戰史上的英雄,而且還占據了公眾話語的中心地位,這種代表舊南部奴隸主利益的歷史敘事理應加以改寫。在這種基于南部白人視角的歷史書寫中,奴隸制的黑暗被掩飾,黑人在內戰中的自由解放經歷被刻意抹殺,而內戰后的南北和解及主流社會輿論導向無疑為這一歷史敘事的構建開辟了空間。
南北和解與歷史記憶
美國內戰后,一種旨在宣揚南部邦聯戰爭正義性——“失去的事業”內戰史觀興起于戰敗的南部。在這一史觀中,南部邦聯對北方聯邦軍隊的戰爭是一場偉大的戰斗,旨在捍衛南部各州的“州權”與獨立自治,雖敗猶榮。而在這場戰斗中,南部邦聯軍隊最終未能抵擋實力占優的聯邦軍隊的“入侵”,致使其捍衛南部傳統社會秩序的使命遭受挫敗。20世紀初,在聯邦政府力圖促進南北雙方和解的背景下,這一“失去的事業”論調開始逐步融入聯邦政府的政治話語中。1912年塔夫脫總統出席在首府華盛頓召開的“邦聯之女聯合會”第19次全國年會,他在會議致辭中明確提出:“奴隸制度不是引發南北戰爭的主因,州權主義才是導火線”,因而“北方將士是為了維護統一而戰,南部將士也是為了捍衛獨立與自治而戰,所有的將士都是為了自由制度而戰。”塔夫脫的致辭無疑肯定了南部的“州權主義”與邦聯戰爭正義論。事實上,自19世紀末美西戰爭爆發以來,聯邦政府為了得到南部的支持,開始著手致力于促進南北雙方和解,并將對南部邦聯陣亡將士的悼念與追認納入到和解進程的重要議題中。1900年,麥金萊政府將128具南部邦聯軍隊將士遺骸莊嚴地安葬于阿靈頓國家公墓。1903年,聯邦政府舉行了首次紀念南部陣亡將士的掃墓活動,并于1905年將聯邦軍隊在內戰期間繳獲的邦聯軍旗全數歸還南部。南北和解大力推動了南部邦聯紀念物的建設。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初的南北和解進程是南部在內戰后實施種族隔離的歷史背景下推進的。1877年,聯邦政府與南部簽訂《海斯—蒂爾頓協定》,聯邦政府從南部撤軍,結束了對南部的軍管,標志著南部民主重建以南北雙方的妥協而告終。撤軍后,內戰前的白人奴隸主以地主和種植園主的新身份重新掌控了南部各州,而剛從奴隸制枷鎖中解放出來的黑人很快又淪為種植園主的佃農。此后南部各州開始陸續施行《吉姆·克勞法》,確立了種族隔離制度。1896年,聯邦最高法院在《普拉西訴費格森案》中裁定,“隔離但平等的教育設施符合憲法”,從而為種族隔離提供了法律依據。自此,19世紀末以來,聯邦政府與南部在“失去的事業”內戰史觀、“州權主義”等問題上達成了和解,而這種在南部種族隔離背景下實現的南北和解,事實上意味著聯邦政府對于南部種族隔離制度的妥協,進而助長了內戰后南部種族主義社會秩序的回歸。
“失去的事業”內戰史觀蘊含了南部白人對于內戰前奴隸制社會秩序的深切懷念,這種對于舊日南部的眷戀也時常體現在一些文藝作品中,1936年出版的暢銷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小說被視作一曲獻給舊南部的贊歌,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曾榮獲八項奧斯卡獎。然而,因作品內容包含了對舊南部奴隸制社會秩序的美化、對黑奴形象的扭曲,以及帶有種族歧視的語言,該作品和改編的電影一直備受爭議。正因為此,在當前新一波反種族主義抗議潮中,美國家庭大票房平臺(HBO)暫時下線了該電影。
塑像存廢問題引發的思考
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新一波抗議潮不僅把矛頭指向邦聯將士與領導人塑像,還波及了其他一些涉及蓄奴制與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歷史人物。在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移除了位于入口處的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塑像。塑像中老羅斯福騎在馬背上,兩旁分立著一位印第安人和黑人,塑像因此被視為含有征服原住民與黑人的隱喻。在曾經的南部邦聯首府、弗吉尼亞州小城里士滿,一座哥倫布塑像被涂鴉、焚燒后拋進了湖中,塑像沉湖處留下一張書寫著“種族主義,你不會被懷念”字樣的手繪圖。在里士滿一條歷史悠久的陳列邦聯塑像的紀念碑大道,前南部邦聯總統杰斐遜·戴維斯的塑像被抗議者推倒后,弗吉尼亞州長還宣布將拆除紀念碑大道上的羅伯特·李將軍塑像。然而,州政府的舉措遭到了當地一些居民的反對。他們將州政府告上了聯邦法庭,聲稱塑像是19世紀末建造的歷史文化遺跡,屬于當代居民的公共財產。聯邦法庭對此頒布了強制令,禁止州政府移除塑像。這一案例可以說集中體現了塑像之爭背后不同群體在理念、現實考量與訴求上的沖突。
塑像存廢不是根本問題
隨著2020大選臨近,塑像存廢問題也成為兩黨政治博弈的角力場。國會大廈的塑像廳內陳列有100座塑像,由全美50個州各指定兩座塑像在廳內展示,其中有包括前南部邦聯總統、副總統、李將軍等人在內的11座邦聯塑像。6月10日,民主黨領袖、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致信國會圖書館,要求移除這些邦聯塑像。她在信中表示,國會大廈內的塑像應該體現美國人的最高理想,以“展示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想要成為誰”,而“立碑紀念那些為了明顯的種族主義目的而鼓吹殘酷與野蠻行徑的人,是對這些理想的嘲諷與侮辱”,因此“保留這些塑像是在向仇恨致敬,并非向歷史遺產致敬”。6月18日,國會大廈內四名曾在南部邦聯任職的前眾議院議長的肖像被撤下。值得一提的是,6月19日是美國奴隸制終結155周年紀念日,佩洛西在紀念日的前一天撤下肖像,具有一定象征意義,意在表明當今民主黨人支持反種族主義抗議運動的立場。非裔美國族群是民主黨的傳統支持者,如今大選將近,民主黨人的表態與政策舉措顯然具有選舉政治上的考量。
對于如何處理邦聯紀念物及標識的問題,掌控眾議院的民主黨人與占參議院多數的共和黨人之間存在明顯分歧。而對于“倒像”運動,特朗普總統采取的是一貫強硬的態度,并強調維護“法律與秩序”的重要性。6月26日,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令,要求保護邦聯歷史建筑、紀念碑和塑像,嚴懲破壞者,同時指示美國司法部長重點調查、起訴破壞邦聯紀念物者,并警告一些沒有保護好紀念物的地方政府和執法部門,將凍結對其聯邦資金的支持。可以預見,塑像之爭所呈現的種族主義沉痼,將與司法不公、警方暴力執法等問題交織在一起,進入大選公眾議題,進一步加劇兩黨爭斗與當前美國政治的極化。
值得關注的是,在弗洛伊德事件持續發酵的過程中,美國民眾對于司法體系中存在的“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認知度顯著提升。《華盛頓郵報》6月9日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對于2014年一系列警方暴力執法事件引發的全美“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運動,當時只有43%的人認為暴力執法的根源在于種族主義,但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的民調顯示,有超過2/3的人認為,警察暴力背后有更大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因素。同樣,在當前抗議潮中“倒像”運動的蔓延也體現了公眾對于種族主義歷史根源的認識。然而,正如根除司法體系中的“系統性種族主義”需要深刻的社會變革,消除種族主義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制止警方暴力執法和推倒塑像、移除公共空間的邦聯標志物等層面。對此,美國萊斯大學“種族主義與種族經歷研究”項目主任、非裔教授托尼·布朗認為,不應簡單地移除塑像,而應該將塑像展示于特定的語境與空間,并加以闡釋,以起到警示歷史真相、提升公眾意識的作用。在這一點上,休斯頓市的做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休斯頓市政府曾將一座名為“邦聯精神”的塑像移除,這座邦聯塑像一百多年來一直矗立于該市的山姆·休斯頓公園,如今被陳列于休斯頓非裔美國文化博物館,成為博物館展覽的一部分,以告誡人們銘記種族主義歷史。因此,邦聯塑像的存廢本身不是問題的根本,而如何還原塑像所承載的歷史的本來面目,重塑歷史記憶,以構建反種族主義的社會認知,才是當今美國社會修復種族主義歷史之殤、化解種族矛盾所真正需要反思的問題。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