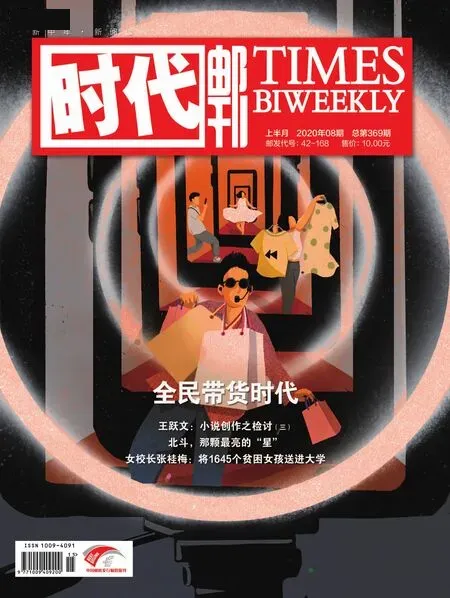民法典誕生背后的那些事
● 謝江珊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終于問世。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民法典,標志著我國正式從民事單行法時代邁入民法典時代。
民法典共7編(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加附則,84章,1260條,總字數逾10萬。
這是目前我國條文數最多的一部法律,從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包羅萬象。
5月31日,《現代法學》主編、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趙萬一說民法典具有開創性,后續可能會帶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采用“法典化”的方式進行集中調整。
“這部民法典是中國自己的民法典,具有中國自己的鮮明特色,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法治表達。不論是體例、結構還是具體內容,都不同于任何一個國家的民法典。它是社會、經濟和生活的法治基礎,沒有民法典,就無法進一步實現法治社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立法專家委員會專家楊立新表示。
人大601會議室屢次見證
“今天民法典誕生了,我心里特別高興,這也是給我的最好的生日禮物,此生再無遺憾!”5月28日,在西南政法大學舉行的“親歷見證民法典”報告會上,著名民法學家金平難掩激動。
作為參與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前三次民法典起草而唯一健在的人,金平被譽為“當代民法史活化石”。民法典表決通過的第二天,恰逢老人98歲壽辰。
我國曾在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啟動民法典起草工作,但出于各種歷史原因,民法典始終未能出臺。
1979年,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啟動,但彼時剛剛實施改革開放,制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條件尚不具備。最終,決策層決定按照“成熟一個通過一個”的工作思路,確定先制定民事單行法律。
此后,我國先后制定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民事立法,逐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民事法律規范體系。
關鍵的轉折出現在2014年秋天。當時,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應依法治國,但魏振瀛等民法學者了解到,最初公布的五年立法計劃中并未提及民法典的制定。
先由背景分析開始,通過已學的相關的知識建立初步的背景分析,接著是概念性的材料分析認知,認知完成后開始直接的知識應用實踐任務。連貫的認知過程有利于快速學習新知識,并將新知識推入學生已有的知識背景中去,形成牢固的知識網絡。在教學過程中多個新知識點的連接方式可以采用串聯逐步展現,伴隨應用的難度增加,也可以并聯一起推送,具體方式的選擇和知識點具體的難度相關,難度高的串聯較好,用逐漸增加的難度維持注意力,難度低的并聯較好,用大量低難度的知識點形成新的背景認知維持認知強度。
“那年秋天,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法學樓的601會議室,民法學者舉行了一場會議,堅持呼吁將編纂民法典作為一個國家重要的政治、經濟和生活大事,重新納入到立法計劃當中。”5月30日,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大學民商法學教授費安玲回憶道。
學者們的疾呼得到了回應。最終,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編纂民法典的任務。
此后,這間會議室多次見證了民法典的孕育過程。
2019年11月23日,還是在601會議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勝明做了一場“民事立法四十年”的主題講座。主要討論《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制定、修改,以及民法典編纂的相關內容。
42.5萬人提出102萬條意見和建議
從2014年10月第五次民法典編纂啟動,到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正式通過——1800多個日夜,令所有參與編纂的學者難忘。
2015年1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以下簡稱“法工委”)首次召開民法典編纂工作會議,提出初步立法計劃和安排,確定民法典編纂采取“兩步走”:第一步,制定民法總則,作為民法典的總則編;第二步,編纂民法典各分編,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后,再與民法總則合并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同年3月,由法工委牽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原國務院法制辦)、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法學會等五家單位各自組成民法典編纂工作協調小組。編纂過程中的協調、決策、進程等問題,都會提交到協調小組的會議上研究、討論。
關于民法典的具體編纂過程,多位民法學者透露,一般是先由學界提出專家建議稿,提交法工委參考;經過多輪討論和征求意見,法工委民法室在現行法的基礎上起草民法典室內稿、征求意見稿以及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稿;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后再面向社會征求意見,直至最終形成提交全國人大會議審議的民法典草案。
據悉,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法工委先后10次通過中國人大網公開征求意見,累計收到42.5萬人提出的102萬條意見和建議。
2016年6月,民法總則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法總則。一個月后,編纂民法典分則各編工作正式展開。
“我們參加了民法總則的編纂,最后上會前,立法專家委員會還專門開會討論過。但在民法分則的編纂上,我主要還是以學者身份參與討論并提供建議。”楊立新說,作為中國法學會“繼承編草案”起草小組的負責人,他領導的小組最初由3人組成,最多時曾達20余人。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民法典編纂工作組秘書長謝鴻飛透露,5家參與單位經常一起開工作會議,討論有爭議的問題。
討論的問題具體包括兩類:一是專業問題,由學界、司法實務界或律師界提出;二是民眾關心的熱點問題,比如離婚冷靜期、夫妻共同債務、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時間屆滿是否繳納續期費用等。
“每家參與單位都會組建一個民法典編纂小組,由一位級別較高的干部擔任組長,再配備工作人員。組長開工作協調會,跟進工作進度、協調下一步工作如何開展。工作人員開具體會議,分析討論具體條款如何擬定。”謝鴻飛介紹,他所在的社科院民法典編纂工作組,核心成員有12人左右,集中討論物權編和合同編,“我們最后提供了一個全本建議稿,共1000多條”。
謝鴻飛說,5年時間里,令他最記憶猶新的是民眾對民法典的熱心參與度。“比如婚姻法第24條的夫妻共同債務,爭議太大了。我們社科院民法所經常收到各地來信,希望廢除或者修改這一條。”
編纂民法典需要很高的立法技術,受訪的民法學者們坦言困難不少。
“大家要聚在一起琢磨。比如合同編的一個條款會對侵權編、物權編甚至婚姻家庭編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因為這個條款放到合同編合適,但可能對物權編產生不良影響。”在費安玲的記憶里,2017年至今,自己參加了10余次這樣的會議。
不斷尋找平衡點
饒是五年磨一劍,此次民法典中的一些條款仍引起較大的社會爭議,譬如“離婚冷靜期”。
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077條規定: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愿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
“初衷是好的,但離婚冷靜期的提出,我個人認為還是過于匆忙了,應該再考慮得周全一些。”在費安玲看來,離婚冷靜期的提出牽一發而動全身,將帶來一系列的社會效應。
“其實這條在寫進民法典之前,并沒有進行大數據和模型分析。當人們對婚姻產生恐懼,為了求得更多的自由,就會選擇不結婚。如果未來有大量的人都不結婚而選擇民事同居,會不會帶來更多法律上一系列的困惑或難題?”費安玲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對此,楊立新回應,離婚冷靜期設立的目的之一,確實是為了解決離婚率逐年增加的問題。
“我國目前的離婚程序過于簡單。現實中的確存在很多的草率離婚、沖動離婚的現象。”楊立新解釋道,離婚冷靜期的設立就像給離婚增加了一個門檻:離婚冷靜期的設立,為的是讓“可離可不離”的人再思考一下,“并不是限制離婚,也不侵犯離婚的自由”。
“目前離婚冷靜期的規定是30天的時間,但這個規定沒有區分特殊情況。”楊立新強調,如雙方有激烈的沖突、存在家庭暴力或者虐待的情況,“這些都不受冷靜期的限制。”
“遇到爭議特別大的問題,民法典會做一個模糊規定。比如網絡虛擬財產、大數據受法律保護,但具體怎么保護?沒有說得太清楚,留下一個很開放的空間。至于爭議更大的,就直接刪除了。”謝鴻飛進一步解釋,中國社會處于轉型階段,大家的觀點不會完全一致。“在民法典的立法中,的確缺少社會學調查,所以導致一些法律條款并不符合大多數人的觀念或者生活經驗。”
不過,正如趙萬一所言:“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部自己認為最理想的民法典,民法典的內容太廣泛,涉及的社會關系太復雜,不可能達成完全共識。而且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太快,法律與經濟現實之間必然存在一些脫節,法律不可能完全反映社會發展的需要。最終出臺的民法典,一定是經過妥協、不斷尋找平衡點的產物。”
“我們終于有自己的民法典了,雖然還有缺點,但達到這個程度已經不錯。先把它統一起來,再慢慢修訂。”楊立新最后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