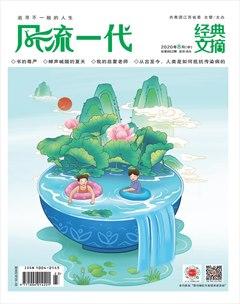蟬聲喊醒的夏天
張金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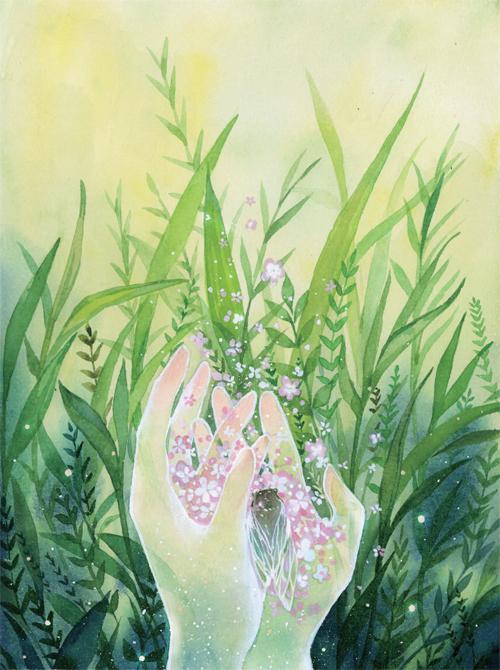
嘰嘰兒
——急先鋒唱來了夏天
鄉下人的農歷,從五月麥香開始翻開夏天的扉頁。
南風吹,麥浪金黃,烈日炙烤大地,農人躬身跟土地商量,要拿汗水做聘禮迎娶麥子回家。
天空嫩藍,香風掃盡云彩,他們勒緊腰帶,準備抬麥子的花轎。仰頭往喉嚨里灌水,眼睛被毒花花的太陽刺傷。那些水慷慨地穿過軀體,化作汗蚯蚓一樣漫過青灰的頭皮,掠過眼角,順著脖頸子淌下來,癢癢的,沿著茁壯的汗毛一路匯集,最后從塞滿黃土的腳丫落地,把那一撮黃土攪拌成泥巴。身上癢癢的,似無數個小蟲在遷徙,他撓一把,指甲縫里塞滿油灰。
這時候他們還不覺得是夏天。
打場的日子才是夏天。晌午,日頭將鋪展在場里的麥穗曬焦了。草草吃過午飯,一家老小都上了場。早先他們用連枷摔打,后來套上牲口拉起石碾子碾壓,現在是拖拉機拖著鐵磙子,一路嘩啦嘩啦叫喊著來了。摔打連枷的時候,起麥草的時候,揚場的時候,汗珠子噼里啪啦,那才真正靠近了夏天呢。
揚場的時候孩子最快樂,風將麥糠吹向一邊,飽滿的麥粒像金雨灑下來。孩子歡叫著,沖到麥粒的金雨下,伸手接住些麥粒,或者直接躺下來打滾,任由麥粒打在身上。這時候,一陣風里,若有若無的叫聲抵達他的耳朵,他跟娘說,有嘰嘰兒了。娘說,又是那個急先鋒吧。大人們通常聽不見這時節的蟬鳴,他們眼睛里耳朵里都是麥子歡快的喧鬧。孩子卻從此每天都在追著那個急先鋒遙遠的絲線一般的鳴叫。
鄉下孩子有個特殊的假期,一到“過麥”學生們都放麥假。“過麥”就是收麥子的這一段時間,是農人最辛苦緊迫的農事時段。小孩子跟在田里拾麥穗,長時間站在日頭下就曬得打蔫。他看著白花花的麥茬,眼花了,分不清麥穗和麥根,耳朵也在嗚里哇啦叫喚,是嘰嘰兒叫吧,他陡然精神一振,抬頭望望地頭綠葉簇新的白楊和槐樹,再聽,卻沒有了聲音,那聲音仿佛又在遠處。但他確信是嘰嘰兒來了,心頭一陣歡悅:這個急先鋒。此時,拾麥穗的苦累似乎也減輕了。
嘰嘰兒是形體最小的蟬,每年來得最早,麥芒黃的時候就來打頭陣了。它的幼蟲像食指的指尖般大小,爬出泥土時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泥猴子似的,即便是沒有泥,人也不容易發現它,它的外衣本身就是土色的。孩子們叫它“嘰嘰兒龜”,喜歡捉活物的孩子一般不去捉嘰嘰兒龜,它太小,太憨,可憐巴巴地剛爬出地面就迫不及待找個地方蛻皮。在樹干的底部,在蒿草上、蒼耳棵上,一段干樹枝上,甚至是碌碡上,它似乎預知世間有無數風險,要趕緊蛻去舊衣長出翅膀。捉它干什么呢,養著它就是養著熱鬧的夏天,孩子對這個急先鋒充滿寵愛和善意。孩子們喜歡捉的是“知了龜”,因為它碩大,一團肉,好吃,但嘰嘰兒龜是不能吃的,大人說,吃了嘰嘰兒龜就會耳聾。誰要截留夏天最美的音樂,誰就不配再傾聽自然的音階。
在麥香的風里,在人們善良的養護里,嘰嘰兒的叫聲越來越茁壯。麥子入囤,農人蒸了雪白暄騰的饅頭敬完天地,嘰嘰兒就玩命地叫來了夏天。
嘰嘰兒形體小,灰色的腰身和翅羽,憨厚木訥,常常不往高枝上去,也不善于扯樹葉隱藏,它伏在一人高處的柳樹上,伏在槐樹的橫斜枝杈上,有人看見它就忍不住去撲,它也不飛,把翅膀當成了紗裙,而是在樹干上小步快挪著,繞到另一側躲避。
夏天是從蟬歌開始的,粉墨登場的夏日名伶或豪放或婉約,或凄清孤絕,或音絲潺湲,熱鬧著夏日的舞臺。這些舞臺角色里,最單薄、身量最小的是嘰嘰兒,它這個急先鋒其實像戲劇里的配角,最早出場,是為了鋪排劇情,引出主角。嘰嘰兒的音調好似青衣,小家碧玉那種,娓娓而唱、嚶嚶而啼,有時候也底氣十足,拼了命要撕破夏天的熱幕,這又使人聯想到那些夾腰罵街的小女人。它聲音尖細,腔調直,叫得很努力,像麥秸草燎烤著的熱鏊子,如針尖一般刺透悶罐一樣的夏日。
伏天啦
——熱浪頂峰的宣告者
蟬的家族成員眾多,它們的夏天好像一臺大戲劇,生旦凈末丑,一個也不缺,你唱我唱,熱熱鬧鬧。假如嘰嘰兒與馬知了琴瑟和諧,夫唱婦隨,夏日的歌吟就少了跌宕的風情,好故事要一波三折,鄉村夏日的蟬歌也紛繁多變。
“伏天啦”的出場,打破了二聲部的和諧。身量適中的伏天啦是在天氣最熱的三伏之初出現,它像一個敲著銅鑼的宣告者。“當當當,伏天來了。”這位歌者身量適中,衣飾講究,頗有紳士風度。它個頭兒介于馬知了和嘰嘰兒之間,出土時間比前兩者晚,身體顏色黑中帶土黃,翅薄如紗。
比伏天啦更晚出場的是“聞友”,它的肚子和翅翼略帶淺綠,鄉下人用它的叫聲標志田園收獲,只要聞友叫,瓜田里的西瓜就熟啦。伏天啦和聞友這兩種蟬的叫聲復雜,都是多音節發聲,頗有古風的平仄感,而且很講究節奏。伏天啦唱的是華爾茲,慢三步,這三拍子的歌謠聽著聽著就讓人腳底發飄,恨不得跟著旋轉一番,連庭院里的雞都優雅地要跳芭蕾舞了。聞友的歌唱最跌宕,它將最簡單的類似聞友的兩個發聲闡釋得仄平仄平仄仄平,像一首從古卷中走來的七律。
聞友不僅音韻跌宕優美,智商還高,它特別狡猾,總是不停地變換唱歌的舞臺,這里唱一段,那里唱一折,好像游吟詩人,當聽者還沉浸在它歌聲余韻里的時候,它一展翅膀飛走了。各類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則,嘰嘰兒的低處快速蛻變和聞友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都是物種繁衍的本能。
祖母在綠槐下搖著蒲扇常常講這四種蟬的故事:嘰嘰兒是個漂亮的女孩,她父母包辦婚姻,將她許配給馬知了,嘰嘰兒看不上這個傻大個子,就天天嘰嘰嚶嚶地啼哭,后來終于跟她的意中人伏天啦私奔了,馬知了就張開大嘴喳喳大哭,伏天啦得了嘰嘰兒很高興,天天唱著“可得了、可得了”。聞友是旁觀者,它去勸馬知了說:“不要不要吧,不要不要不要吧。”
這故事讓孩子們聽得入迷,他們沿著吵鬧的音階,仔細辨聽它們各自的叫聲,覺得真是太像了。
夏日午后,人們懶懶地搖著大芭蕉葉蒲扇,倦倦地聽蟬。混沌的云,低壓在窗前,悶濕的屋子里,地面泛上一層水珠兒,蟬的叫聲嘶啞而黏稠,叫人更煩躁。于是盼望一場透雨,雨下透了天才不會悶熱。濃云墨似的聚攏了來,幾道亮閃,幾個響雷,雨就下來了。雷電交加的混聲合唱里,其他聲響都消匿了,那蟬在雨中會怎么樣呢?一樹葉子能遮蔽它的小巧軀體嗎?電閃雷鳴的夏日,等待已久的清涼,爆裂的青春懸掛瀲滟的彩虹。驟雨初歇,檐下珍珠閑掛,如漁舟唱晚,一湖淡然寧靜,霧靄模糊了簫曲,輕風吹來花香,蟬音竟然無恙,仍從花香中裊裊飄來。
(摘自“小十月OctoberKids”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