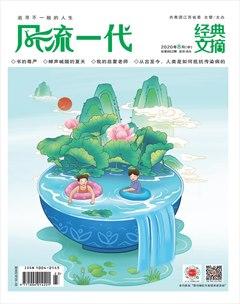“地球獨(dú)子”的故事
于丹


2011年,即將升空的“天宮一號(hào)”目標(biāo)飛行器曾面向全國(guó)中小學(xué)生征集實(shí)驗(yàn)搭載方案。其中,上海市幾名高中生提交的“搭載瀕臨滅絕植物種子”的方案被采納,四種瀕臨滅絕的植物種子與“天宮一號(hào)”一起,飛向了神秘的太空。
生長(zhǎng)在中國(guó)的“地球獨(dú)子”
如果要選一種植物上太空,你會(huì)選擇哪一種?是一到秋天便將世界染成金黃的銀杏?還是世界三大主糧之一的水稻?是花中之王牡丹?還是能夠治愈瘧疾的黃花蒿?每個(gè)人或許都有自己心中的答案,對(duì)于選擇的標(biāo)準(zhǔn),也能說(shuō)得頭頭是道。但在2011年,伴隨著“天宮一號(hào)”發(fā)射升空的植物之一,想必很少有人認(rèn)識(shí)——它的學(xué)名叫作普陀鵝耳櫪。
翻開《中國(guó)植物志》,對(duì)普陀鵝耳櫪的描述是這樣的:?jiǎn)棠?樹皮灰色;小枝棕色,疏被長(zhǎng)柔毛和黃色橢圓形小皮孔,后漸無(wú)毛而呈灰色;葉厚紙質(zhì),橢圓形至寬橢圓形……從這種標(biāo)準(zhǔn)的植物學(xué)描述中,好像還是找不到它能夠上太空的理由。但如果提起它的另一稱謂“地球獨(dú)子”,一切似乎就變得順理成章。普陀鵝耳櫪目前全球僅存的唯一一株野生古樹就生長(zhǎng)在中國(guó),它被《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列為極危等級(jí),也是國(guó)家一級(jí)重點(diǎn)保護(hù)野生植物。
“地球獨(dú)子”和它的同伴們,原本一直生活在我國(guó)浙江舟山群島上,可以說(shuō)是土生土長(zhǎng)的中國(guó)特有植物。人們還不清楚這個(gè)物種是什么時(shí)候從更大的家族中分化出來(lái)的,又經(jīng)歷過(guò)了怎樣的風(fēng)雨一直存續(xù)至今,但可以肯定的是,“地球獨(dú)子”如今成為整個(gè)家族僅存的獨(dú)苗,與人類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從未見過(guò)的奇異之樹
故事還要從大約90年前講起。那個(gè)時(shí)候,因?yàn)橐淮闻既坏臋C(jī)緣,普陀鵝耳櫪在植物分類學(xué)中擁有了自己的位置,并開始被世界所認(rèn)知。最初發(fā)現(xiàn)它的植物學(xué)家,叫鐘觀光。他本是一位致力于實(shí)業(yè)救國(guó)的青年志士,先后創(chuàng)辦了四明實(shí)學(xué)會(huì)、靈光造磷廠,還創(chuàng)辦了《科學(xué)世界》雜志,建立了上海科學(xué)儀器館,為我國(guó)近代科技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xiàn)。如果不是因?yàn)楹髞?lái)罹患肺癌,鐘觀光也許就不會(huì)與植物打上交道,更不會(huì)與普陀鵝耳櫪相遇。
在鐘先生患病療養(yǎng)期間,他對(duì)植物學(xué)研究產(chǎn)生濃厚興趣,并由此開創(chuàng)了我國(guó)學(xué)者自己采集和制作標(biāo)本,并進(jìn)行分類學(xué)研究的新時(shí)代。1930年前后,鐘先生在考察浙江東南沿海島嶼時(shí),在普陀山發(fā)現(xiàn)了一棵他從未見過(guò)的樹。這棵樹樹杈成雙,雌雄異花,雌花為淺紅色,雄花為淡黃色,很是特別。1932年,經(jīng)植物學(xué)家鄭萬(wàn)鈞教授鑒定,這種樹屬于樺木科鵝耳櫪屬,因?yàn)閮H生于普陀山,所以取名普陀鵝耳櫪。在普陀鵝耳櫪被命名的時(shí)候,這個(gè)家族的成員還散布于普陀山各處。但因?yàn)樯鲜兰o(jì)50年代大規(guī)模的毀林開荒,普陀鵝耳櫪的家族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僅殘存一棵野生古樹,生長(zhǎng)在普陀山慧濟(jì)寺,如今已經(jīng)有200多歲的高齡。這棵古樹身高約14米,直徑約60厘米,枝枝杈杈地向周圍伸展出大約72平方米的遮陰面積。隨著樹齡的增長(zhǎng)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變化,普陀鵝耳櫪家族最后的成員,逐漸顯露出衰老的跡象。在同伴們一一離去后,它的余生似乎也已經(jīng)沒(méi)有任何懸念——在慧濟(jì)寺的香火氣中,在誦經(jīng)聲中,安靜地度過(guò)風(fēng)燭殘年。等到它離開這個(gè)世界時(shí),地球上就再也沒(méi)有普陀鵝耳櫪這個(gè)物種。
因?yàn)槿祟惖陌l(fā)現(xiàn),這種植物第一次擁有了自己國(guó)際通用的學(xué)名;因?yàn)槿祟惖母蓴_,它的存在可能很快就會(huì)從這個(gè)世界上被抹去;也因?yàn)槿祟惖恼龋暗厍颡?dú)子”的命運(yùn),出現(xiàn)了新的轉(zhuǎn)機(jī)。
幫助“地球獨(dú)子”繁衍
從上世紀(jì)80年代開始,杭州植物園、浙江省林科院等多個(gè)單位的科技人員,開始了拯救普陀鵝耳櫪的工作。作為普陀鵝耳櫪家族的唯一幸存者,生長(zhǎng)在慧濟(jì)寺旁的這棵古樹,開始得到人們的悉心照料。為了時(shí)刻關(guān)注它的健康狀況,甚至有專職的護(hù)林員負(fù)責(zé)古樹的管護(hù)工作。如今,羸弱的“地球獨(dú)子”逐漸煥發(fā)出蓬勃生機(jī),已經(jīng)能夠年年開花結(jié)實(shí)了。
但整個(gè)家族的生存危機(jī),并沒(méi)有因?yàn)椤暗厍颡?dú)子”的老樹開花而緩解。究其原因,是普陀鵝耳櫪的生殖策略,使它在繁衍后代方面毫無(wú)優(yōu)勢(shì)可言。
每年四月,是普陀鵝耳櫪開花的季節(jié)。它的花雖然雌雄同株,但雄花一般在四月中上旬開花,雌花一般在四月中下旬開花,由于花期重合時(shí)間短,雌雄花相遇往往只有九天時(shí)間。一年之中,生命的大門僅在這九天之內(nèi)打開,但偏偏雌花總是高高在上,長(zhǎng)在樹冠的頂部,而在樹冠上、中、下均勻分布的雄花序,要想借風(fēng)力將花粉送上雌花的高枝,又是一重考驗(yàn)。本以為普陀鵝耳櫪的求子之路已是難上加難了,無(wú)奈天公也不作美。往往花粉還未到達(dá)雌花,就趕上舟山群島的亞熱帶季風(fēng)氣候。降雨和大風(fēng),以及隨之而來(lái)的堿性浮塵,讓雄花和雌花這對(duì)苦命鴛鴦極難成功受孕。即使勉強(qiáng)結(jié)出種子,100粒中,飽滿的也只有2到4粒。也許是過(guò)于擔(dān)心自己的孩子會(huì)遭遇什么不測(cè),普陀鵝耳櫪的種子種殼厚而堅(jiān)硬,很難自然萌發(fā)。在這位“地球獨(dú)子”的腳下,從未發(fā)現(xiàn)有天然更新的小苗。
為了幫助“地球獨(dú)子”繁衍后代,科學(xué)家們使出了渾身解數(shù),與普陀鵝耳櫪的保護(hù)和繁育難題死磕數(shù)十年。今天,普陀鵝耳櫪的繁殖難關(guān)終于被攻克了,收獲了上萬(wàn)株人工育種的樹苗,并在各相關(guān)部門的共同努力之下,走出普陀山,在全國(guó)多家植物園里落地生根。但對(duì)于科學(xué)家們而言,要真正拯救一個(gè)物種,僅僅在數(shù)量上取得優(yōu)勢(shì)還不算成功,基因?qū)用娴姆睒s也至關(guān)重要。遺傳多樣性,對(duì)一個(gè)物種而言,意味著它所擁有的持續(xù)進(jìn)化的潛力有多大,以及它的家庭成員面對(duì)劇烈變化的氣候環(huán)境時(shí),被一網(wǎng)打盡的風(fēng)險(xiǎn)有多高。科學(xué)家們研究后發(fā)現(xiàn),盡管“地球獨(dú)子”已經(jīng)擁有了很多后代,但它們的遺傳多樣性卻很低。也許一場(chǎng)災(zāi)難,就會(huì)將普陀鵝耳櫪再次推向滅絕的邊緣。于是,為了激發(fā)普陀鵝耳櫪遺傳變異的活力,它的種子搭乘著“天宮一號(hào)”飛向了太空……
如果人類曾經(jīng)對(duì)一個(gè)物種犯下過(guò)幾近滅門的罪過(guò),不知這樣全力拯救,是否能夠贖罪?今天,在人們的不懈努力之下,那棵生長(zhǎng)在慧濟(jì)寺中的“地球獨(dú)子”,它的腳下,也長(zhǎng)出了人工促成的天然更新幼苗。也許有人會(huì)問(wèn),為什么要如此不遺余力地去拯救一種看似注定要滅絕的植物呢?值得嗎?這個(gè)問(wèn)題如果放在以前,大概需要如此這般論證許久,才能夠顯得足夠有說(shuō)服力。但是放在當(dāng)下,放在2020年這個(gè)人們無(wú)數(shù)次想要重啟的“魔幻之年”,似乎問(wèn)題的答案已經(jīng)顯而易見了。澳大利亞的大火,波及世界的新冠肺炎,東非的蝗災(zāi),南極地區(qū)破紀(jì)錄的最高溫度……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一再感受到人類的渺小以及生命的偉大。
如果大自然母親要給今天的人類上一課的話,那么2020年開年發(fā)生的一切,大概是最殘酷、最令人心痛的一次自然教育了。如果我們需要從這節(jié)課中學(xué)到些什么的話,也沒(méi)有什么比“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更重要的了。
(摘自2020年3月10日《北京晚報(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