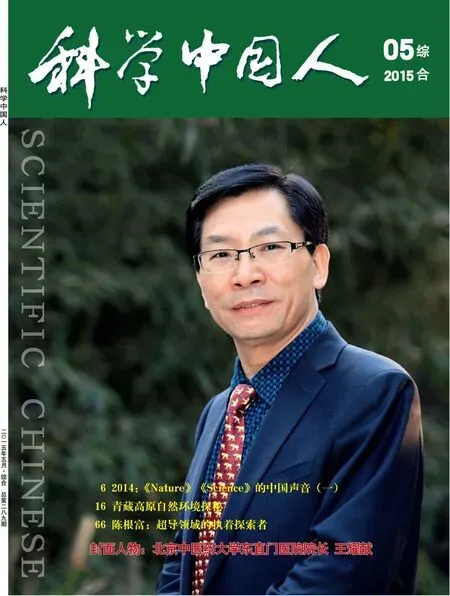程鑫:追逐太陽狂暴之謎
徐芳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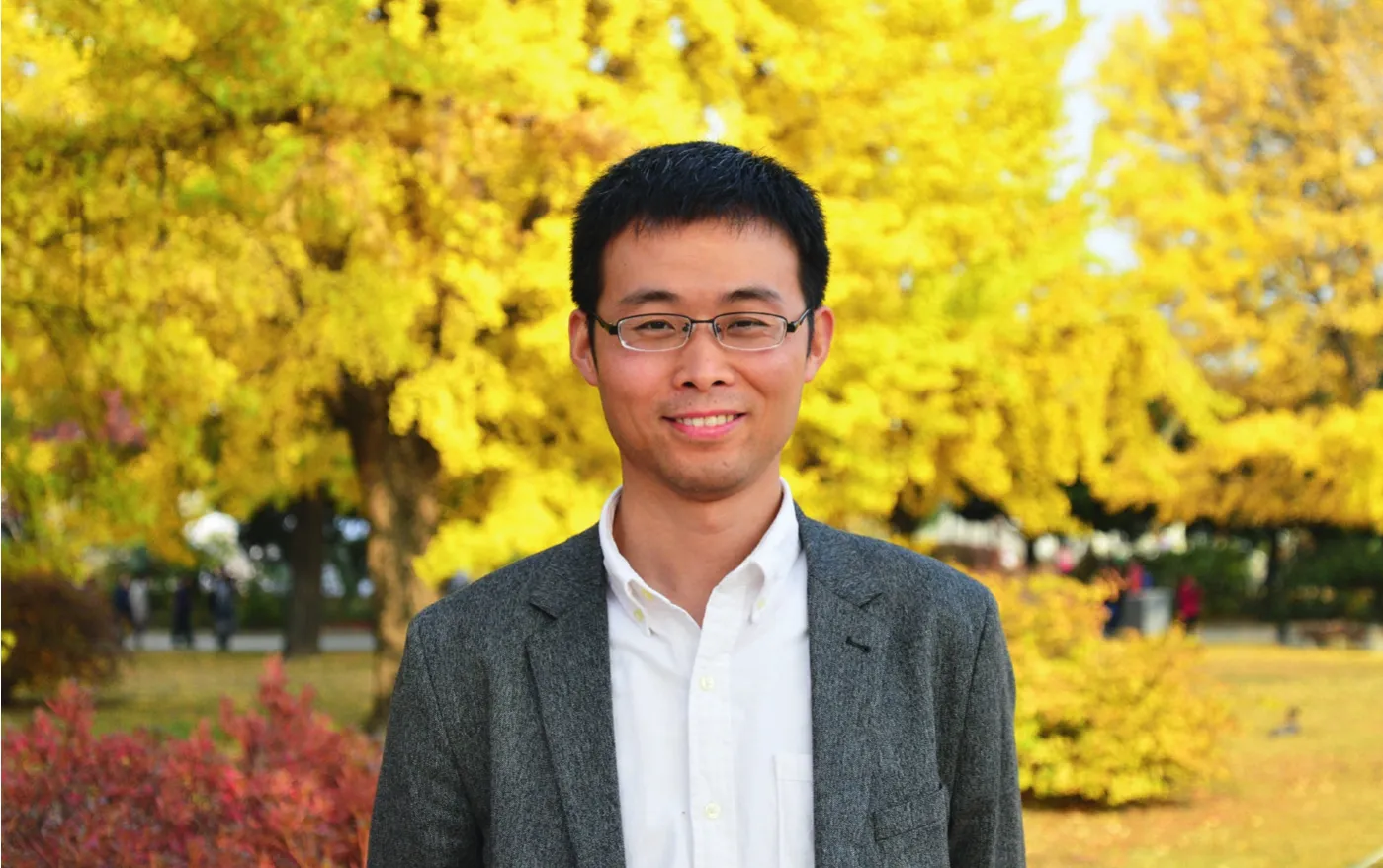
程鑫
太陽讓地球擁有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色,但在更近的觀察距離上它卻具有狂暴的一面。它的外層——日冕,是一個炎熱且充滿活力的地方,在那里會不斷發出帶電粒子流形成太陽風,更會有太陽系中最大尺度的爆發現象——日冕物質拋射(CME)發生。CME發生時,數十億噸磁化等離子體爆炸噴發的物質會對地球產生影響,損壞衛星的電子器件,殺死在太空漫步的宇航員,大的風暴甚至會使電網中斷。所以研究CME的起源和演化不僅對理解太陽活動現象的本質有重要意義,而且對能否提高空間天氣的準確預測能力也很關鍵。為破解太陽狂暴之秘,不少人正在為此前赴后繼,南京大學天文與空間科學學院副教授程鑫也是其中的探秘者之一。
太陽上捕捉“磁繩”
關于CME的起源,科學家們猜測,可能與太陽活動區存在著的巨大“磁繩”有關,這種“磁繩”可能正是引發太陽風暴的罪魁禍首,但“磁繩”是否真的存在一直沒有定論,因為它的演化速度極快,可見時間極短,要捕捉到它并非易事。盡管如此,程鑫還是發現了它。捕捉到“磁繩”時,他還是南京大學天體物理專業的一名在讀博士生。
在太陽上捕捉到“磁繩”,發生于2011年。當時程鑫正作為南京大學天文系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物理、天文與計算科學學院聯合培養的博士在美國跟隨張捷教授做CME的觀測工作,發現“磁繩”對程鑫來說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赴美之前,程鑫針對“磁繩”其實已經開展了一些工作,并且他一直在思考著一個問題:“CME到地球附近時,的確能探測到磁繩,但是在太陽附近,雖然大多數文獻都認為CME是‘磁繩’,但在沒有日冕磁場直接測量的情況下,這一觀點并不能完全說服我,所以我一直在尋找證據來證明這件事情。”
當時張捷教授的研究方向正好與程鑫的興趣相吻合,更幸運的是2010年2月美國航天局剛剛發射了一架名為“太陽動力學天文臺”的觀測器,其攜帶的大氣綜合成像儀每隔10秒對太陽拍一次照,所得數據正是張捷教授和程鑫感興趣的。
“每天早上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電腦看數據,看那些在太陽不同部位發生爆炸時拍的照片。有一天在一個高溫波段我看到一個很有意思、以前從來沒見過的結構,就拿給張捷教授看,我們看了好多遍,討論了很多次,但都不敢相信這可能就是‘磁繩’。后來經過深入的數據分析,我們達成一致,確定這可能就是大家一直在找的‘磁繩’。”程鑫回憶。
通過這次觀測,程鑫首次發現了磁繩在CME爆發之前已經存在的證據——在極紫外波段表現為一個扭曲的高溫熱通道結構,并發現在爆發過程中,這一高溫磁繩會被進一步增強,并控制CME的形成和早期動力學過程,這些發現極大推進了學界對CME物理機制即磁繩核心作用的認識。相關文章發表以來,不僅他們為磁繩存在特征命名的“熱通道”一詞被國內外大多數太陽物理學家所使用,而且引發了國內外很多團組利用SDO數據研究磁繩的興趣。
程鑫說也沒想到這項工作會產生那么大的影響,當時只是覺得有意思,看到大家都關注這件事情時,他心里還是非常開心的。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多年過去,程鑫的研究已向CME爆發領域的深處邁進,而他對科研的熱情和執著卻始終如初。因為興趣選擇了現在的工作,因執著他也收獲了一些成果。因在CME爆發領域的一系列成果,程鑫獲得美國地球物理學會“Basu獎”和第五屆“黃授書獎”。提到獲獎的事情,程鑫反而有點不好意思,他說:“比我優秀的人多得是,我今后還需要更加努力”。
從2007年進入南京大學天文系讀研究生至今,在天文與空間科學領域堅持了13年的程鑫,一路走來也并非一帆風順,幸而有諸多前輩,尤其是恩師長江學者丁明德教授的一路扶持。當遇到困難時,他更是時常會想起父親去世前對他說的話:“你該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出身農村的程鑫,家里本不算富裕,大學快畢業,父親又查出患了癌癥,這種情況下程鑫本想放棄自己讀研的夢想出去工作,是父親的堅持改變了他的想法,繼續走上求學的路。

太陽爆發圖解
進入南京大學天文系讀研究生期間,程鑫選擇了自己喜歡的研究小組——太陽組。本科學物理專業的程鑫,一開始對天文一無所知,為了盡快適應這種轉變,明確自己的研究目標,他用了大半年時間把近10年太陽爆發領域頂級雜志上的代表性文章都看了一遍,最后找到了自己感興趣的方向——CME,并一直堅持研究至今。
程鑫的母親常說他的性格很倔,但他認為“倔”是對所喜歡事情的一種執著:“倔勁兒用到科研上,別人可能輕易放棄的事你如果能堅持下來可能就有了新的發現”。
可能跟每個人的成長經歷有關,人不可能跳出自己的經驗去思考問題,帶學生也一樣,程鑫會用要求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學生,他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先提出問題再想辦法解決問題,同時也必須非常努力。
現在,程鑫已是一位父親,日常他必須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平衡,幸好有妻子的全力支持,這讓程鑫有了更多時間投入科研工作。當問到程鑫未來的目標是什么時,他說是帶領研究生在太陽爆發領域多取得些突破性的成果,為我國空間天氣預報提供理論支撐。
“使者”助力未來研究
科學研究離不開高質量的數據,尤其對太陽和空間物理、空間天氣學而言。程鑫介紹,為揭開籠罩在太陽頭上的神秘面紗,獲取高質量數據,人類朝太陽派出了不少“使者”。自1995年起,包括SOHO、TRACE、RHESSI、Hinode、STEREO、SDO、IRIS等太陽觀測科學衛星被相繼發射,這些科學衛星各個身懷絕技,除TRACE和RHESSI已退役外,其他5顆衛星都在軌正常運行,繼續為人類揭示太陽的奧秘。
讓程鑫興奮的是,2020年2月10日,歐洲航天局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攜手研制的“太陽軌道飛行器”(以下稱“太陽軌道器”)成功發射,它將首次從高緯度給太陽拍照,揭示太陽極區磁場的奧秘。“這是繼2018年升空的‘帕克’太陽探測器(以下稱‘帕克’)后,人類近期朝太陽派遣的第二位使者。‘帕克’比‘太陽軌道器’能更近距離觸摸太陽,研究太陽風如何產生,但缺點是它沒有相機給太陽爆發源區拍照;而‘太陽軌道器’可以彌補這個缺點,它與太陽距離適中,能對太陽進行遠程拍照及原位測量。‘太陽軌道器’將與‘帕克’雙劍合璧,刷新我們對太陽爆發的認識。”
然而“太陽軌道器”的成功發射,并不意味著人類探測太陽腳步的停歇。未來10年,人類還將發射更多太陽探測衛星,中國的“先進天基太陽天文臺”(ASO-S)和南京大學的“Ha望遠鏡”就是其中兩個。
據程鑫介紹,ASO-S是我國太陽物理界自主提出的一個太陽空間探測衛星計劃。它以太陽活動第25周峰年作為契機,將實現我國太陽衛星探測零的突破。ASO-S的科學目標簡稱為“一磁兩暴”,“一磁”即太陽磁場,“兩暴”即太陽上兩類最劇烈的爆發現象——耀斑爆發和CME,即觀測和研究太陽磁場、太陽耀斑和CME的起源及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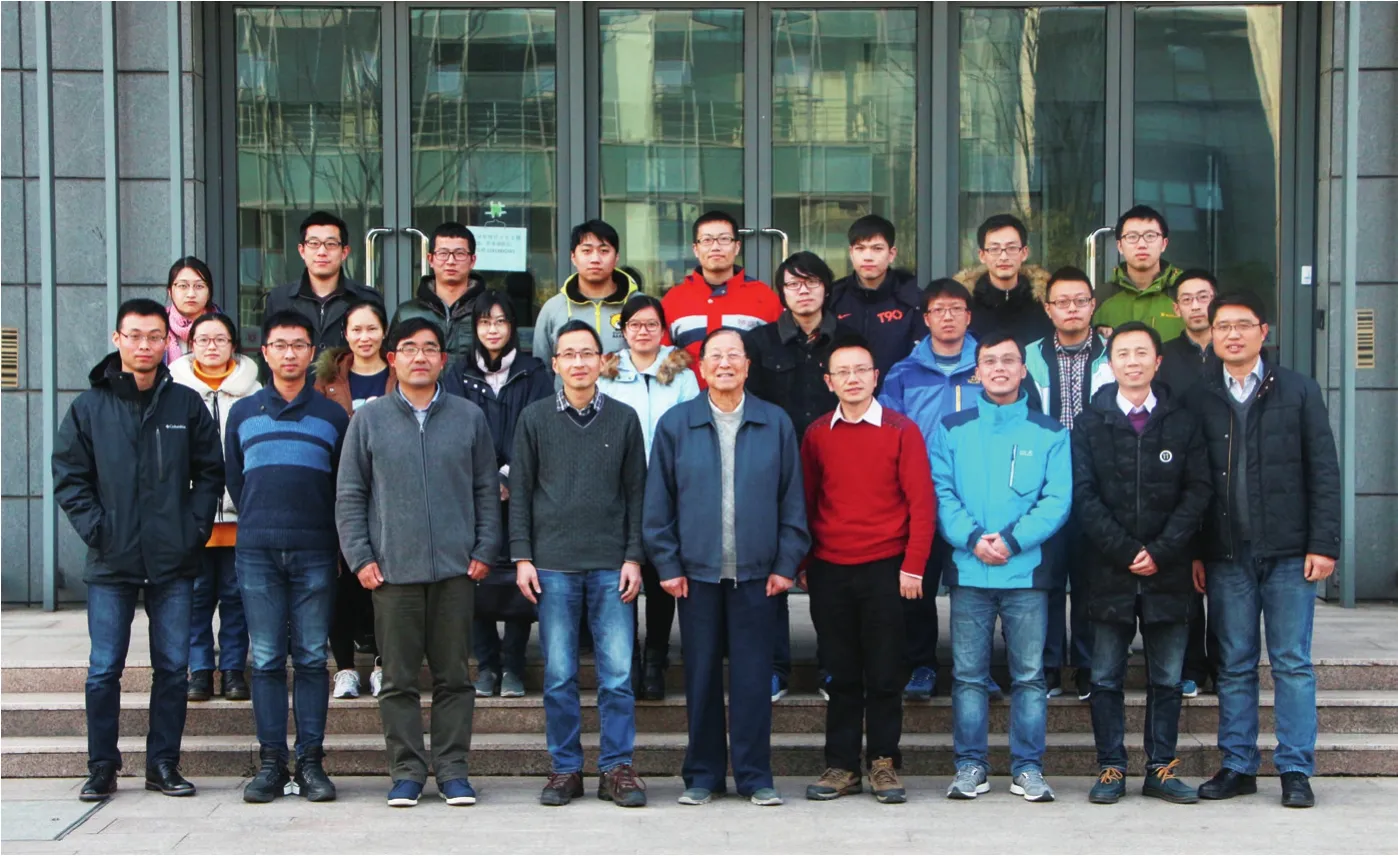
南京大學太陽物理課題組合影
為實現這樣的目標,ASO-S上共安排了3個主要載荷:全日面矢量磁像儀用來觀測太陽光球矢量磁場;太陽硬X射線成像儀用來觀測太陽耀斑非熱物理過程;萊曼阿爾法太陽望遠鏡主要用來觀測CME的形成和早期演化。ASO-S獨特的載荷組合將首次實現在一顆衛星上同時觀測太陽全日面矢量磁場、太陽耀斑高能輻射成像和CME的近日傳播,力爭在太陽物理前沿領域“一磁兩暴”觀測和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揭示太陽磁場演變導致太陽耀斑爆發和CME的內在物理機制,在拓展人類知識疆野的同時,也為人類生存環境有重大影響的空間天氣提供預報的物理基礎。
有這些太陽觀測設施的助力,程鑫對未來的研究充滿信心。在接下來的工作中,他將把CME的初發、CME磁繩的三維演化、磁重聯物理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幫助提高當前空間天氣的預報水平。另外,基于太陽爆發的研究經驗,他也將探索類太陽恒星的爆發過程。程鑫說:“我們不能阻止太陽風暴,就像不能阻止地震和火山爆發一樣。但是,我們卻可以提前預報它,將危害減至最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