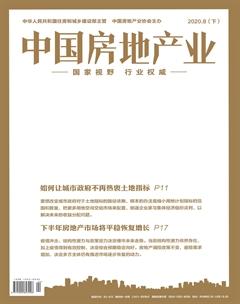如何讓城市政府不再熱衷土地指標
李鐵

前一段時間,中央連續頒布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等文件,都提出了關于土地等資源要素按照市場規律配置的政策目標。
但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還是習慣于上級政府下達的用地計劃指標。即使目前一些學者們提出的所謂改革方案,也還是在土地指標的區域的分配格局上做文章。
例如,是否要多給經濟發達地區一些土地指標?是否要增加一些城市的發展空間?即使在涉及西部大開發的問題上,城市政府也是希望中央能夠多給一些政策支持,特別是用地指標的支持,甚至還提出新的擴張性空間發展規劃。
土地制度是城市發展的初始動力
我曾經在達沃斯論壇上和印度、巴西等國的部長們交流,他們最大的感慨是,他們的國家最無法學習的就是中國的土地制度。在他們看來,如果可以按照中國的土地制度去征用土地,那么發展速度一定會趕上中國。
了解一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知道,城市高速擴張的時期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以后,當時實行了土地指標的計劃分配管理制度,同時關閉了6000多個縣以下工業園區,確保了各級城市的發展用地。
那么,為什么說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制度?因為各級城市政府的征地成本太低了。低征地補償標準曾經實行了20多年,主要就是以畝來計的青苗補償費,最多就是以此為基礎翻幾倍。相對于工業發展的收益來說,這么低的征地補償費幾乎等于無償征用。即使后來補償標準得到較大幅度提高,但是相比于之后服務業發展和房地產發展的收益,以及城市政府可以拿到的土地出讓金,可以說仍是九牛一毛。
極低的土地征用和開發成本,形成了城市發展的初始動力。可以這么說,中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可以低成本獲取土地。雖然后來土地征用的成本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有了房地產開發的征地,可以通過更高的土地開發收益對于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進行高額補償。但是按照計劃分配的農地征用指標,仍在是以青苗補償費為基礎,相比于工業發展和房地產發展,以及土地出讓金的收入,還是天差地別。
城市政府之所以熱衷于拿到國家分配的用地指標,是因為拿到指標就等于拿到了低價征地的“尚方寶劍”。也就意味著,可以借著征地機會,大量占用非基本農田開發“公益性項目”,比如興建工業園區或者新區,這能大大減少補償成本。
這樣一來,城市政府就可以零地價,甚至負地價招商引資。工業投資者則可以有充分的選擇空間,誰給的成本最低,哪里得到的好處最多,就在哪里投資。
我記得過去下地方調研的時候,當地市長和我講,某家著名的汽車生產商同時在和6個城市進行談判,條件是零地價、一定年限的退稅、幫助獲得銀行貸款等等。為了爭取到這家公司的投資,幾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還愿意提供基礎設施和廠房。也就是說,企業家只要有了投資項目,甚至可以不用在前期建設上投一分錢,直接拎個包就能來,來了就能在這個地方大展身手,賺得盆滿缽滿。
為什么可以如此不計成本向投資者提供土地?原因在于城市政府可以拿到兩塊收益:一個是未來企業投資后產生長期稅收,可以確保城市政府行政機構運轉的資金來源;另一個是可以通過房地產開發獲得土地出讓金收益,完全可以補償因吸引工業投資而付出的成本,同時還能剩余足夠資金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算了這筆賬后就能知道,城市政府向投資者提供低成本用地,表面上看似是虧本,實際上有利可圖,畢竟財政稅收和土地出讓金是城市政府最大的收入來源。
很多研究者把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歸結于市場的發育,以及企業家群體的崛起。不可否認,他們確實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沒有政府劃撥或者低價提供的土地等相關要素資源的支持,那么企業發展的初始成本就會大幅度提高。
其實,政府不僅僅提供了低價土地,還通過做農民的工作,解決失地農民的補償和安置問題,大大減少了企業的社會成本和負擔。
城市政府為什么依賴土地指標
因利益所在,對于城市政府來說,土地就是經濟發展的生命線,就是預算內和預算外資金的聚寶盆。因此,城市政府爭取所謂的發展權,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每年下發的用地計劃分配指標,因為只有計劃內的用地指標可以直接占用耕地,而且能以最少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
雖然在本世紀初,有關部門也推出了城鎮建設用地增加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的政策,但是這種做法要占用的是大量農村住宅,相關的補償標準和安置標準,則遠遠超出了占用耕地的補償標準。特別是在大城市郊區,推進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不僅要解決農民的搬遷和新房的建造,而且涉及到就業安排和各類資金補償,還面臨著各類拆遷糾紛等。因為征地成本高,這類用地更多適用于房地產開發,因為能夠賣給開發商,補償標準就可以提高。雖然政府能從中獲得豐厚的土地出讓收益,但相比國家下達的計劃內的用地指標,征地的成本還是增加太多。
各級城市政府都熱衷于降低用地成本。與獲取農村不同類型建設用地、城市閑置用地相比,無疑,通過國家下達指標通道拿到的土地,其用地成本最低。這推動了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希望盡可能拿到最多的用地指標。
但是,指標總量是有限的,不同城市得到指標注定有多有寡,這意味著不同城市的發展機會是不均衡的。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近些年省會城市和原來的計劃單列市發展得比較快,因為這些城市的行政等級高,能夠有優勢得到遠超出其他地級城市的用地指標,再通過發展新區等形式,盡可能把用地指標留在自己管轄的空間內,可以吸引投資,獲得更多稅收和土地出讓金,以更好解決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的資金來源。
很多人提出要發展大城市,其實他們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為的是更多保障自己的利益。畢竟可能影響政府決策的精英人群基本都居住在高等級城市,要求國家支持高等級城市發展,看似是主張所謂的大城市發展路徑,其實是把自己的利益和大城市綁在一起。而支持高等級城市發展政策的核心之一,就是解決它們的土地來源問題,包括所謂的“人地掛鉤”政策,以及用地指標政策調整,都是把用地權向自己所居住的大城市傾斜。
如何破除土地指標路徑依賴?
如果土地要素仍然通過城市行政等級由上而下的計劃方式分配,何談能夠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呢?顯然,要對捆綁在土地上的利益格局進行重組,這是繞不過去的坎兒。
在現有國情下,肯定無法實施西方的土地私有模式,因為將涉及太多的制度性調整,而且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阻力太大,最終會導致改革政策無法落地。更重要的是,這會抬高中國城市和產業發展的經濟成本,還會抬高因所有制結構調整而形成涉及要素、機構及個人等更為廣泛的社會成本,顯然得不償失。
我認為,充分利用現有兩種土地公有制的轉換,增加集體經濟組織在城市發展中的長期收益,進而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應該是未來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
要想改變城市政府對于土地指標的路徑依賴,根本的辦法是縮小用地計劃指標的范圍和數量,把更多用地空間交給市場來配置,倒逼企業家與集體經濟組織談判,以解決未來的收益分配問題。這樣一舉多得。因為企業和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談判不涉及到強行征地和補償的問題,在雙方都可以通過發展獲得長期收益的前提下,談判成本大大降低。基礎設施的修建可以由企業自建,也可以由集體經濟組織修建,這些都可以通過雙方未來的合作方式來承擔。更重要是把一次性出讓土地的各種短期成本,分攤為企業和集體經濟組織按市場規律開展合作之后的長期支出。
因此,加快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城市一級開發市場,具有重要意義:可以更多地提供土地空間,減少對耕地的占用;可以通過企業和集體經濟組織的合作,把短期成本長期化,降低一次性開發投入,同樣可以降低企業的投資成本;集體經濟組織參與土地開發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大大降低征地和拆遷阻力;集體經濟組織分享到了開發收益,有利于鄉村振興。
而對于城市政府來說,減少了補償投入和征地產生的社會成本,但是并不會損失稅收收入;城市政府的短期行為會受到遏制,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會大幅提高;中小城市發展機會將大大增加,未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格局將會按照市場規律重組;更重要的是,閑置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資源將會得到有效利用,目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為19萬平方公里,是城市建設用地的將近3倍,而農村常住人口才占常住總人口的40%。
當然,如果實施這一改革,暫時性沖擊最大的是城市政府的利益,包括此前土地抵押形成的債務無法償還,未來房地產開發受阻,政府資金來源無法得到保證,投資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確定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將會受到影響等。
還有就是如果按照改革的思路去發展經濟,大多習慣于傳統發展模式的政府會很難適應,因此亟需探索和實踐。
一種設想是,可以通過稅收的調整來解決一部分城市政府的財源問題,但背后仍有一系列問題待解。比如,如果集體經濟組織參與了城市開發,那么集體土地資產是否要繳稅,還有城市房地產開發后,住房擁有者是否要繳稅?這會涉及到廣大人群的利益問題,也是改革將面臨的重要挑戰。
其實,以往改革都是通過基層的探索實踐總結經驗,可謂摸著石頭過河才有的創新。那么,是不是可以考慮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上,也給予城市政府和基層更多的探索權利,以找到最適合中國城市發展的方法?這方面還需要下更大的決心。(本文作者系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編輯:朱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