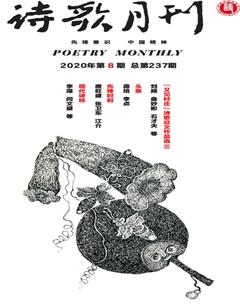主編薦語
寫作的方向有諸多個,是開放性的,寫歷史經驗和日常經驗是其中射向要傾述事物本體核心的兩個“彈道”,有人在兩條路上交叉穿行,有人在一條道上走到底。龐培屬于前者,李點屬于后者,這是詩人自己創作的美學修養和世界觀所決定的,我想說的不是這些,我想告訴讀者的是,看他們在這兩個方向踐行的成功之處,或者說,他們這樣寫為什么就成了。
詩人龐培的散文、隨筆和評論均是上乘的,他這組詩是在死亡和活著、西方之思與傳統之悟、歷史感和現實當下幾個維度里進行詩闡釋,做到詩的新發現。我喜歡他在詩歌里的“子彈”和死亡的詩陳述。充溢著哀而不傷的沉重與沉潛,以及《一首波蘭詩》《書上說到了微米爾》的新的表達,更喜歡他的《網兜》《新涼州詞》,“網兜”是龐培打撈已逝時光的網,在那網里,活躍的是陳年舊事的新鮮生命個體和龐大的社會客體,他讓“網兜”的形象出現在詩壇的長廊里,并將留下這個“物件”的標志性符號。他所有的反思和批判均在這一“網兜”里,他成功的讓活著的更好地活著,讓人側目注視;讓死去的重新活過來,讓人沉思與省醒。他的詩歌氣韻常常如他所言:“詩歌有一種停電的效果。”停電之后,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孤寂和恐怖,還有幽思和冥想,以及追問。
他在這些維度里閃進閃出地飛翔,在歷史與現實空間里擺渡,交叉地推進詩的高度和深度,讓復合性和延伸性得到無限的擴張和蕩漾。
日常的不一樣發現是考驗一個詩人優劣的標尺。李點的這組詩沉浸于對日常的詩性獨特發現和表達,日常給我們的是瑣屑、重復、程式、不經意和無意義,如果詩歌不能從這里逃出,用俯瞰和“第三只眼睛”遠遠審視它,就會讓我們陷入口水和日記的流水賬,其實,當下詩壇每天大量生產這些無個性、無發現的日常詩,這是我們要警惕的。李點是“從俗世中來”,卻朝著“到靈魂里去”,她是在“日常中提煉生活的黃金”,她的“黃金”意識就是她的精品意識。日常生活詩寫作首先需要的是新的發現,她在《地鐵中》看到哺乳的母親時,感到自己身體的異樣變化,那是偉大的母愛在被喚醒和歸來;對于日常生活寫作,詩人還要有批判意識,在《清明節想起父親》時,她寫道:“若塵世美好,我便溫婉/若塵世猙獰,我便有自己粗糙的表達方式”,寫出兩代人對待命運不一樣的態度,以及新的知識分子女性的抗爭和決絕;日常生活詩寫作還要用新角度來表現,她在《謊言》里用自己向母親撒謊,和母親向自己撒謊,雙撒謊這個“故事節”來引出“善意謊言”背后隱藏的對一個親人“喪事”的隱瞞,透著善良和慈悲。讀李點的詩使我聯想到科塔薩爾《我們如此熱愛格倫達》小說集中的主題追問: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是漸漸干癟的日常,還是某個飽滿的,不可測的世界中的一部分。
無論是對歷史經驗還是日常經驗的書寫,歸根到底還是寫新發現,和找到新的表達方式,對于已失的歷史要找到對當下現實的內在關聯和關照,不然,陳芝麻爛谷子說破了天也沒有多大的講頭。同理,對日常的書寫肯定要拒絕隨手記,同期聲,沒有嚴格的篩選,就把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人與事寫入了分行的文字,那肯定不叫詩,叫什么呢,往好里說,叫個人的日記,往壞里說,嗨!我就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