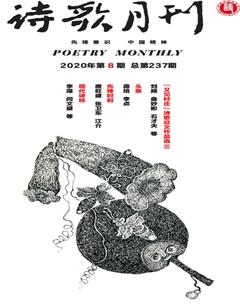教新詩寫作,我必須成為讀者
周東升
一
教了十多年的新詩寫作(寫作課的一部分),我一直面臨著這樣的困惑:教什么和怎么教。這兩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問題,它們如影隨形地糾纏著我,時時令我力不從心。我呢,不停地回答它們,不停地變換著教學的內容和方法,直到今天,也沒發現有什么值得公之于眾的經驗。
教什么,從來不是教科書寫得那么容易,特別是新詩寫作。在特殊年代,詩歌只有一種風格,一種寫法,這當然好辦,按照套路寫就行。而今天的新詩是多元化的,任何一種風格都沒有理由獨占鰲頭;學生更是個性化,他有權寫任何一種類型的詩。因此,在有限的課堂時間里,教什么就成了一個大難題。各種寫作教科書,涉及詩歌寫作,通常忽略多元路徑之間的差異,忽略學生的個性,以為詩歌寫作有一個普遍的經驗可以傳授。那不過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幻覺。對此,當下的寫作可以提供足夠多的反駁。韓東、柏樺、于堅、臧棣、蕭開愚、翟永明、王家新……哪一個不是獨特的?一旦從這些不同類型的寫作中抽象出一種普遍的寫作理論,這種理論就再難還原為具體的寫作方法。教師可以滔滔不絕,夸夸其談,自以為發現了詩歌的秘密,可是學生面對這種抽象理論,只能陷入漫無邊際的混沌,下筆茫然無措。
多年前,我剛剛接手寫作課,想法很幼稚,以為按照自己理解詩歌的方式去教就可以。我談音樂性,談詩歌的語調,談如何經營一首詩的聲音,讓它聲情并茂;并通過語調塑造一首詩的形象,令讀者聲入心通。兩輪教學之后,我便萬分沮喪,我發現我在誤人子弟,沒有一位大學一年級的學生能夠在這樣一種“玄學”中受益。
語調自然是詩歌寫作中極重要的問題,但是,絕大多數大一學生缺乏新詩閱讀的基礎,根本無從掌握。雖然中學教材中涉及的詩歌,諸如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鄭愁予的《錯誤》、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等,都是經營語調極為成功的范例,初學寫詩者或可領悟語調的魅力,卻絕難貫徹到分行訓練中。寫作是中文專業必修課,學生沒有不修的選擇權,若是利用這種限制迫使學生接受不適合他們的教學內容,是不道德的。我很快又陷入“教什么”的困境。
后來我還試過從意象、戲劇化、小說化等具有操作性的技術入手,設計各種方案加以訓練。但創造一個意象并不容易,像曾卓的《懸崖邊的樹》、牛漢的《半棵樹》,都在“樹”的形象中熔鑄了半生的苦難,才有那么鮮活的意象。意象訓練的結果,多數變成了簡單的詠物,寫不出意象的生命力。戲劇化同樣難以把握,作為詩歌結構,理解這個概念本身就很困難;作為寫作技法,訓練若是停留在對白、獨白這個層面,沒有多少意義,而構造戲劇化情境,對于初學者難度過高了。小說化也即敘事技術,容易把握,可又太容易陷入某些口語詩的套路。在最初的基礎訓練中,我斷不能容忍有學生誤把分行散文和“段子”當詩歌。總之,從技術入手也不盡如人意。
大概是2012年以后,寫作課上常有同學來旁聽,講詩歌寫作時還要多一些,最多有十幾位。他們是學校詩社的成員和其他專業的文學愛好者。雖然這門課不是為他們開設,可是他們來了,我不能不在教學設計上考慮他們的需求。相對于大一的同學,他們有較好的詩歌閱讀和寫作經驗,這令我在“教什么”上更加為難。我向來不敢自信,總是懷疑過去的做法,從此以后,每學期更新教學內容,年年備新課,更加失去了“老教師”應有的從容。
上寫作課的同時,我還在上一門選修課——現當代詩歌欣賞。在交流中,我也慢慢醒悟,真正熱愛詩歌寫作的人,是不需要教的。他們來到我的課堂,不是為了做學生,也不是為了學寫詩,他們真正的目的是來我這兒尋找“讀者”,他們渴望聽到自己的詩歌和讀者碰撞的回聲,他們要憑借這回聲進行自我定位、自我校正。這個發現,給我的虛榮心潑了冷水,卻給我的教學帶來巨大的幫助。它使我意識到,要想做一名合格的寫作課老師,首先必須成為一名合格的讀者。有趣的是,明白了要做讀者之后,做老師似乎也自如多了。
二
又是幾年摸索,到了2016年,我調整了寫作課的文體訓練順序,由常規的“詩歌—小說—劇本”轉變為“劇本—小說—詩歌”。這個設計,給我帶來一些驚喜。劇本寫作中的場景意識,小說寫作中的敘事策略,以及電影的鏡頭語言和鏡頭組接的方法,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入到詩歌訓練中。劇本和小說的虛構性,也能啟發學生擺脫個人化的局促,去表達更為深廣的經驗,而不是個人真實經歷。如此,我們的詩歌訓練便有了一個較高的技術起點,而我就可以把精力和時間集中在“寫什么”和“怎么修改”這個環節上了。
對于每年新入學的大一新生,詩歌“寫什么”始終是一個困惑。他們熟悉的中學語文教材里的名篇如《雨巷》《再別康橋》等,幾乎都是音樂化、情緒化的作品,很容易把學生引向“假大空”的陷阱,都不是初學者的好范例。經過幾番挫折,我決定把“經驗”作為寫作起點階段的表達對象,讓詩歌寫作從日常生活出發,從切身經驗出發,從言之有物出發。當然,這種實用主義的做法,我也常常懷疑它的恰當性,但至今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性方案。
“因為詩并不像一般人所說的是情感(情感人們早就很夠了),——詩是經驗。” 里爾克這句話,常常被我拉來當大旗。在我們的文化語境中,“詩言志”“詩緣情”深入人心,這導致很多人不加深思地就把詩歌作為抒情工具。這樣的想當然必須要破除。詩歌離不了情感,情感可以是寫詩的動因,可以是詩的效果,也可以是詩的對象。但初學者最忌諱的是把情感作為對象——直接抒情,這是成熟的寫作者才能駕馭的方法。多少浪漫主義詩人都曾在此失手,而里爾克的“經驗說”正是對浪漫主義濫情的糾正。
當然,在詩歌訓練中,里爾克的“經驗”也需要限制。詩作為表達方式,是經驗的結晶,因此,里爾克借布里格之口說:“為了一首詩我們必須觀看許多城市,觀看人和物,我們必須認識動物,我們必須去感覺鳥怎樣飛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開放時的姿態……”但是,詩既是表達方式,也是表達對象,可以說,詩是詩的表達對象。用廢名的話說,“新詩的內容則要是詩的”。作為表達對象,詩不是一般的經驗,而是一種特殊的經驗,一種無法直接說出的經驗。
何謂特殊的經驗?這很難闡明,但并不難感知。它首先是可感的,觸目驚心的,銘刻于心的,卻不能和它所在的具體場景、環境或氛圍剝離。詩人常說它是神秘的,因為它不能直接說出,要表達它,只能把它和它植根的場景、環境或氛圍一起呈現。但它實際上并不神秘,它鮮活可感,就活在記憶里,活在生命里,活在想象里,活在夢境里。它無法以抽象的概念形式存在,就像每個人的生命里,沒有一種叫愛的抽象物,只有愛的動作,愛的聲音,愛的碰觸,愛的氣息,愛的氛圍,愛的臂彎……當你有效說出了這些“具體”,你就表達了愛,這幾乎等于說你寫出了一首詩。
如果遵照王國維的說法,詩“有造境,有寫境”,那么,這些“具體”既可以“寫”,又可以“造”,取哪一種路徑,決定于寫作者的個性。從實際訓練的角度看,“寫境”作為起點,更容易上手,而“造境”則需要一定基礎,這好比繪畫的學習,通常要從寫生入手。但是,理一分殊,王國維認為“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
詩作為特殊的經驗,無法直接說出來,在當下的寫作中,有不少詩人忽略了這一點。他們把詩歌作為一種特殊經驗的表達難度,混同于用修辭包裝經驗或觀念的技術難度。因此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一首修辭高明、觀念深刻,具有批判性的詩,缺乏的恰恰正是詩。所以,在寫作教學中,我一直努力避免把詩歌訓練變成純粹的修辭訓練或技術訓練。修辭、技術只有服務于“特殊經驗”的表達時,才是必要的。而一般的、可直言的經驗,顯明的或深刻的觀念都是散文的對象,無須用詩表達。你寫成明白易懂的說明書,更便于指導工作、生活;寫成哲學作品,可辨名析義,使人明理;寫成論文,則能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何必非要吃力不討好地寫成朦朧的復義的新詩呢?
有時候,遇到對現代詩了解較多的學生,還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如何理解現代詩的“知性”?如何理解瓦雷里的“抽象的肉感”、艾略特的“思想知覺化”?這是很難一下說清的問題,但在初步的訓練中必須澄清,否則學生又會從抒情的泥坑滑向說理的沼澤。我們知道,一百多年的現代詩主流正是“知性”(intellect)之詩,或“智”(wit)之詩,它們機智而深刻,冷靜而思辨,能夠洞徹虛假的現實,滌蕩濫情與偽浪漫。但它們也偏于晦澀、冷僻、枯索;又常常高高在上,不近人情;偶爾還會裝腔作勢,故作高深。可以說現代詩成于“智”,也敗于“智”。因此,現代詩的“智”或“知性”并非無可挑剔,更非不可動搖的路線和方向。也許今天的詩人對于經典現代詩的態度,反省應多于膜拜,比如對艾略特的《荒原》。
初學詩者對于瓦雷里、艾略特等大詩人的話更不能迷信,時代在變,語境也在變。事實上,瓦雷里、艾略特并不認為先有抽象之理,然后再將之形象化。他們所謂的抽象、思想,只是帶有理性意味的感性體驗。有些當代詩人對此有致命的誤解,他們一直在包裝那種先在的道理或思想,把一種可以言明的觀念模糊化,頗有些裝神弄鬼的感覺。抽象的肉感化、思想的知覺化,很容易產生歧義,作為訓練的路徑,可謂危險的旅途。安全也更具操作性的仍然是發現那特殊的經驗,通過具體的場景、環境、氛圍去呈現它、捕捉它。
詩歌寫作訓練,當然不必先普及詩歌理論。但是作為老師,有必要說明這一切,因為,當代詩歌批評常有一種不良的習氣,很容易影響到初學者的寫作,那就是不加辨析的盲從大詩人,把大詩人的名言當真理、當依據。大詩人的話有它自身存在的歷史語境,不一定都適用于當下的寫作。對此,教師不應該喪失判斷力。雖然判斷可能出現偏頗,但只要不絕對化也無妨,學生們前途無限,自有校正能力。沒有方向的訓練卻是實實在在地浪費學生的寶貴青春。
教學中,我參閱過不少寫作教材,包括最近幾年火爆的創意寫作教材。它們提出各種詩歌理論,設計花樣繁多的操作方法,可是一看例詩便大失所望——它們是在教寫平庸的詩。如果編者或老師自身缺乏基本的詩歌感受力和判斷力,何以教人呢?在當下,詩歌寫作教學的公共資源還太少,各個環節都靠自己慢慢摸索,而整個基礎教育和高中教育,沒有教給學生必要的新詩閱讀、寫作能力,大學里,新詩寫作教學的任務之重和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三
我的寫作課首先要完成“培養方案”規定的任務和目標,要為學生的專業學習服務,不可能專去培養詩人,也不可能專講詩歌寫作。分給詩歌的時間大概有5講,每講2節課。有時候,學生興致高,就想辦法增加一講。通常,第一、二講,我都是帶著大家一起讀詩。讀詩當然是快樂的,學生眼睛里迸發的新奇之光也令我愉悅。但讀詩不是為了閱讀的愉悅,背后隱藏的目的有多種:一是了解當下的詩歌狀況,二是了解新詩寫作的多元化格局,三是糾正對新詩的種種誤解,四是初步獲得詩歌寫作的基本認知,即寫什么和怎么寫。選詩時,我也盡量多元化,課堂上無法讀完,可以延伸到課前或課后。隨著年年增補,寫作課的詩歌閱讀篇目已經增至30多位當代詩人60多首新詩。每位詩人的詩作在課堂上都肩負著特定的教學使命。比如多多《冬夜的天空》的觀察視角,陸憶敏《美國婦女雜志》暗藏的對白方法,韓東《一摸就亮》《梁奇偉》中的小說化手法……又比如柏樺如何利用聲音創造一首生動的詩,臧棣詩歌如何用思辨來激活詩的情境,于堅如何在細節中展開廣闊的社會、歷史畫卷,陳東東詩歌如何把現實與超現實糅合……
閱讀之后,訓練之前,還要做幾點說明。這是專門為初學者準備的,并要求他們辨析:第一,論“自家的孩子和王婆的瓜”;第二,論“鐵匠的斧頭和木匠的斧頭”;第三,論“看風景的人和風景里的人”。這三組比喻,分別喻指詩歌訓練中的三個常見問題:第一,經驗的處理問題,即寫作者對待個人經驗,應該有意識地將之對象化,不能總覺得“自家的孩子”什么都好,而不能取舍。寫作者應該向“賣瓜的王婆”學習,她實在是一個好榜樣,不論瓜好瓜壞,她總是擅于創造言辭上的完美之瓜。第二,寫作的目標問題,即寫詩要像鐵匠那樣為讀者打造一把好的“斧頭”,而不是像木匠那樣使用斧頭去砍、去劈、去表達。你無須掌控別人怎么理解你的詩歌,怎么使用你的詩歌,但你能夠要求自己把詩歌打造得精良、鋒利又耐用,令那“木匠”愛不釋手。第三,主體問題。寫作者應像“看風景的人”那樣,具有明確的“我在寫作”的主體意識,而不是去作被看、被寫的風景中的人。他要么創造一個角色、替身,要么戴上各種面具,除此,他不會以真身進入詩歌的文本。一個好的詩人,就像偉大的導演,常在鏡頭外,他的任務是導出好電影,而不是演出好電影,更不是說出好電影。
在我看來,這三點是訓練前必須展開討論的。同時,我也會告訴大家,這絕不是金科玉律,這只是訓練的要求。訓練結束后,你覺得遵循這樣的要求有益,你可以繼續,倘若覺得多余,你就自行解放。訓練有框框,寫作要自由。
寫作訓練,我歷來反對“多寫主義”。和有節制的訓練相比,過多的訓練費力不討好,國內外都有相關的調研支持這一說法。因此,我布置作業,字數只設上限,不設下限。小說每篇不超過8000字,劇本每部不超過30頁,散文3000字以內,評論5000字以內,詩4首,每首不超過30行(允許以一部長篇小說,或一部短篇小說集,或一部散文集,或一本詩集替代全部作業)。以前,總有不少學生追求寫得多,篇數多,字數多,激情澎湃,動輒一兩萬字,寫得暢快,卻不重視質量,經驗不能沉淀,收獲甚微。近些年,“限產限量”后,寫作課的時間和精力就集中在后期的修改上了。一般情況下,學生寫完詩歌的初稿,要先按照“修改清單”,做第一次修改;然后交給我這個讀者,讀者不滿意,就提出建議,做第二次修改;之后再閱讀再建議,不能定稿的,做第三次修改。最終,我這個讀者也會忍不住動手,和學生一起討論修改,直至全部定稿,編出一本班級新詩選。因為我個人對詩歌有偏愛,加之詩歌短小,所以詩歌的修改通常不少于三次,至于別的作業不免要寬松些。否則,即便有助教幫忙,這樣工作下去,也是吃不消的。在科研主導的大學體制里,做這些沒有“科研含量”的工作,是不能與時俱進的。
其實,這最后的修改環節,我認為是整個詩歌寫作教學最重要的。可它是由一個個的特例構成的,每次建議和修改都有具體的針對性,難以化約為一種經驗或方法。作為寫作課老師,我也不知道如何描述它的重要性。同時,作為學生們的讀者,我也常常感到慚愧。因為,有時候我也會失去耐心,大發雷霆;有時候還會偷懶耍滑,敷衍了事……倘若一定要在文章末尾總結一下這些年的教學收獲,恐怕還是江平、玉倫他們給我的啟發:比起老師,詩歌寫作課的學生更需要一名真誠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