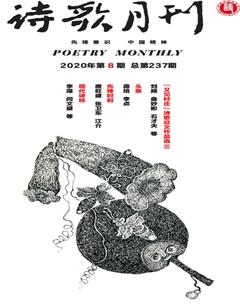欠我一院子的菊(組詩)
何苾
夜空
太陽也有睡眠
在無人知曉的夜的后背就寢
拂曉在天邊安了個鬧鐘
總讓黎明叫醒太陽
夜空是不是也有邊界
每顆星星的哨所
也有肉眼看不見的掠奪
我在守護夜空的安寧
月亮圓了又缺,缺了又圓
我有一粒心思
在季節的連接線上起飛
飛向夜空最邊遠的那個角落
聽太陽失語,我看見
宇宙蓬勃的心臟
我既不愿驚擾夜空
也不想輕手輕腳
在夜空最燦爛的那一瞬
用我的明眸,拓下流星的腳印
做一副標本
高秋
秋風的刀剪揮過
落葉紛紛,花白的樹蔭
增添了庭院的寂涼
寒意從窗縫鉆進
向我討一件風衣
十月的天,薄了
瘦云掉下的影子也薄
大雁抒寫天空的方向
翅膀的語言
我眼里最美的詩
皺紋在集中打盹
夢見日子在出售年齡
高秋的蜜蜂
欠我一院子的菊
找到自己
不一定步他人后塵
也許一場風雨,他的腳印
成為你腿上的泥濘
別以為挺直了腰桿就有氣節
冰天雪地,你依然昂首行走
或許會摔成骨折
莫因月亮的圓缺而傷感
人生的燦爛往往與陰晴相反
倘若有淚,就灑給江河
不要一味地攀爬
即便你站到了峰頂
山腳下的人也會把你看小
別總想把光環戴上自己的脖子
縱然你生前鮮花簇擁
也難免身后雜草叢生
用清澈的眼睛擦亮陰天
用溫暖的心烤干雨季
時間以上、空間以外,幾多嶄新的路
時間的影子
我瞅見了時間的影子
在雷霆的喉結
在閃電的裂縫
在黑夜心跳的那一次
那一次跳動的節奏
那個節奏兩側的音樂
那段音樂鼓出來的高度近視的眼睛
我瞅見了時間的影子
在時空隧道的拐彎處
馬鞍、獵槍、牛仔帽
牛鞅、耕犁、蓑衣
長衫、課桌、書籍
太陽傘、池塘、擁抱和吻
當我掀開時間的影子
屠宰場,賽馬場,斗牛場
球場,賭場,戰場
或是廣場上叫賣的小販
或是街面上席地而坐的乞丐
或是墻腳下蹲著的一群衣衫襤褸的孩子
時間的影子飄忽不定
騎在世界的頭上
踩著世界的腳
鉆進世界的腹腔
一群螞蟻爬到世界后背
給另一個世界壘起一個支點
舊事
舊事在飛
像蜜蜂,鉆進荒坡野菊的花瓣
像蜻蜓,騎上岸邊飄舞的楊柳枝
像雪花,趴在老屋子的瓦溝里
把舊事塞進記憶的葫蘆,用酒浸泡
醉了的舌頭,醉了的眼球,醉了的心
把舊事放入記憶的醋罐,慢火煨湯
酸了的鼻息,酸了的胃覺,酸了的人生
舊事穿上新衣,戴上新帽
穿著兩只不同尺碼的鞋
給舊事注射興奮劑
讓它闖進奧運會,踢一個烏龍球
倘若幫舊事撰寫一篇演講稿
不打標點符號,不提行
搭一個旋轉舞臺
喜鵲當主持,烏鴉當聽眾
扁平的日子
你有海一樣的舌頭
吞吐一片天空
曾經的剛直被歲月擠壓
壓縮了的白晝和黑夜
日子扁平了,沒有朝暮
往事潮濕,記憶生苔
脫皮的諾言鈣化成樹
眼底長出了珊瑚
模糊的視線
縫合著人生的裂隙
一絲光陰在爬行
懷抱一個未圓的夢
受孕新的光點
遠方的黑色角落
一道閃電分娩
動蕩的海繼續動蕩
呼嘯的天繼續呼嘯
你能夠心靜如水
垂下眼簾
轉向草木(外二首)
王大塊
多么明朗。
使用“云開霧散”時恨不得把視頻擺在你面前。
但仍不徹底,你感不到微風的涼。
草木皆兄弟姐妹。
請忘記一個成語,前三個字“草木皆”。
露珠正從葉片上滾下
顫抖著
我的身體片段隨之跌落地面
由宇宙的暗黑到水滴
滑入的是另一種大
不僅消化我,也消化了宇宙。
思維,唯一而單向
語言從來粗暴地修改它。河岸兜著河水走。
我指給你看吧。看到了也別說。
那須根,須根中奔波的螞蟻
那莖,莖上剝落的老皮
那小花,一個指頭指著虛空。
隱痛
實實在在的痛以猶猶豫豫的方式
種在我的手指上
它游走,游走
腳跟和頭發忽然產生了聯系
誰干的呢?
深究起來,連我自己都難逃罪責
每個人都說是無意的
如果是好事呢?
身體開始變得重要。
三個口號抵不過一個隱痛
這,仍然是口號
一些人從我面前走過去
排著隊死掉。
從震驚到波瀾不興,我用了十五年多一點
除非有更令人震驚的。
倒推過去,一切都是必然
隱藏著狡猾的偶然
隱藏著我解決不了的痛
窗簾
深夜里也不閑著。有一點縫隙
光就會透進來。
不要用庸常語言來解釋它。
它想告訴我的,我已全部看到。
這只是個開始,和床連接在一起。
多么復雜的事
都可以回溯,如果你敢。
我悄悄為其命名。
壓抑了很長時間的三個字。
它還可以變化的,從“阿”到“啊”
只在我一念間
而你們目力所及,是最后一個。
玻璃是干什么吃的呢。
把一切都推給布。窗簾是布。
衣服是布。床單上的我,也是布。
布內的內容,必須由布決定。
我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