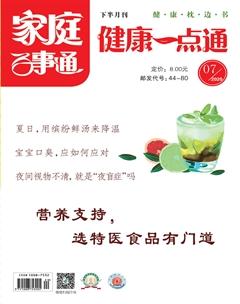媽媽,我帶您回家
王生虎
1
年后的一個晚上,爸爸突然打來電話說:“你媽肚子疼,快回來帶她去看看。”他語氣有些慌張,我頓時有不好的預感。
從小到大,他們從不向我提及任何身體不適的話題,哪怕爸爸被摩托車撞了,媽媽的手被鐮刀割破了……他們從來不說。這給我一種錯覺:他們的身體都很好,從不生病。但在每一次事后,他們不小心說漏嘴了,我才知道他們是在刻意隱瞞,怕我擔心、不愿給我添麻煩。所以,爸爸的電話讓我震驚——若是小毛病,怎么可能告訴我,更何況還在夜晚打來。
我心亂如麻地趕到家,媽媽的疼痛已緩解,她還埋怨爸爸:“叫你不要打電話你非要打,大晚上的讓孩子跑這么遠的路。”她仿若無事,但煞白的臉色讓我陷入深深的恐懼。
第二天,我帶媽媽去市區醫院看病。離家前,爸爸再三叮囑媽媽:“把病瞧好了再回來。”他知道媽媽性子急,怕她丟不下家里。媽媽溫順地點點頭:“嗯,這一次一定把身體看好了。”
后來,住院檢查CT結果顯示:胰腺癌晚期。聽醫生把話說完,我驚呆了,淚水奪眶而出。醫生又說:“這病已經治不了了,回去吧!”
在回去的車上,媽媽坐在后排問我:“虎啊,是不是沒治了?要不然怎么連水都不掛、藥都不開。”我戴著墨鏡,怕媽媽看見我的淚水,也不敢說話,怕她聽出我的哭腔。這一切都徒勞無功,媽媽怎么會不了解兒子呢。她沉默了一會兒,反倒安慰我:“沒事,我都七十多歲了,不算短壽。”
2
回去后我不甘心,又聯系上省腫瘤醫院一位專家。媽媽聽說要去省城找專家看病后歡天喜地,出發時收拾好衣服和洗漱用具,打算住院治療。
到了省腫瘤醫院,疫情期間,我們連住院部都進不去。專家下樓來領我進大廳,看看CT片、病歷,搖搖頭說:“都擴散了,手術沒用,化療也不行,年紀這么大,別讓她四處奔波遭罪了,回家吧。”聽完,我絕望地走出大廳。
媽媽在風中等候我,花白的頭發凌亂且飛舞著。看見我的神情,媽媽的臉色迅速黯淡。我摟著媽媽的腰、貼著她的臉低聲地說:“媽媽,我們回家吧!”媽媽點點頭,挺直腰桿,像個健健康康的人,走得比我還快。可是她失望的表情,割得我心兒滴血般疼痛。我像一個廢物,連安慰的話都不知道怎么說。

3
幾天后,媽媽疼得更厲害,只好向我說:“我想掛掛水,或許掛水舒服點。”我只好又帶媽媽去附近的醫院。醫生支開她,問我:“她的情況你是知道的,你想做什么?”我說:“我想讓她住院,掛掛水。一來緩解她身體疼痛,二來給她心理安慰。”
住院當晚,還沒輸液,媽媽打電話給爸爸:“我好了,過幾天就回去。”她的聲音響亮且充滿喜悅。我知道,這是心理作用,但我寧愿她就此快樂下去。可惜事與愿違,從第二天起,她的狀況開始向不好的態勢發展。媽媽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消瘦,從鴿子湯到面條面湯,再到稀飯湯,漸漸吃不下任何東西。她無力行走,去洗手間也得讓人挽著。她聲音孱弱。她說肚子疼,我為她按揉,她卻疼得更厲害。我為她修剪指甲,她連轉動身體的力氣都沒有。看著虛弱的媽媽,我一次又一次地背著她抹眼淚。
4
輸液幾天后,媽媽徹夜難眠,因為疼痛沒有片刻消停。我懷著一種哀傷悲壯的心情走進醫生辦公室,我不能忍受媽媽在劇痛中煎熬。
醫生給媽媽用嗎啡止痛。可嗎啡止痛的效果日漸減弱,從兩天一支到一天兩支,媽媽依舊疼得眉頭緊蹙。終于,媽媽抓著我的手,低聲地說:“虎啊!我想回家。”媽媽想回家,她這是放棄生命,只為在彌留之際想再看看自己親手打造的家園,我的淚又噴涌而出。
親人們知道媽媽 要回家后,并不悉數贊同,擔心她回去疼起來吃不消,還說在醫院輸液,可以維持更長時間。
媽媽的要求被婉拒后,她的眼淚溢滿眼眶。媽媽去日無多,這是無法回避的事實,既然許多靜好的日子被我們錯過,何必偏執于十天與五天之間的長短。最主要的是,此時,回家是媽媽心心念念的愿望。我不能讓媽媽抱有遺憾,我必須在她清醒時帶她回家。
我咨詢醫生能不能開好藥,讓我帶回去幫她注射。醫生說可以,不過有點麻煩,需要來回多跑路。只要能滿足媽媽的心愿,跑斷腿我也心甘情愿。
小時候,媽媽怕我摔倒,緊緊抓著我的小手。媽媽身體不適后,我也無數次握著她的手。我知道這種交流經歷一次少一次,并會停滯在某個未知時刻,心疼地久久不愿放下。我要讓媽媽明白孩子對她的眷戀,讓她充滿溫暖地遠行;我要把她對孩子的愛意深深刻進心里,伴我一生一世。

我把媽媽的手放在手心撫摸,輕輕地告訴她:“媽,后天我帶你回家。”媽媽眉頭瞬間舒展,一根指頭在我手心若有若無地撓撥。她是在感謝我嗎?可是我那么無能,護衛不了她的健康。她還記得日子,雙目無神地慨嘆:“后天,后天是初三吧?”我使勁點頭。媽媽竟露出久違的笑容:“回家和他們說說話,我就好了。”
這輩子,回饋媽媽恩情的行為竟然是“帶她回家”,我淚水一次次風干,又一次次掛滿臉頰。鄉間有“借壽”的說法,可是我找不到身懷這種奇術的人。否則,我一定把我的壽命與媽媽平分,生生世世和她在一起。她不痛,我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