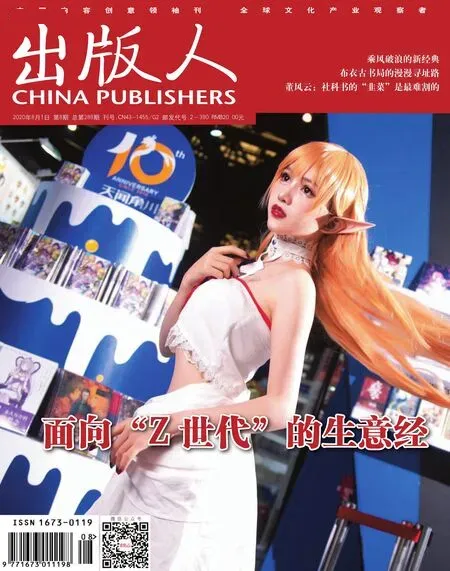隱顯之間:可遇不可求的設計
文|陳飛雪
這一切僅僅用了純文字與空間的排布,非有強大的專業力和深厚的美感難以成全,那一層耐得住細細端詳引發的閱讀愉快,就是編輯的幸運和額外福利了。

2018 年春夏到2020 年初,我幾乎在同一時間線上,編輯《愛書來》和《小津安二郎全日記》,幸得良緣,李猛先生應允為兩本書擔綱整體設計制作,因而有了一段極為受益又愉快的合作。
對這次合作,我滿懷期待和好奇,不僅因為帶動出版風潮的《故宮日歷》最初即出自李猛設計,也因為他做書的專注度極高,就十多年時間長度而言,尤其和同行比,他的出產量算少的,用他自己的話,“早早畫地為牢”,可他設計的《明式家具二十年經眼錄》《中國古代金銀首飾》《木趣居》《我們的中國》《物色》《圖說敦煌二五四窟》《蒙古國紀行》,每一本在編輯同道間會被討論很久。2018 年他獲得以專業著稱的坡州圖書獎“出版美術獎”之后,尚曉嵐與他有過一個充實的訪談,向著“讓書是書,讓讀書是讀書”的目標,李猛的實踐與方法,確實與很多同行不一樣。他非常細致甚至近乎挑剔地挑書,挑作者,挑編輯,挑出版機構,挑印廠,對每一個環節的參與者,他都有要求,“只有前述各方面都達到高標準了,才有可能做出有價值的完全的書”。讓我過目難忘的還有他的自問,“通過十多年的追求,我向自己發問:到底什么樣的內容值得去投入新的思考、拓展設計的邊界?”顯然,出版的沙場上,李猛在用不止于設計的馳騁,追尋一個大哉問的答案。那么在這兩本書上,他裝幀設計的特質會怎樣呈現呢?
《小津安二郎全日記》和《愛書來》,一日記一書信,碰巧都偏私人化和向內的特質,寫作屬性使內容和文本形式較之通常的出版物,多了細碎、隨意和附件多樣貌等需要合理表達與平衡之處,加上需盡可能保存原貌的編輯圖求,單內文排版這一項,必有賴行家設計,方有到達理想水準的可能。而這理想,說到底,讓內容處于恰當的位置,讓閱讀者舒適,讓設計消隱,出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一本書有它圓融自洽的好面貌。
小津導演三十年的日記,分由三十二冊大大小小日記本存載,日人田中真澄悉心整理,其中既有片斷性的記述,俳句創作,友人唱和,也有兼具日程表性質的內容;既有一天僅記一字的日記,也有同一年日記主人不知何故用了四本手賬重復記錄的文本;有整理者對日記里書寫錯誤的更正或保留及其說明,也有譯者周以量教授的發現和附加注釋,更有兩百多條校異,三百多部電影的片名、導演、演員列表(日、英、中文),和多達數百人的《相關人名錄》,這一切,和八百頁的非常篇幅一起,需要得到妥帖的安排,和美觀的呈現。
李猛把書稿拿去看,什么也沒說。過了一陣,他說他專程去日本回來了,在蔦屋書店買到一本書——《小津的事業和生活》,綠封皮,書里收有小津導演畫的畫,并掃來幾張與我分享。我猜他還去了一些地方,看了許多東西。之后又過了半年,他發來內文設計方案,真是滿目清朗開闊,條分縷析。書眉高掛年份與頁碼,正文里日期左起,日記平行于右,注釋再落右下,既保存了日式的手賬感,視覺上,時間如川流如水滴如珠簾,串起小津三十華年的日與夜。這本幾乎沒有圖像的八百頁書籍,字體字號變化也十分節制內斂,卻極富節奏感和視覺感,甚至有類似呼吸的韻律;那些紛繁復雜的內容在不易察覺的高妙安排下,化作足以讓人舒適閱讀的邏輯表達,似乎它們原本就這么圓融條暢,氣息平和安靜,足以讓閱讀者貼近小津的心聲而無額外的干擾。如果再想到這一切僅僅用了純文字與空間的排布,非有強大的專業力和深厚的美感難以成全,那一層耐得住細細端詳引發的閱讀愉快,就是編輯的幸運和額外福利了。
《小津安二郎全日記》出版后,整本書在封面裝幀上低調又準確地傳遞了小津氣質這一點,引起同行關注,網上也看到稱揚連連。精裝硬封,灰色布紋,封面壓凹印的“小津安二郎”簽名,封底中央壓印一個“無”字(北鐮倉圓覺寺小津墓碑上唯一的刻字),除此別無他物,極端簡潔。打破常規的豎立的書套上,豎立的標宋體書名“小津安二郎全日記”,凜凜然如片場風格嚴肅的導演本人,對于熟悉松竹映畫時期小津電影片頭的讀者,第一眼就能喚起“這正是我熟悉又期待更了解的那個人啊”的暗合之喜與期待之心。
小津電影的美學,是向著靜謐、單純、一意孤行去的。如學者姜建強所言,是“波瀾不驚一切,而一切都在波瀾里”的。經由李猛整體設計的中文版《全日記》,也是將一切洞悉,交付基于邏輯美感的清朗和節制,交付深刻的默契和闊大氣度,交付恰如其分的引而不發,那份日系感和沉著的古典氣息,如父如兄,如小津導演一再以沉隱于日常生活、看似毫無玄機的作品確立起無可追摹的大師風格,從而使裝幀到達與作品本身極度貼合的高度。這是能喚起讀者深層滿足感的作品效果。
如果說,《小津安二郎全日記》的設計到達了可遇不可求的“契合感”,那么書信集《愛書來》的裝幀,我認為從數十年同類題材和作者書籍的常態中,一躍而出,打破了一些習以為常的思維和審美期待。
《愛書來:揚之水存谷林信札》的兩位通信作者,谷林和揚之水,是當代文化界具有獨特人格的學者、讀書人,其交往最見風格的,就是持續近二十年的通信往來。二人以書信為交流和馳騁文字的媒介和載體,緣起于1990年代,身為《讀書》編輯的揚之水,與兼任作者、義務校對和義務評論員的谷林先生,交流讀書、寫作、編輯、文史考證或書界人與事,結下深厚澄明的情誼,且綿延持久,直至2009 年谷林先生駕鶴西去。鴻雁難再傳書,而余音繞梁不絕。


李猛本就擅長表現中國傳統中的精髓和精致,對此類書籍題中應有之意的雅正,是了然于胸的,也毫無偏差地傳遞了出來:圖片和內文在他手里端莊有序地編排而出,他獨有的設計敘事,令書信往還之間,篇章轉換之間,無不透著蘊籍、溫情和敬意。別有洞天的是,他似乎對“這一本書”和“這樣的作者”另有一層直覺和領會,抓準兩位通信人深層的浪漫氣質和彼此觸動靈感的精神狀態,以富有才華的共情,從數百封信件中,揀出一張錯落著不規則彩鉛小色塊的信箋當素材,鋪陳豆綠的底色合成護封的圖像,極為靈動,揚之水題簽的“愛書來”,則運用不多見的天藍色置于書名位置,整體面貌頓生清麗和純明,還有一點超脫于俗世和年齡的爛漫,色調呼應著精裱在硬殼上的藍色絲絨布面。藍絲絨硬封上,純墨色“愛書來”端端正正、結結實實豎排壓凹燙印在正中央,仿若鐫刻般沉和穩,周旁與封底,再無一字一物,又是一派闊大天地的氣象。
這一層從靈動清麗到簡凈深沉的張力,是李猛賦予這本書的詩意,富有個人風格,又極其貼合作者與文本。由此他的工作超越了設計的邊界,給編輯以同行的默契與專業支持,這是身為編輯的我,最為感激和心懷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