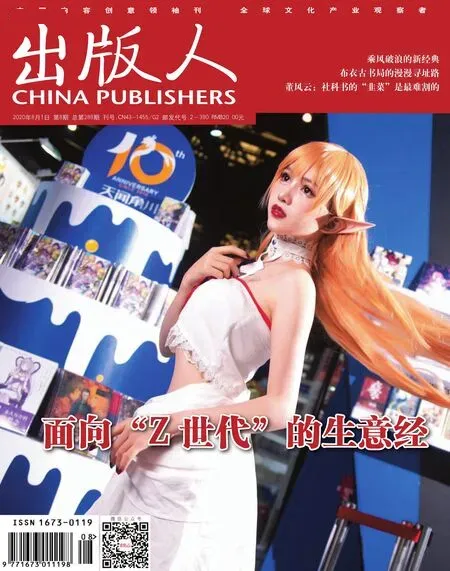春山春濃春亦敗
文|禾 刀(書評人)

何大草 著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出版:2020年6月定價:39.80元
“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在王維現(xiàn)流傳至今的400 多首詩中,這首《終南山》中規(guī)中矩,并不顯眼。這首詩大概作于王維四十歲時,幾年前,恩師張九齡被貶荊州,王維對官場的熱情跌入低谷。大約三年后,經(jīng)人介紹,王維買下宋之問在終南山腳下的輞川別墅,并花費一年時間修葺。此后,輞川別墅成了他隱居避世之地。
何大草從小酷愛讀王維的詩歌。本書是對王維人生最后一年的文學(xué)式書寫。這一年,王維剛好進(jìn)入耳順之年。或正因如此,他無論對生活還是他人,不怨不怒。本書生動再現(xiàn)了王維與裴迪的日常與復(fù)雜情感,與一二友人的交往,以及他不為人知的內(nèi)心世界。詩與禪是探究王維內(nèi)心宇宙的兩把鑰匙,它們包裹著王維的內(nèi)心,令其呈現(xiàn)出詩意與哲學(xué)的光芒,生命由此獲得了滋養(yǎng)、圓融與升華。這同時也是窺視中國文人在歷史磨難中一路走來的一條門隙。
亂世避世與盛世避世
本書采用了大量對話,對話對象有裴迪、老方丈、貴婦等。對話暗藏禪語機(jī)鋒,意味深長。
761 年4 月初,王維和忘年交裴迪信步去了辛夷塢。在裴迪看來此時春意正濃,而在王維眼里,此時“春敗了”。“濃”是當(dāng)下,“敗”則指未來,這是“春”的宿命,當(dāng)然也是王維心理的折射,畢竟王維已經(jīng)步入人生的暮年,對人生早已參透。
關(guān)于生存理念,王維與裴迪有段精彩對話。裴迪問“會為五斗米折腰么?”王維的回答“少有地爽快。‘我會’”。同是田園詩人,同以歸隱鄉(xiāng)野為人生樂趣,但二人還是各有不同。
陶淵明雖然留下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情畫意,夢想過“桃花源”,但在王維看來,退居鄉(xiāng)野的陶淵明“保住了氣節(jié),無愧于清名”,但“他一輩子吃的虧,就在不俗上”。事實確實如此,退居鄉(xiāng)野的陶淵明過得并不好,一度饑腸轆轆,“餓得兩眼發(fā)黑”,不得不放下身段外出乞糧,也僅“討半斗糠皮、兩升面粉”。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人活一世,不應(yīng)為物質(zhì)耗盡一生,但必要的生活還是要有的,畢竟生活才是一切出發(fā)的基礎(chǔ)。
談到二人的區(qū)別時,何大草曾指出,陶淵明是亂世避世,而王維是盛世避世。王維生活物資并不短缺,但他不吃肉,不喝酒,連茶都不喝,清心寡欲。這些恰恰與裴迪相反,也可以看成是王維的“出世”之舉。然而,王維又不想完全脫離生活的底色,這也是他不贊同陶淵明的隱居方式,所以他認(rèn)為,“萬事皆空,肚子不能空”。
“詩和遠(yuǎn)方”勾起許多人的浪漫想象,實際上古人早就實現(xiàn)了這一“宏偉”目標(biāo),李白、杜甫等無不是游走四方,一路上也寫就許多精彩詩篇。但他們過得并不好,至少他們對自己的生存狀態(tài)并不滿意,時常處于生活的窘迫之中。
王維的避世生活其實很有趣。輞川別墅坐落于終南山腳下。終南山直到今天仍是四面八方隱士競逐之地。另一方面,輞川別墅離皇帝所居的都城長安僅幾十里地。這也為王維與朝廷保持聯(lián)系提供了可能。正因為離得不遠(yuǎn),所以皇帝才可能半夜召見他,就為王維這句“月出驚山鳥”的詩,而討個明白。
避世而又不遠(yuǎn)離,這就是王維。就像他的詩,看似一目了然,又似暗藏禪機(jī)。
詩仙與詩佛
李白是詩仙,王維則是詩佛。書中通過裴迪還有呂逸人的來信,多次將此二人鉤連在一起。
李白與王維同歲,據(jù)說都曾因玉真公主引薦,才有幸接觸上層社會,都曾受到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厚愛。但李白最終被唐玄宗變相逐出京城,而王維則安居他的輞川別墅,時不時還被召見。李白、王維都曾卷進(jìn)安史之亂的歷史漩渦。后來李白因卷入永王案被貶,而王維則因在安祿山部下任偽職被貶。
李白被赦免,興奮之余,于是有了“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詩是好詩,但李白與他所期待的入仕之路越來越遠(yuǎn)。王維被貶后,也留下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詩“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二人的詩都是借景喻情,但李白的顯然更直接,而王維的更含蓄。對此,裴迪有所不解,“有人嘆息,分明是平常之景,你寫來咋就有駭人心魄的意味呢?”王維的心里卻說,“我面對的豈是平常之景啊”。王維的詩就是這樣,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像是隔著一張薄紙,但你怎么也捅不破。
王維,字摩詰,源自《維摩經(jīng)》。他是凡間的佛,他又是佛間的詩人。直至走完人生的所有道路,他依然只能騎在入佛的門檻上。相較于李白的灑脫與無所顧忌,王維盡管在官場也不大如意,但要圓融得多。從他與唐玄宗下的那盤“只許贏不許輸和平”的棋局便可見一斑,他對官場的生存法則應(yīng)用自如。另一方面,他的清高又驅(qū)使他遠(yuǎn)離官場中的那些烏煙瘴氣。這也導(dǎo)致了王維進(jìn)退兩難,入世與出世并存的特殊性格。
如果說陶淵明“隱”這面鏡子照出的是王維的盛世避世生活,那么李白“忍”這面鏡子照出的則是王維的官場生存哲學(xué)。王維在朝廷雖然不能算是如魚得水,但也能算是從容應(yīng)對,比如恩師是張九齡,卻又與恩師的死對頭、權(quán)奸楊國忠比較合得來。王維特別能忍,在街市上,他寧愿挨拳師一拳,哪怕差點丟了性命,也得要回屬于自己的小狗。
書中寫到了兩人的“相遇”。說的是在酒樓上,有人說李白來了,結(jié)果王維眼里偏偏飛進(jìn)了沙子,睜不開眼,就這樣,兩大詩人完美錯過。但王維身邊的裴迪還有呂逸人顯然不愿錯過這樣的機(jī)會,他們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王維的“痛處”,“硬”是把李白擺在他的眼前。裴迪說“就你當(dāng)初和李白,彼此能感受到對方的存在,表情卻是漠然的”。呂逸人的信里也寫道,“曾經(jīng)有一個李白可能讓閣下暗暗嫉妒過,閣下是長安詩魁,他是大唐詩仙”。說不清這種感覺到底是歷史的遺憾,還是因為文人相輕,心底里的那份清高作祟的原因,也許只有王維自己能回答。
明明心里很想相見,行動上卻又猶豫不決。也正因如此,何大草說,“王維的魅力在于他的不徹底”。也許這也是禪吧。
單刀直入和羚羊掛角
書里寫到一位“過氣”的貴婦。雖然淪落到終南山的鄉(xiāng)野,但貴族氣質(zhì)猶存。王維最后贈給這位貴婦的字是“單刀直入”。與其說這幾個字是給那位貴婦的,不如說是給王維自己的。人就是這樣,越缺什么,就越希望什么。
有段對話,裴迪問:“放下你的禪,好好說話,不帶機(jī)鋒可以么?”但這是王維,不帶機(jī)鋒那還是王維嗎?所以他根本做不到,就像他與李白本來惺惺相惜,但又彼此放不下清高。明明他與楊貴妃的族兄、奸相楊國忠關(guān)系很好,但又以為別人看不出來,還故作疑問地問裴迪:“他圖我什么呢?”裴迪“單刀直入”地回答:“你的虛名。”
王維曾自嘲虛名,說那畢竟是虛的。裴迪的比喻恰當(dāng)貼切,“虛名未必就虛罷。一塊玉標(biāo)為和田玉還是藍(lán)田玉,賣的價錢就不同”。裴迪這里所說楊國忠看重王維的“虛名”,大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王維本身詩歌水平,寫不了詩,當(dāng)一個善于鑒詩的伯樂同樣能抬高自己的地位。另一個可能更令楊國忠不敢小覷,那就是唐玄宗也很喜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至于是不是真的喜歡,對于善于鉆營的楊國忠而言,并不重要。
在老方丈問王維如果給自己寫四個字寫什么時,王維給出的答案是“羚羊掛角”。這詞的原意指詩文的超脫,王維用在這里當(dāng)然恰如其分。更懂禪意的老方丈卻講了另一個更接近這四字字面意思的故事——所謂的超脫,只是人們刻意想象的結(jié)果。一旦這種想象上升為固化的思維,人們往往容易忘記了其最初的含義。
這里的最初,應(yīng)該說的是人性的本真。王維當(dāng)然有本真的一面,比如他在給呂逸人寫信時:“鼻涕滴下,他吸了一口,沒吸住,還是滴在了紙上”。
找回個人本真并不難。生活的本真,其實就源自生活的細(xì)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