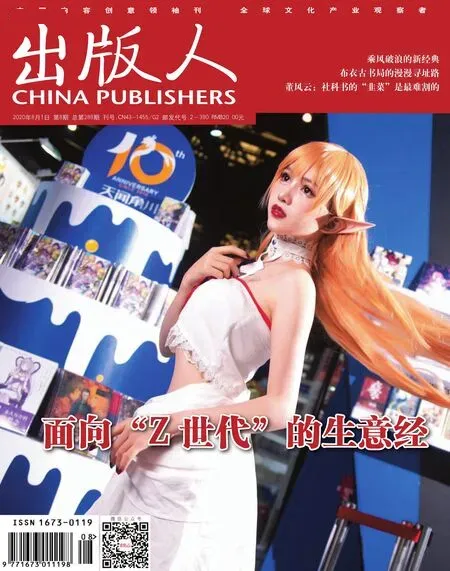閻連科:過度贊美,是對女性的傷害
文|袁復生(書評人)

閻連科 著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2020年5月定價:46.80元
有幾年,“國學熱”熱得不行的那幾年。
我時常在飯桌上,會和朋友們反復說起一個段子——
我老家有最后幾位讀古書的老先生,有位老先生走過小溪到了他小兒子家,對著兒媳婦開始訓話:“你們這些婦道人家啊,不要老是打牌,要講三從四德!”結果我那位族嬸沉默了十秒鐘,對著公公迷茫地發問:“公公,得得得,我嫁過來的時候那么窮,我究竟得了你們家什么東西啊?”老先生頓然無語以對,一口老痰,半天咳不出來。而我嬸娘的這句金句,也就成為我們當地流行一時的笑話。
在我讀完閻連科最新散文集《她們》之后,這故事又像一個幽靈似的,盤旋在我腦海之中。不僅是這個黑色幽默的故事,還有少年時代帶著我一起插秧、搞雙搶、看電影、看儺戲、去觀音寺燒香的她們,我看著她們上吊自殺,我看著她們在油菜花開的時候變成瘋子,口吐白沫通靈的神婆,與半夜喜歡吹笛子彈二胡的叔叔私奔的本家姐姐……
她們,向我奔涌而來。
在很多書評中,都會提及《她們》的第一章里,閻連科帶著兒子回到老家,偶遇當年的相親對象,情急之下,躲進了男廁所的故事。這個故事被人解讀為“鳳凰男的內疚”,因為這位與他相親的女性,是眾多相親對象中唯一有過婚約的一位。在一個物質與精神生活都極度匱乏的時代,閻連科遵從了自己的內心,決心從“相親模式”的婚戀關系中逃離。逃離故土和逃離故土相親的姑娘,本質上是逃離這種匱乏與沒有選擇自由的痛苦。
這種逃離,也是他與“她們”的一個起點。而逃離之后的回歸,帶著他生命經驗、見識的回顧與審視,則是閻連科書寫《她們》的獨特視角。
與閻連科以前充滿張力的作品大多不同,《她們》寫得有點溫柔敦厚。
但往往在平淡的敘事之中,閻連科小說家那種獵鷹一般的目光,就不經意流露出來了,與此同時流露出來的,還有那些女性“錐處囊中”的個性——比如 “睡著她還在夢里唱戲”的大娘,比如半職業通靈做法的“女巫”三娘……
除了家族中的女性,在《她們》的第七章中,閻連科查閱了很多縣志、史料、故土新聞,找到那些他覺得值得留下印記的女性——有為了追求“夫妻生活和諧”而勇敢離婚私奔的;有因為男友一輩子都買不起一塊手表,她設立目標攢夠100 個手表作為定情信物嫁給他,卻為了收集這100 塊手表成為了性工作者……這些女性,完全不是中原大地上勤勞勇敢美麗善良的女性代表。不管是否“正確”,但她們呈現出了真實的個性、困境乃至罪惡。
如果停留于此的話,《她們》已然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但《她們》顯然走得更遠,不僅寫了自己家族里的三代女性,更寫了家族之外更多的女性,以及時代在女性身上的變遷痕跡。更重要的是,閻連科有一種“拒絕贊美”的反思姿態。
在《勞作與女性生命學》一節,閻連科控訴勞作之于鄉村女性的損害。因為過度的勞作,他母親身上長滿了各種各樣的脂肪瘤,乃至后來在部隊醫院,軍醫非常不解地托著那一滿盤十幾個腫瘤對閻連科說:“你們農村的婦女太經得起病瘤折騰了!”
母親只是眾多無名無姓的“她們”中的一個。在我們的書寫傳統中,“為母則剛”占據了我們另一種主流敘事。面對這種贊美,閻連科斬釘截鐵地對我說:“對女性過度贊美已經是對女性過度的傷害。我們對女性對母親,偉大母親,所有的偉大母親就是讓她勛章勛章,再受勛章,但從來沒有思考過母親作為女人有什么權利?”
“恰恰是在一片贊美中傷害無數的女性。”這就是《她們》的寫作中,體現出來的一種難得的現代性。
在我們歷史與現實之中,無數的女性一邊被贊美,一邊被遺忘。對抗遺忘的,靠的不是記憶力,而是真實。
什么是真實?把人還給權利,把女性還給她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