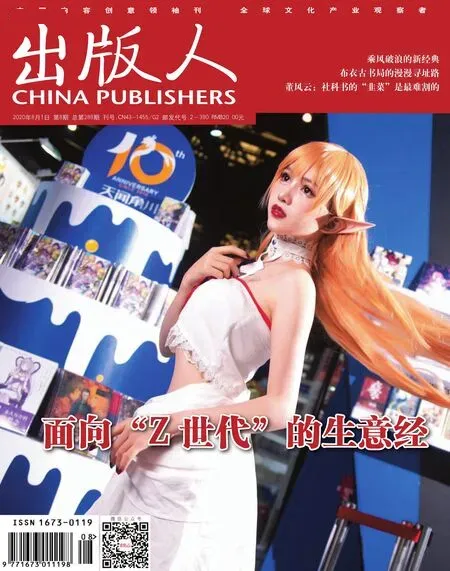《天賜》非天賜,厚土蘊芳華
文|遲 云
我與陳先云是山東出版集團的同事。
我是2014 年9 月調到出版集團任職的,第一次與先云見面,是2016 年1 月22 日上午,在她幫扶的村子村口。我代表集團看望慰問在農村任第一書記的三位同事,當時,陳先云作為集團唯一下派的女干部,駐扎幫扶安樂莊村。
陳先云幫扶的村子有三千人口,在當地是一個大村莊。在慰問走訪的過程中,我們走街串巷,進院入戶。陳先云不停地向我介紹他們開展的修路、養牛、助學等扶貧扶智的項目,介紹貧困戶的致貧原因和脫貧計劃,她的思想與感情的投入,使自己完全站到了村子發展的境況之中。出于職業習慣,當時我就意識到:一是農村,特別是社會變革時期的農村,蘊含著許許多多真善美和假惡丑的素材,是生活的富礦,可是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主動且善于開采的人越來越少了;二是陳先云有著較高的學養支撐,觀察細致、敏銳,思維清晰、有條理,表達又雅俗兼具、富有感染力,她具備了做“開礦人”的潛質;三是扶貧攻堅是當下社會的一個重點熱點,備受關注,投入的精力財力不少,但實施起來困難重重,過程充滿酸甜苦辣。所以,真實而藝術地反映這一題材的文學作品,必定是對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的貢獻。
我很認真地告訴她:一要用心做事,不負韶華;二要多交朋友,記錄故事;三要用心觀察,領悟思考;四要整理成書,對得起自己和社會。陳先云當時聽得很認真,很謙虛也很真誠地答應了,我們就這樣在漫天飛舞的雪花裝點的村口,在鄉鎮干部的見證之下,達成了一個充滿期待的約定。
時光荏苒,轉眼到了2018 年的春天。一天上午,陳先云抱著一疊書稿,很拘謹地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她說她已經完成第一書記的任務,回到山東畫報社的記者崗位快一年了,今天是來交作業的。她說的作業,就是她用心血寫出的約21 萬字的作品《天賜》(當時她定名為《月亮河》)。
利用業余時間,我非常認真地讀完了陳先云的作品。她簡練的筆觸細致而精到,彌漫在語言中的情緒如霧一樣絲絲縷縷,對鄉村景物獨具慧眼的描摹構筑出特定的意境,這一切為作品主題的豐富和人物形象的立體展示,培植了豐厚的文化土壤和濃郁的精神氛圍,使原創作品的誘惑力充沛地呈現出來。閱讀的過程并不輕松,可以說隨著故事的展開,隨著人物命運的曲折悲歡,我的心一直是緊收著的,情緒一直是緊繃著的。作者非常巧妙地選取了一個生于貧窮之家的留守兒童天賜的視角,帶著純潔善良的本性和混合著既自強又自卑的心態來觀察這個陰晴多變的社會,使周邊的一切都成為舞臺的背景或人物,或黑或白,或正或邪,或明或暗,種種勢力和因素都圍繞著生存、生活中世俗的現實利益和微茫之中的現實道義而展開。在這個貧窮的村莊里,“常書記”作為下派到村里的第一書記,工作的軌跡都活動在天賜的眼里,記錄在天賜的心里。“常書記”就是一個標靶,她的工作移動,串聯起了故事的梗概,她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勾兌成了作品細節的味道。作品中涉獵的農村發展可能遇到的問題,比如勞動力外流、因病致貧、黑惡勢力、留守兒童、教育落后、家庭暴力、買賣婚姻、老人贍養等,十分寬泛,讓人閱讀之后,仿佛聽到了鄉土的心跳,悲憫的情懷和擔當的責任禁不住油然而生。
讀過之后,我沉思了很久,仿佛又看到了陳先云迎著風雪在村巷穿行的身影,而《天賜》不正是浸潤著她兩年扶貧心血、反映千千萬萬個基層工作者頑強奮斗精神的作品嗎?它的意義,不僅僅是對她這兩年生命的綻放做的記錄,更是對我們當下的鄉村振興、精準脫貧事業做的記錄,為我們下派在貧困鄉村的第一書記留存了歷史形象,為蛻變之中的鄉村記下了困惑和期望、丑惡和善良。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陳先云的《天賜》非天賜,而是她扎根土地、深耕生活的積累,是她情懷擔當的寫照,是她生命歷程的一次閃光爆響。■

陳先云 著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2020年7月定價: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