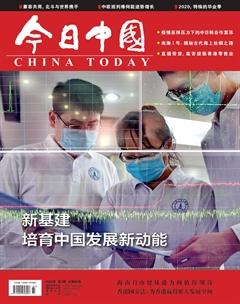顧嘉清:用聲音講述畫面之外的故事
晏學
“第一次感受到聲音藝術的精妙絕倫”。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聽了1分鐘的杜比全景聲宣傳片后,顧嘉清說,“我終于找到了我的天分和興趣天衣無縫的結合點的職業—聲音設計師。”
26歲的顧嘉清,出生于浙江省寧波市, 2015年畢業于中國傳媒大學音樂與錄音藝術學院錄音工程專業,兩年后赴美就讀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電影制作專業,攻讀碩士學位。作為聲音指導及聲音設計師,她參與制作過多部長篇影視作品,其中包括美國的《最后三天》及中國的《再見十八班》等。顧嘉清還擔任過美國《山間一日》《春花》《Crush》等多部獨立電影短片的聲音設計師。
2020年,顧嘉清在美國華納兄弟聯合制片的長篇電影《麥克白》中擔任聲音指導工作,她帶領團隊,歷時4個月,完成了影片后期聲音制作,最終以杜比全景聲的重放手段展示在觀眾面前。在談到聲音設計這份工作,顧嘉清說:“電影聲音設計就是用聲音,講述畫面之外的故事。”
決定成為聲音設計師
顧嘉清在大學主要學習聲學、音響系統設計等一些基礎理論知識。在大三結束的時候,顧嘉清有了一次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交換生的機會。在這一次交換過程中,一次觀影體驗讓顧嘉清對未來職業規劃有了全新認識。
在電影放映之前,電影院播放了1分鐘的杜比全景聲宣傳片。坐在千人放映廳的黃金聽音位置上的顧嘉清,第一次感受到了“熱血沸騰”的視聽效果。
在顧嘉清心目中,電影聲音設計,就是用聲音講述畫面之外另一半的故事。
“如果說畫面是將故事呈現在二維的屏幕上,那么聲音設計就是將這個二維的故事補全,變成一個三維的立體感受。如何在影視作品里用聲音來幫助塑造人物形象,刻畫人物的心路歷程是我最關注的事情。”
對于電影呈現出的音響效果,可能有很多觀眾認為是在拍攝現場實時錄制的。而現實是幾乎所有觀眾聽到的聲音都是經過處理、替換和補充,后期添加上去的。在顧嘉清眼中,從背景環境里的一聲狗叫到機器人變身時的聲音,都是聲音設計師根據人物的性格,故事的發展而特別設計的。
“對我而言,聲音的意象化和不確定性賦予了它巨大的可塑造性,從而賦予了創作者更多的想象空間,使其成為最有效的電影藝術創作手段之一。”顧嘉清理解中的聲音設計師,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創造性的職業。
認真打磨每一個細節
擔任電影《麥克白》的聲音指導,是目前顧嘉清最重要的履歷。
“從我拿到這個片子到最后完成整體的后期聲音制作一共花了將近4個月的時間。最開始和制片人聊片子的時候,確定了最后要混杜比全景聲。”在顧嘉清的介紹中,這部電影的聲音制作占據了重要地位。
作為一個歷史題材的劇情片,《麥克白》并不像科幻片或者動作片有很多明顯的聲音設計,只能在背景環境聲音設計上下功夫。因為電影本身又是年代戲,所以幾乎所有的背景環境當中的人聲都要后期重新錄制。加上拍攝預算的問題,在拍攝的時候不會找大量群演來實拍,需要后期通過特效補齊畫面之后,由聲音來填滿整體觀影的恢弘感受。因此,在整個制作過程中,光錄制背景環境的人聲,就錄了10天。其中一天甚至請了50個群演進棚,錄制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街上的抗議聲音、在劇院觀看演出時群眾的反應,以及那個年代酒吧、餐廳、大街上的環境音。
“這部電影有很大戲份是在劇院里發生的。我們假想了大量演員排練及工作人員交談的對話,把它錄下來,放在背景環境當中,營造一個30年代忙碌的劇場的場面。我們還請了能說各種不同語言的演員來錄制這些對話,來營造一個30年代紐約各路移民聚集的景象。這些如果不追求三維效果,完全可以不做。當然,電影的寓意表達就會差很遠”,顧嘉清介紹電影聲音錄制時說。不過這種精細的打磨還體現在方方面面。
在電影制作中,除了錄制背景環境中的人聲,還需要制作大量符合當年街道上的聲音、辦公室的聲音以及公寓樓里的聲音。也因此,顧嘉清帶領著自己團隊做了各種各樣的研究。從那個年代普遍開的都是什么牌子什么型號的車,有軌電車是在哪一年從紐約市消失的,到移民都是從哪個國家來的,說什么語言,30年代的流行語言都有哪些,全都一一去查證。
“這個大街上的車流聲,是一層層疊加風聲、古典車行駛聲、鳴笛而做成的,比做現代電影費時很多。”顧嘉清說,“如果不認真打磨一部電影,這些也完全可以不做。但我相信,好的結果和成就都來自于認真地打磨每一個細節。”
在最后混錄杜比全景聲的時候,顧嘉清和她的團隊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技術難題。例如,杜比全景聲在混音的時候必須要求畫面和聲音制作工程是24幀。但是,在最初拍攝和畫面剪輯的時候,一直是23.98幀,這就導致了在最后混音之前要將整體的聲音制作工程做采樣率的轉換,從23.98轉到24幀。在對比了各種轉換的方法之后,為了能夠保證在截止日期前交片,最后還是采用了在Protools(Digidesign公司出品的工作站軟件系統)里導入的時候做一個采樣率的轉換。
“當時非常擔心會出現聲畫不同步的問題,我仔仔細細地盯著屏幕看了好幾遍這一近兩個小時的電影,來檢查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同步。也是因為杜比全景聲的緣故,在聲音導出之后,做聲音和畫面合成的時候不能在一般的房間里檢查有沒有問題,一直到放映前三天,在一個杜比全景聲認證的影院里測試的時候,才第一次聽到最終的成品,懸著的心才最終放下來。”顧嘉清回憶起制作的經歷時說,“認真打磨每一個細節,就是我從事這個職業的初心”。
紀錄片聲音設計需有勝于無
在談到紀錄片的聲音設計時,參與了多部紀錄片聲音設計的顧嘉清表達了她的看法。
“我覺得和劇情片的聲音設計相比,雖然紀錄片往往是以一個客觀的角度來記錄發生的事情,但其實在制作的過程中融入了很多導演自己的想法。”表達真實,是顧嘉清在制作紀錄片聲音時的主要標準。“其實往往越在生活中遇到事情,越難以將這個聲音做得真實。如果觀眾注意到聲音了,那就說明你還沒有做好。”
在制作美國影片《山間一日》的時候,顧嘉清團隊記錄了兩名身有殘疾的女性追尋愛情的過程。其中一位是在一場事故中失去了雙手雙腳的年輕護士。有一場是影片要拍攝她在家如何吃飯,如何化妝等家庭瑣事,以及最后上床睡覺的過程。導演很想展示她堅強的外表下孤獨的內心。顧嘉清當時就通過背景環境的聲音設計,突出窗外的鳥以及野外蛐蛐的叫聲,搭配畫面,以展現她內心的孤獨。
“聲音往往會幫助導演去傳達一些他想要的信息。紀錄片的聲音設計大部分時候是需要一種非常自然、有勝于無的設計”,顧嘉清說。
顧嘉清的作品入圍過包括加拿大Big Sky紀錄片電影節、學生奧斯卡、洛杉磯短片電影節、中國紀錄片學院獎和廣州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等獎項。而作為聲音設計師,她曾于2018年及2019年,兩次提名具有聲音屆“奧斯卡”之稱的MPSE金卷軸獎。
對于未來職業規劃,顧嘉清有著自己的想法。
“經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認為電影行業將被迫迎來改革。虛擬環境電影制作將會慢慢成為主流。”因為虛擬環境電影制作的拍攝方法不需要有大量的現場人員,在給導演更大的創作空間的同時,也降低了拍攝成本。顧嘉清表示,自己正在研究如何實現這種虛擬電影的音效設計,希望能為聲音設計事業的發展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