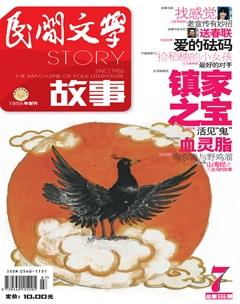找感覺
李謙

不久前,我為了創(chuàng)作一部東北農(nóng)村扭秧歌題材的小說,采訪了一些當(dāng)年的秧歌隊(duì)員,不僅勾起了很多往事的回憶,還了解到這種曾經(jīng)火爆東北農(nóng)村一二百年的拜年形式已經(jīng)徹底消失,因?yàn)樯鐣?huì)城市化進(jìn)程的強(qiáng)力推進(jìn),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大秧歌如火如荼,可再也找不回當(dāng)年的感覺了,扭秧歌拜年,已經(jīng)成為生長在東北鄉(xiāng)下的中老年人的群體記憶。在一種復(fù)雜情緒的驅(qū)使之下,我產(chǎn)生了撰寫《找感覺》的沖動(dòng)。故事里的秧歌頭兒劉發(fā)、“白蛇”李鮮花、為請秧歌哭鬧的男孩,以及淳樸的鄉(xiāng)親們對善的堅(jiān)守和知恩圖報(bào)的情懷,無一不來自火熱的生活,這也正是關(guān)東這片熱土?xí)r時(shí)刻刻能讓我迸發(fā)創(chuàng)作欲望的原因。
臘月十五那一天,氣溫達(dá)到了零下三十多度,漫山遍野白茫茫的。前些年,一進(jìn)臘月門,道上都是去趕集辦年貨的人們,現(xiàn)在卻不同了。
這時(shí),一輛轎車駛進(jìn)了秧歌屯,在寂靜無人的村道上緩緩駛了一個(gè)來回。司機(jī)隔著低矮的墻頭見村頭一戶人家有一個(gè)老人在院子里打水,忙下車,敲響了院門。老人名叫劉發(fā),他打量了一下門外的人,疑惑地問:“你找誰?”
司機(jī)是個(gè)五十多歲的男人,滿臉堆著笑說:“大叔您好。我早就聽說咱這兒有一個(gè)秧歌屯,從前一進(jìn)臘月門,就組織秧歌隊(duì)扭拜年大秧歌,聽說最紅火的年月,家家都參與進(jìn)來,從臘月十五排練起,一直到二月二龍?zhí)ь^結(jié)束,大馬車?yán)?duì)員們,扭遍了附近幾個(gè)鄉(xiāng)。那個(gè)熱鬧,城里的人都跑來看。說的就是這個(gè)屯子吧?”
聽了這話,劉發(fā)立馬興沖沖地說:“嗨,就是咱們這兒!沒錯(cuò),沒錯(cuò)!想當(dāng)年,我是秧歌頭兒呢,還在隊(duì)里扮孫悟空,到哪個(gè)村都有一大群孩子跟在后頭起哄,齊聲喊著‘孫猴子、孫猴子。嘿,真帶勁兒!咱的秧歌隊(duì)大啊,舍得投資,扮相齊全。白蛇青蛇、唐僧師徒、八仙過海、跑旱船、媒婆、大頭人……應(yīng)有盡有!”
說著話,劉發(fā)忙請司機(jī)進(jìn)了屋,拿煙倒茶,如同招待老朋友。司機(jī)樂呵呵地進(jìn)了劉家,“大叔,我姓林,您就叫我大林吧。我姥姥家就在旁邊那個(gè)屯子,小時(shí)候過年愛住姥姥家,一住就是一整月,追著你們屯的大秧歌看,真過癮!”他笑哈哈地說著,兩人之間的生疏又褪去幾分。“大叔,您是一個(gè)人住啊?”大林問道。
劉發(fā)嘆了口氣:“唉,老伴兒走了五六年了,兒子媳婦在城里打工,安了家,也把孫子接進(jìn)城上學(xué)了。原本他們讓我也進(jìn)城養(yǎng)老,可我不習(xí)慣住城里,就留在了屯子里。”
大林若有所思地點(diǎn)點(diǎn)頭:“那,現(xiàn)在你們屯這秧歌大拜年的習(xí)俗……”
“哪兒還有什么秧歌拜年!”劉發(fā)激動(dòng)地說,“早沒了!現(xiàn)在不打獵,不伐樹,屯里也沒多少土地,年輕人都進(jìn)了城,留在屯里的都是些老弱病殘,平時(shí)屯里那個(gè)靜啊。只有到了臘月二十六七,才開始熱鬧起來,孩子們回來過年,待上六七天,又一股腦都走了。至于秧歌隊(duì),當(dāng)年那些隊(duì)員們,大都是我這歲數(shù)了,老胳膊老腿哪還折騰得動(dòng)。臨時(shí)回家住幾天的孩子們,哪里肯搭工夫練這玩意兒。所以,秧歌屯早就是個(gè)虛名了!沒這習(xí)俗了!”
劉發(fā)的話里帶著幾分感傷,大林連連點(diǎn)頭。“大叔,是這么回事,我是做生意的,不瞞您說,多少也有些家業(yè)。不愁吃不愁喝了吧,小時(shí)候的一些事兒就刻骨銘心地想。現(xiàn)在城里的秧歌隊(duì)不少,哪個(gè)廣場上都有一伙,可我就是想念小時(shí)候追著秧歌挨個(gè)屯子跑的日子,所以特意回來找感覺。但是我也猜到了會(huì)是這個(gè)樣子……”
兩人同時(shí)嘆氣。
“大叔,不知道屯里那些老秧歌隊(duì)員們,還有沒有心思再聚到一起,組織秧歌隊(duì)了?”
劉發(fā)一下愣住了,老隊(duì)員?當(dāng)年的小隊(duì)員們,現(xiàn)在也六十開外,老隊(duì)員也七八十歲了。每年正月,大家伙兒聚到一起看牌神侃,沒有一個(gè)不感嘆歲月流逝得太快。可是讓他們再下場子,敲鑼打鼓扭起來,怕是……“林老板,大家都一把年紀(jì)了,高蹺誰還敢踩?跌了摔了不給兒女們添麻煩嗎?組織秧歌隊(duì)就是為了到各家各戶去拜大年,可誰家愿意請一支老年秧歌隊(duì)呢?鬧不好出點(diǎn)兒事故,都得吃不了兜著走!”劉發(fā)連連搖頭。大林笑了:“大叔,我都想過了。高蹺肯定不能踩,我們就扭地出溜兒。咱也不去外屯,就在自己屯里拜年!我出資給大家辦意外保險(xiǎn),真有麻煩了也有人出醫(yī)藥費(fèi)。您看怎么樣?”
劉發(fā)被說服了,當(dāng)下抄起電話,把當(dāng)年那些老秧歌隊(duì)員們都請到家里,說有要事商量。
很快,劉發(fā)家就擠滿了人,聽明白林老板的意思,大家的眼睛閃閃發(fā)亮,紛紛表示愿意參與扭秧歌大拜年。
“這回把秧歌撿起來,甭管年節(jié)咱都扭,像城里人那樣老有所樂。身體好了,孩子們才能安心在外打拼!”說話的是當(dāng)年扭白蛇的李鮮花。當(dāng)年,她可是秧歌隊(duì)的靈魂人物,從十幾歲扭到三十多歲秧歌隊(duì)解散。
李鮮花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話,于是全票通過,秧歌屯的拜年秧歌隊(duì)成立了。大家紛紛表示,當(dāng)年的鑼、鼓、镲、服裝、彩扇、道具,都在倉房里收著,保證啥都不缺!
大林這時(shí)對大家說:“好!大家太給力了!從前請秧歌隊(duì)拜年的一般都是當(dāng)?shù)赜蓄^有臉的人家,你們賺的是打賞錢。現(xiàn)在我們不出屯子,秧歌隊(duì)給屯子里每一家都拜年,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打賞就算了。我承諾,從排練第一天開始,一直到表演結(jié)束,每人每天我付一百塊的辛苦錢。就這樣定了!”
大家高興之余,又很納悶,這個(gè)城里的大老板為啥對秧歌隊(duì)情有獨(dú)鐘?就為了找回童年的感覺?這付出也太大了吧?可是大家跟他不熟,也不好多問。大家約好了第二天早上八點(diǎn)在劉發(fā)家的大院集合,排練場地就定在劉家。他家的院子大,跑得開。
第二天不到八點(diǎn),人就到齊了。這些生活在鄉(xiāng)下的老人,仿佛被喚醒了青春,眼睛里充滿了神采。但卻出了一個(gè)問題,道具和服裝出了問題。鼓被耗子嗑了洞,衣服一扯一個(gè)口子———秧歌服顏色鮮艷,料子滑溜,質(zhì)量卻很差,放了二三十年,不霉才怪呢。
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商量怎么補(bǔ)救,林老板到了,樂呵呵地從車后備廂抱出兩個(gè)大包裹,里面都是色彩艷麗的秧歌服、彩扇、手絹,一應(yīng)俱全。
排練開始了,大家雖然老了,可基本功的底子還在,喇叭匠的曲子還不跑調(diào),打镲敲鼓的人手也不抖,地出溜兒又不用踩高蹺,才一天下來,就已經(jīng)有模有樣了。
最有趣的是,大林也穿著一身鮮艷的服裝上了場,他扮的是媒婆:頭上戴著假發(fā)疙瘩鬏兒,涂著艷麗的腮紅,左手挎著竹編籃子,右手執(zhí)著長長的煙袋鍋?zhàn)印悬c(diǎn)兒跟不上節(jié)奏,時(shí)不時(shí)還順拐,給大家增添了不少笑料。有人恍然大悟,說,看來大老板是為了圖一樂,才舍得為咱們花這些錢,咱就是陪人家樂呵的!
這話傳開了,大家都覺得有道理,興高采烈地說,這事兒要瞞著孩子們,等他們回來過年,給他們一個(gè)驚喜。
第二天,有幾個(gè)跟著孩子在城里養(yǎng)老的老隊(duì)員也被叫回來了,幾天下來,秧歌隊(duì)已經(jīng)有三十多名隊(duì)員,接近當(dāng)年的規(guī)模。
在嘹亮的嗩吶聲里,除夕到了。初二一大早,大林開著車趕到了秧歌屯,隊(duì)員們早已經(jīng)集結(jié)在劉家院子里,劉發(fā)的兒子媳婦滿臉喜氣,同時(shí)點(diǎn)燃了兩掛鞭炮,又放了六個(gè)二踢腳和六個(gè)煙花,取“六六大順”的寓意,嗩吶聲中,秧歌隊(duì)開始扭起了第一場大拜年秧歌。村子里家家戶戶大門洞開,人們穿著喜氣洋洋的新裝來到劉家。
進(jìn)入實(shí)戰(zhàn),隊(duì)員們仿佛回到了當(dāng)年,扇子手絹舞得翻飛,動(dòng)作靈活得根本不像是一群老人。二十分鐘后,隊(duì)員們出了劉家,進(jìn)入第二家開始大拜年,例行的放鞭炮迎請之后,有的年輕人看得眼熱,跟著下場順手搶過誰的扇子或者手絹也扭起來。這也是這地方扭秧歌拜年的風(fēng)俗習(xí)慣,觀眾隨時(shí)可以下場參與。
一天一天過去,轉(zhuǎn)眼到了初六,人們逐漸回城,下場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初六是秧歌隊(duì)拜年的最后一天,因?yàn)槌跗吣贻p人就要返城上班,過了初七,秧歌屯就恢復(fù)了從前的寂寞。
大家想給全屯每一家都送去祝福,最后一站是五保戶老人楊三槐家。楊三槐前年就進(jìn)了敬老院,他的小木屋已經(jīng)快歪倒了。有人說,楊三槐都不在這兒住了,別扭了,怪累的,反正也沒人看見。劉發(fā)搖搖頭說:“三槐雖然不在這兒住了,可他的房子、土地,還都在秧歌屯。認(rèn)落一屯,不落一鄰,聽說三槐的身體不大好,扭秧歌拜年圖的就是一年里開個(gè)好頭,保平安健康!”
于是,喇叭匠提起了沉重的喇叭,隊(duì)員們扭動(dòng)著疲乏的腰身,開始了最后一場大秧歌。
這一場結(jié)束,夕陽即將落下,隊(duì)員們收起扇子和手絹,心里有點(diǎn)兒感傷。大林拿出早就準(zhǔn)備好的大紅包,給每個(gè)隊(duì)員發(fā)了一個(gè)。
隊(duì)員們面面相覷,劉發(fā)說:“林老板,這錢我們不能要。”
“為什么?我們不是說好了嗎?”大林很奇怪。
“其實(shí),我們更應(yīng)該感謝的是你!是你的組織,讓我們找回了當(dāng)年的感覺。人到老了才知道,能夠找回年輕時(shí)的心情,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們收獲這么大,還要你的錢,沒道理呀!”
大林笑了,“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四十多年前,村子里有一個(gè)姓林的外來戶,搬來沒兩年男的得病死了,女的領(lǐng)著一個(gè)五六歲的男孩,過得非常苦。就在那年正月,小男孩每天追著秧歌隊(duì)跑,回家跟媽媽哭著鬧著要請秧歌隊(duì)來家里扭秧歌。媽媽流著淚哄孩子,說咱家不是有頭有臉的人家,人家不能來,來了咱也給不起賞錢。可孩子聽不懂這些,怎么哄都是鬧。鄰居的秧歌頭兒看見了,他跟隊(duì)員們商量,破例在小男孩家扭了一場,卻不肯收賞錢。那以后,每年春節(jié),秧歌隊(duì)都會(huì)給小男孩家免費(fèi)扭一場拜年秧歌,連著好幾年,直到他和媽媽搬回老家……”
劉發(fā)大吃一驚,緊盯著大林,突然一拍大腿:“對,是你!你是住我家鄰居的小林子!你媽呢?還好吧?”
大林的眼圈紅了:“我是小林子,我媽前不久去世了,臨終前念念不忘秧歌屯。我很后悔,沒早點(diǎn)兒帶她回來看望大家。這幾十年里,無論我做什么,都不會(huì)丟掉一份善念,也因?yàn)檫@份善念,我在事業(yè)上得到了很多幫助。這可能是我成功的秘訣吧,而這秘訣,正是來自咱秧歌屯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