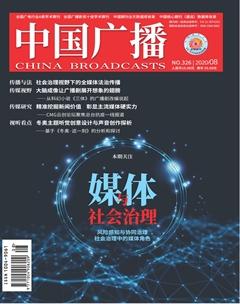廣播音頻與互聯網移動音頻的融合發展
賴黎捷 顏春龍
【摘要】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深度改變了傳播生態,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進入縱深階段。在廣播向智能媒體轉型升級中,移動音頻市場規模雖然穩步擴大,但也遭遇了優質人才短缺和產品不足等瓶頸。本文從廣播網絡化、音頻化發展趨勢出發,結合廣播音頻、互聯網移動音頻各自的特點、短板,梳理二者的發展現狀及互融的現實路徑,為廣播音頻發展提供思路。
【關鍵詞】廣播音頻 移動音頻 網絡化 音頻化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4月28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發布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8.97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3%,移動互聯網使用持續深化。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攪動了音頻生態圈,傳統廣播受到巨大沖擊,而移動音頻迅速崛起。傳統廣播如何向移動互聯網發展?移動音頻如何找到可持續的盈利模式?傳統廣播、移動音頻以及有聲閱讀、在線音樂等相關產業如何構建以音頻為中心的良性生態圈?這是擺在廣播媒體人面前亟待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2017年,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人工智能作為國家戰略在各個領域推進。除了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的運用,智能設備已經成為音頻產品與音頻內容生產無縫對接的首選路徑。與之相適應的是,以中央廚房、云平臺、可視化、短音頻、內容付費等為標志的智慧型廣播也全面崛起。
本文試從廣播媒體的現狀以及在向移動互聯網發展過程中遭遇的瓶頸人手,探討其如何以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為支撐,與快速發展中的移動音頻平臺實現深度互融,共生共長。
一、移動互聯時代,廣播的發展現狀及瓶頸
傳統廣播發展至今,從傳播渠道上經歷了從廣播電臺到網絡電臺再到“兩微一端”新媒體呈現。從傳播技術上看,經歷了從以調幅/調頻為主的無線電傳輸到以數字廣播為主的互聯網傳輸,再到以音頻應用為主的移動互聯網與人工智能傳輸;從傳播形式上看,經歷了從現場直播到錄播,再到在線直播,從單向傳播到互動傳播再到以用戶為主導的精準傳播。
(一)移動音頻競爭,廣播媒體壓力巨大
在報紙、雜志、電視等傳統媒體被網絡媒體沖擊得風雨飄搖的背景下,廣播是近幾年勉強支撐、尚沒有大面積衰退的媒介,但困難已經顯現,尤其是地市級及以下的廣播,普遍出現了影響力下降、營收困難等情況。廣播媒體不斷探索、創新,積極向全媒體轉型。近年來,上海廣播電視臺推出“阿基米德”音頻客戶端,探索廣播向移動音頻的轉化;廣東廣播電視臺珠江經濟臺探索廣播電商模式,江蘇廣播電視臺推出“大藍鯨”系統,探索音頻與綜藝視頻等的融合。2020年3月,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聲音聚合平臺“云聽”正式上線,依托總臺優勢資源,聚焦泛文藝、泛知識、泛娛樂三大品類,為各類終端用戶提供優質的聲音產品和服務。
然而,目前廣播媒體所辦的音頻客戶端內容多集中于音樂、娛樂、都市生活等領域,且同質化程度越來越高,而在人文歷史、商業財經、教育培訓等領域則乏善可陳,①尚需要拿出較大力度加以改進。而與之相對照的是,市場化的移動音頻平臺在用戶內容生產、泛娛樂化社區經濟、知識付費等方面風生水起,逐步形成了差異化競爭態勢。移動音頻領域的競爭,廣播媒體的壓力不小。
(二)廣播互聯網化的瓶頸
1.產消分離,內容創新不足
傳統廣播遭遇的瓶頸首先是產品問題。缺乏互聯網思維,特別是缺乏面向移動互聯網用戶的產品開發意識,造成產消分離,內容創新不足。
廣播傳播模式過去為一對眾的單向傳輸,音頻內容生產以專業化的新聞、音樂、交通和都市娛樂頻率為主,播出方式以固定時段的預定節目為主;移動互聯網端的用戶則以趣緣為主導,向科學、教育、衛生、人文、地理等各個領域垂直延展,閱聽形式以碎片式、場景化收聽為主,偏好任意點播、在線收聽等。目前,不少傳統廣播的互聯網化都局限在對“兩微一端”的盲目擴展,缺乏對移動互聯網內生動力的挖掘和與移動音頻平臺的協同,缺乏對與移動互聯網媒介屬性適配的個性產品的研發。
2.生產粗放,管理機制落后
廣播媒體由于長期獨立于市場機制之外,對于新技術、新事物的敏感度以及基于市場的創新思維和管理手段,都與移動互聯網下市場的實際要求相距甚遠。傳統廣播向新媒體的轉型,往往是廣播加上互聯網,其生產流程和管理機制并未實現根本轉變。有些廣播媒體還是在合并后的廣播電視集團中的獨立存在,并沒有與電視、新媒體真正重組、互融;有些廣播媒體雖然與電視媒體合并共同打造新媒體,但每個頻率或終端都由其獨立的團隊和管理機制進行運作,難以形成協同生產。從人力調配到運行依然是傳統媒體思維方式,是傳統廣播向移動互聯網的單向融入,缺乏對移動音頻應用平臺的主動合作和對移動端用戶的主動吸納。其聽眾大多從傳統電臺遷移而來,新增移動端用戶數量不多,黏性不強,還沒真正實現移動互聯網化。
3.大數據運營能力欠缺,盈利模式單一
廣播媒體在向新媒體轉型過程中,其大數據運營能力普遍欠缺,缺乏精準定位、適銷對路的音頻產品,其盈利模式仍局限于傳統的廣告變現模式,缺乏對粉絲經濟的開拓和在新媒體端的流量變現方式。
現在,部分廣播媒體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開始重視大數據技術在整個生產流程中的運用,如陜西廣播電視臺音樂廣播通過大數據挖掘,對播出歌曲在網絡中的點擊熱度、評論分析、用戶心理、熱播時間等進行全息測算。黑龍江廣播電視臺成立戰略數據部,創建聽友數據庫。②湖南長沙市廣播電視臺提出營銷整合三全策略,全媒體營銷、全案代理、全效果跟蹤。③但這些嘗試大多仍限于對用戶端的分析,還沒有滲透到從研發到生產的全流程,其后續投入、技術開發、節目生產尚未形成良性互動的產業鏈。
4.版權維護不足,跨界合作沒有形成機制
廣播媒體專業性強、制作精良,但版權意識不足,版權維護投入不夠,沒有實現音頻產品的價值變現,特別是沒有形成以知名主播為核心的lP產業鏈。
受無線傳輸技術限制,地方廣播媒體只能將節目覆蓋到規定的區域內。走向移動互聯網后,廣播借助移動互聯網、車聯網、物聯網形成新的傳播生態,不僅要發揮自己的云平臺優勢,還要與其他移動音頻平臺進行合作,甚至是跨媒介合作。同時,向教育、出版、娛樂、醫療、體育等多領域跨界,攜手多平臺、多領域共贏。目前,上述這些行動還缺乏相應的機制和動力保障。
二、廣播網絡音頻化之路
廣播媒體互聯網化的最成功產品是播客。早在2005年,美國《連線》雜志曾預言播客將取代傳統廣播的地位。時隔十載,播客在互聯網音頻平臺經久不衰,廣播也以音頻客戶端的形式在互聯網上與其他在線音頻形成共生互融的新生態。
(一)內容移動化:與細分化場景適配的短音頻
短音頻是傳統廣播適應移動互聯網碎片化的結果,也是其發揮自身專業制作優勢的有效路徑。短音頻主要是對廣播端節目進行二次加工,制作成5分鐘以內的精品,適應用戶移動化、碎片化消費的場景需求;同時也便于分類、標記和檢索。2016年,上海廣播電視臺東方廣播中心推出短音頻戰略。2017年,吉林廣播電視臺“沐耳FM”平臺和專門負責短音頻產品生產的機構“聲音工廠”合作,推出《英雄面館》《意聆》《沐耳公開課》等原創類短音頻節目。④
(二)傳播形式升級:廣播可視化
廣播向新媒體轉型,走向全媒體,首先體現為傳播形態的多向融合。廣播節目不再局限于聲音形式,而是向多感官接收形態拓展,廣播節目不僅要可聽、可視、可讀,甚至可運用。其中,廣播可視化尤為突出。早期的廣播可視化只是將廣播節目的主持現場向聽眾開放,如重慶人民廣播電臺就曾將直播間放在百貨商場的底樓,讓人們看見廣播的工作狀態,打造“看得見”的廣播。借助新媒體手段,近年來廣播媒體頻頻進行直播間視頻直播,真正實現了可視化。2015年4月3日,原央廣文藝之聲頻率“海陽工作室”與百度“實時搜索”共同推出的廣播全媒體產品“圍觀海陽”,以視聽方式進行實時直播,并融入彈幕等互聯網元素,使廣播掙脫了聽覺的束縛,實現了從聽到看的自我迭代。⑤廣播可視化打破了音頻的渠道限制,豐富了媒體與受眾的互動手段,進一步拉近了與受眾的距離。
(三)端口融合:從多平臺聚合到智能設備
端口融合是媒體融合的重要方式。廣播媒體在移動互聯網上開設“兩微一端”,入駐社交媒體、移動音頻平臺,并建立起合作關系,讓廣播有了更多的聲音出口平臺。2015年,國內幾乎所有的廣播電臺都入駐了新浪“微電臺”。智能設備是一個新的端口,目前,騰訊“聽聽”、阿里“天貓精靈”、百度“小度”等紛紛入局。⑥智能設備在產品多樣化、使用場景等方面與移動互聯網音頻消費趨勢不謀而合,適合家庭陪伴或在線購物等多場景生活服務。
(四)資源整合:建立云平臺與用戶數據中心
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為廣播向移動互聯網轉移創造了有利條件。2015年,原央廣建立的中國廣播云平臺整合了60家地方臺的頻率資源,探索臺臺聯盟的合作方式。黑龍江廣播電視臺的戰略數據部建有聽友數據庫,在廣播內部可以整合各地節目資源,形成區域互補、上下聯動,做到職業廣播人與專業創作者的協同合作。
(五)整合營銷:打造廣播電商
廣播向移動互聯網方向的轉化,逐漸走上了強化服務功能、打造綜合平臺的道路。蘇州廣播電視總臺的“無線蘇州”就屬此類,其定位為城市公共生活服務平臺,產品涵蓋天氣、路況、資訊、生活服務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元產品聚合、服務功能強化的必然結果便是將線上線下活動進行無縫鏈接,廣播電商成為傳統廣播整合營銷的又一拓展之路。上海廣播電視臺東方廣播中心、上海東方購物聯手打造全國首家全媒體購物平臺——東方廣播購物。廣東廣播電視臺珠江經濟臺構建了“一平臺(網絡商城)、一節目(常態電商節目)、一電商日(每月一次廣播電商日)”的發展思路,江蘇廣播電視臺的“大藍鯨”客戶端將所有廣播電視節目、活動與銷售充分融合。
三、移動音頻反向與廣播的融合
(一)內容融合:集成電臺
早期的互聯網移動音頻向廣播的融合,主要表現為“FM化”和集成傳統廣播的節目內容。它們的名稱也幾乎都以“FM”為后綴。“蜻蜓FM”被稱為“網絡收音機”,一直與廣播媒體合作密切。2013年以前,其內容囊括了3000多家傳統廣播媒體和1000多家高校廣播的節目內容。“喜馬拉雅”等其他移動音頻也或多或少地集成了傳統廣播媒體的節目。
(二)團隊融合:吸納主播
將傳統廣播媒體的優秀主持人納入創作團隊,是互聯網移動音頻進行團隊融合的常見做法。“蜻蜓FM”在2015年啟動PUGC大賽,大規模邀請傳統廣播媒體主持人人駐,在線創作音頻作品。“喜馬拉雅”的發展,經歷了從用戶生產內容( UGCl到專業生產內容( PGC)、再到專業用戶生產內容(PUGC)的轉變,其中專業生產內容模式有賴于其向傳統廣播媒體挖掘優秀主持人資源。
(三)盈利模式融合:專業用戶生產內容
用戶生產內容由于充分調動用戶參與內容生產的積極性而被移動音頻青睞,早期的“喜馬拉雅”以及“荔枝FM”均采用用戶生產內容模式。特別是“荔枝FM”,將“人人都是主播”的理念滲透到音頻生產、播出及營銷的各個環節中。早期的專業生產內容主要指傳統廣播中職業音頻制作者的高水平制作。專業生產內容是“蜻蜓FM”一直堅持的內容生產模式,這種模式有利于形成頭部IP,進而實現價值變現。2018年,“蜻蜓FM”宣布將投入10億元扶持金用于打造主播孵化體系,將主播職業化向前推進。采用專業用戶生產模式的還有“喜馬拉雅”,其將傳統廣播所擅長的專業生產內容與移動互聯網適配的用戶生產內容模式相融合,在內容生產的廣度和深度上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四)場景融合:車聯網與智能設備
移動音頻的移動化傳播優勢與傳統廣播中的交通廣播不謀而合,這促使其向交通廣播、車聯網以及相關智能設備領域進行拓展。移動音頻與交通廣播的融合,實質上是以消費場景融合為訴求,移動音頻通過開發汽車前裝與后裝設備向交通廣播領域滲透,并在可穿戴設備上布局移動消費場景。如“蜻蜓FM”客戶端被預裝在福特、奧迪等品牌汽車中;“考拉FM”生產了全球首款內置3G通信模塊的車載智能音箱,用戶可免費收聽音頻內容。⑦
四、廣播音頻與移動音頻互融的理性思路
廣播媒體與移動音頻平臺各有優勢,前者擅長核心內容生產,后者擅長多渠道推廣與分發。二者互融,可以從三個思路出發:一是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從人、財、物到管理機制的全方位資源共享,二是以準社會交往為基礎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融合及其分層培養機制,三是基于“大音頻”理念的跨界合作、共贏的音頻生態圈重構。
(一)以人工智能技術為支撐,打造智慧型廣播
廣播的痛點之一在于其節目內容的數字化、移動化不夠徹底,如有限的廣播可視化應用,短音頻形態與細分場景的匹配度不夠,用戶數據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遠未達到精準匹配和營銷。移動音頻在用戶數據用于個性化節目推薦、智能終端設備的布局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但在核心內容生產、節目資源與場景化消費匹配等方面還較為乏力。雙方互融過程中,均遭遇可持續盈利模式、版權維護等困局。
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建立統一的、開放的、可共享的數據收集分析應用平臺,打通多平臺數據資源,對雙方生產者、消費者、音頻生產資源等各類數據進行充分挖掘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全產業鏈資源整合.進而打造智慧型廣播。新型廣播可形成從資源聚合的云平臺到以場景打造和社群經濟為基礎內容生產的新媒體化,實現集智能設備、用戶數據、綜合服務功能于一體的終端融合的智能化生產。這有助于解決人員、機制、版權、價值變現等一系列難題。
(二)以準社會交往為基礎,建立生產消費者養成體系
準社會交往由心理學家霍頓( Horton)和沃爾( Wohl)于1956年提出,是指媒介使用者對媒介人物產生情感依戀,進而發展出一種想象的人際交往關系,這種交往關系與真實的社會交往有一定的相似性。準社會交往中的媒介使用者沉迷于與媒介人物的互動,并延伸為實際消費行為,屬于沉浸式傳播。這種原理在音頻主播與其用戶之間得以廣泛運用。“蜻蜓FM”所著力打造的頭部IP就是利用了優質內容生產者的品牌效應,吸附粉絲,進而提升流量;“荔枝FM”則利用粉絲對主播的崇拜和沉迷,打造社群經濟,進而開拓聲音社交。
移動互聯網時代,音頻產品的生產與消費邊界逐步消融,生產者與消費者向生產消費者轉化,即消費者既消費內容又生產內容。以往專業內容生產者、草根主播、消費者各自為陣、涇渭分明,將音頻產業鏈割裂開來。對專業生產者、專業用戶生產者、用戶生產者進行分層次培養,建立生產消費者養成體系,利用微信、QQ等社交媒體和社群活動,推動生產者與其粉絲群體進行準社會交往,有助于增強用戶黏性,使生產者與消費者實現深層互動的關系傳播。
(三)以大音頻理念為引導,重構音頻生態圈
縱觀廣播音頻與互聯網移動音頻的發展軌跡,目前來看,二者的融合整體上仍保持以自身優勢拓展為界。事實上,雙方均置身于在線音頻乃至視聽新媒體等更大、更激烈的媒介生態位。來自數字出版業的在線音樂、有聲閱讀等產品與之形成強勢競爭,QQ音樂等社交媒體在線音頻給音樂類音頻產品帶來巨大沖擊,在線教育音頻產品則對音頻產品的知識付費帶來巨大挑戰,其他如播客等自媒體個性化移動音頻產品均應納入以音頻產品為核心的音頻生態圈。以音頻產品為核心,通過跨界合作與差異化布局構建新音頻生態圈是廣播媒體與移動音頻互融的另一種理性思路。
2019年被稱作“5G元年”,大數據、物聯網、智能硬件以及基于傳感器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數字化內容生產,加上逼真的虛擬現實體驗,都為廣播與移動音頻的互融,帶來了想象的無限空間。
注釋
①楊軍:《從中國移動音頻內容生態演進看傳統廣播的突圍路徑》,《科技風》.2017年第12期。
②⑤凌昱婕、趙潔、歐陽宏生:《“廣播+”:互聯網時代的全媒體整合-2015年中國廣播媒介融合年度報告》,《中國廣播》,2016年第2期。
③《融合路上:廣播人的看法與辦法》,“電臺工廠”微信公眾號,2018年5月22日,https://mp.weixln.qq.com/s/osQbZj GCwh87SvvKOQIFGw.
④⑥黃學平:《短音頻——移動互聯廣播的下一個風口》,《中國廣播》,2018年第9期。
⑦崔珍:《“互聯網+”與廣播業的融合變革》,《青年記者》.2015年第11期。
(本文編輯: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