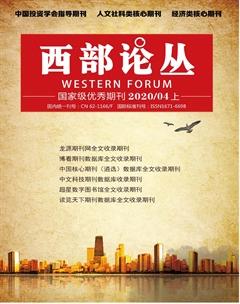淺談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保護(hù)制度
朱芮
摘 要:本文主要針對(duì)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保護(hù)制度進(jìn)行研究,了解我國(guó)私法中弱者保護(hù)制度目前存在的問題以及成因,并提出與之相應(yīng)的解決策略。通過結(jié)合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保護(hù)制度的積極意義,對(duì)弱者的司法權(quán)益建設(shè)問題進(jìn)行簡(jiǎn)略的探討與分析,由此促進(jìn)弱者保護(hù)制度的完善與健全,希望能夠?yàn)槿跽咚痉?quán)益建設(shè)工作的正常開展與發(fā)展提供助力與思考。
關(guān)鍵詞:弱者;國(guó)際私法;保護(hù)制度
一、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保護(hù)制度的概念
國(guó)際私法對(duì)弱者保護(hù)制度的界說是指在限制當(dāng)事人的意思自治中,運(yùn)用相應(yīng)的弱者保護(hù)概念,通過一些特定的法律法規(guī)進(jìn)而使實(shí)質(zhì)正義能夠進(jìn)行一定的規(guī)范。與人權(quán)保護(hù)概念相同,弱者保護(hù)同樣是國(guó)際私法中對(duì)法律選擇實(shí)質(zhì)性正義進(jìn)行探索的重要?jiǎng)恿ΑH藱?quán)保護(hù)會(huì)使國(guó)際私法在對(duì)諸如婚姻家庭等諸多方面進(jìn)行考量時(shí)對(duì)當(dāng)事人的意愿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例如,對(duì)撫養(yǎng)權(quán)等問題進(jìn)行考量時(shí),會(huì)對(duì)被撫養(yǎng)人的自身意愿進(jìn)行相應(yīng)的考量。而弱者保護(hù)則是基于合同當(dāng)事人之間所處的地位差距較大的情況下,對(duì)當(dāng)事人的主觀意愿予以相應(yīng)的限制。在一些具有特殊條件下的涉外合同履行中,對(duì)相應(yīng)的法律條款及具有糾紛的相應(yīng)協(xié)議予以法律層面的否認(rèn)[1]。通過立法的方式對(duì)某個(gè)特定的法律予以直接規(guī)定,或?qū)Ψㄔ核哂械膹?qiáng)制性規(guī)定與要求,再或者在處理時(shí)對(duì)弱勢(shì)方的權(quán)利予以進(jìn)一步的增強(qiáng)。
二、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中的弱者保護(hù)制度
(一)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保護(hù)制度的界說
我國(guó)于2010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涉外民事關(guān)系法律適用法》,進(jìn)而對(duì)弱者保護(hù)的適用方法進(jìn)行了一定的闡釋。從現(xiàn)實(shí)角度講,這是我國(guó)法律制度的操作性進(jìn)步。但《法律適用法》在具體的使用中與我國(guó)相應(yīng)的國(guó)際私法研究觀點(diǎn)同樣,因此對(duì)弱者保護(hù)的概念以及人權(quán)保護(hù)的概念存在一定的混淆問題。在《法律適用法》中所闡釋的弱者保護(hù)制度,整體立法的概念是基于在一定的涉外家庭關(guān)系當(dāng)中,并沒有對(duì)雇傭合同以及相應(yīng)的涉外消費(fèi)者合同予以充分的考量[2]。因此,整體適用范圍在于涉外家庭關(guān)系,即當(dāng)發(fā)生撫養(yǎng)及涉外監(jiān)護(hù)等諸多問題時(shí),才會(huì)存在相應(yīng)的弱者概念。《法律適用法》中還要求其對(duì)有利于保護(hù)弱者的法,或者有利于對(duì)被監(jiān)護(hù)人予以相應(yīng)保護(hù)的法進(jìn)行一定程度的適用。而通過這種概念對(duì)弱者保護(hù)予以適用,將導(dǎo)致弱者保護(hù)制度原有的正義底線予以打破,并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guó)的國(guó)際私法在立法過程中的正義性以及相應(yīng)的司法審判真實(shí)性。因此在具體的實(shí)踐過程中需要對(duì)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中的弱者含義與進(jìn)一步的劃分與確定,并對(duì)整體入地保護(hù)制度的適用范圍進(jìn)行進(jìn)一步探究。
(二)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概念分類
《法律適用法》將對(duì)弱者進(jìn)行保護(hù)的概念引入到了對(duì)自然人的人身安全及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你的保護(hù)過程當(dāng)中。從具體的時(shí)間角度分析我國(guó)的弱者保護(hù)制度,可以從以下四個(gè)角度進(jìn)行詮釋。第一,在合同中關(guān)系當(dāng)中的弱者是較為常見的一種應(yīng)用體現(xiàn)。在合同當(dāng)中的弱者往往由于強(qiáng)勢(shì)一方利用相應(yīng)的權(quán)利,使弱勢(shì)一方的訴求難以得到實(shí)現(xiàn),進(jìn)而對(duì)弱勢(shì)一方的意思自治進(jìn)行一定程度的約束,從而使其不能對(duì)合同中存在的爭(zhēng)議部分予以法律上的訴求。這時(shí),弱者保護(hù)制度將予以適用。第二,當(dāng)涉及侵權(quán)產(chǎn)品等諸多方面時(shí),如果其侵權(quán)產(chǎn)品涉及涉外產(chǎn)品質(zhì)量等諸多糾紛性問題,進(jìn)而使消費(fèi)者的權(quán)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則此時(shí)便認(rèn)定,消費(fèi)者為弱者一方。在具體的保護(hù)過程中,由于侵權(quán)人的過錯(cuò)很難以具體的形式加以證明,因此將通常責(zé)任制用嚴(yán)格責(zé)任制的方法予以進(jìn)一步代替,將使得消費(fèi)者與侵權(quán)者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得以進(jìn)一步的明確。第三,在婚姻家庭中的弱者保護(hù)制度是我國(guó)的保護(hù)制度履行中最為常見的。當(dāng)婚姻關(guān)系涉及涉外關(guān)系及相應(yīng)的涉外撫養(yǎng)權(quán)時(shí),受撫養(yǎng)一方則很容易成為法律概念中的弱者。對(duì)于上述領(lǐng)域當(dāng)中的弱者,其主要的形成因素可以分為社會(huì)與自然兩大部分。就社會(huì)層面而言,其主要的表現(xiàn)為強(qiáng)勢(shì)與弱勢(shì)方所掌握的資源程度不同,信息接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對(duì)等因素,并且由于一方所具有的相應(yīng)權(quán)利,將直接或間接導(dǎo)致另一方在對(duì)自身權(quán)益進(jìn)行訴求時(shí)受到極大程度的阻礙[3]。就自然程度而言,弱勢(shì)一方可能具有先天性身體缺陷,或由于自身生存條件及諸多方面存在的匱乏因素,進(jìn)而使其從客觀角度無法對(duì)自身的權(quán)益予以進(jìn)一步的訴求。
(三)法律特征分析
首先,弱者的身份在我國(guó)法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法定性。這點(diǎn)國(guó)際與國(guó)內(nèi)的國(guó)際私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化特征。法律上的弱者與道德層面上所界定的弱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性,道德與社會(huì)學(xué)的弱者所強(qiáng)調(diào)的往往是具有劣勢(shì)地位一方,而法律層面則強(qiáng)調(diào)權(quán)力受到限制的一方。第二,國(guó)際私法中的弱者身份存在一定的相對(duì)性區(qū)別,強(qiáng)者和弱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轉(zhuǎn)化。不同利害關(guān)系中的同一主體,在不同的法律體系當(dāng)中,其具體實(shí)現(xiàn)權(quán)利的難易程度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同特征。舉例說明,同樣在合同糾紛中,如果涉及消費(fèi)合同,則銷售者很有可能成為強(qiáng)者一方,而消費(fèi)者將成為弱勢(shì)一方。但是,銷售者在相應(yīng)的勞動(dòng)合作合同當(dāng)中,便有可能轉(zhuǎn)變?yōu)槿鮿?shì)一方。因此在我國(guó)的國(guó)際私法當(dāng)中,對(duì)弱者的界定由于其身份的不明確性,存在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現(xiàn)實(shí)性特征。第三,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保護(hù)當(dāng)中的弱者存在著法律的特殊保護(hù)。我國(guó)的法律其自身的立法原則并不對(duì)社會(huì)中的特權(quán)一方予以承認(rèn),而弱者概念的進(jìn)一步提出,便是為了使法律更加具有公平性、正義性。在弱者面對(duì)實(shí)際上的特權(quán)群體是通過弱者保護(hù)制度可以對(duì)自身的合法權(quán)益予以法律偏向性的保護(hù)[4]。
三、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保護(hù)制度存在的不足
當(dāng)下弱者在生涯中存在的主要司法問題成因,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diǎn):
(一)弱者自身的司法建設(shè)能力較弱
弱者面臨的各個(gè)方面壓力較大,從而會(huì)產(chǎn)生焦慮感。現(xiàn)實(shí)并沒有弱者想象中美好,因此當(dāng)發(fā)現(xiàn)理想與現(xiàn)實(shí)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時(shí),會(huì)產(chǎn)生失落感、挫敗感。自我認(rèn)知是個(gè)體在社會(huì)發(fā)展和生存的過程中,對(duì)于自身的生理和司法的自我評(píng)定、自我認(rèn)知直接決定了個(gè)體與周圍環(huán)境的和諧程度,部分弱者在成長(zhǎng)的過程中,缺乏自我認(rèn)知意識(shí),無法準(zhǔn)確的實(shí)現(xiàn)自我定位和自我評(píng)價(jià)。
(二)法律和制度規(guī)范不完善
在弱者保護(hù)制度的監(jiān)理的過程中,法官需要充分的進(jìn)行義務(wù)的行使以及心證的公開化,由于法律和制度規(guī)范不完善,導(dǎo)致失權(quán)問題出現(xiàn)。當(dāng)事人屢次進(jìn)行新的人證物證的提出,對(duì)于法官進(jìn)行案件的整體審理造成了極大的干擾性, 當(dāng)事人也無法預(yù)判裁判結(jié)果所依據(jù)的證據(jù)方法到底在哪里,突襲性裁判現(xiàn)象也就必然會(huì)頻頻發(fā)生。同時(shí),弱者保護(hù)依然遵循法庭調(diào)查與法庭辯論相分離的審理模式,致使弱者保護(hù)時(shí)間被無端拉長(zhǎng),且質(zhì)效低下。為了保證法治建設(shè)工作可以高效的開展,相關(guān)的法律法規(guī)必須要不斷的完善和健全。對(duì)于現(xiàn)階段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弱者保護(hù)制度運(yùn)行工作而言,雖然加大了重視程度,但是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的制定有待完善,對(duì)于弱者保護(hù)環(huán)境的變化趨勢(shì)不能很好的適應(yīng),導(dǎo)致法治建設(shè)工作缺乏依據(jù)[5]。
(三)弱者保護(hù)制度運(yùn)行的評(píng)價(jià)體系不規(guī)范
目前,我國(guó)弱者保護(hù)未圍繞爭(zhēng)點(diǎn)審理以及審理散漫化問題突出[6]。國(guó)際私法中的弱者保護(hù)制度運(yùn)行評(píng)級(jí)體系不規(guī)范,是現(xiàn)階段法治建設(shè)問題中的關(guān)鍵問題。我國(guó)不同的地區(qū)對(duì)于國(guó)際私法中的弱者保護(hù)的確立沒有一個(gè)明確的劃分,對(duì)于評(píng)價(jià)的內(nèi)容以及方法等等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因此不同地區(qū)的評(píng)價(jià)體系不統(tǒng)一,影響了評(píng)價(jià)的正常開展。國(guó)際私法中的弱者保護(hù)制度運(yùn)行評(píng)價(jià)體系是法治建設(shè)工作真實(shí)性的有效保證,如果評(píng)價(jià)體系沒有形成統(tǒng)一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就無法將真實(shí)的情況反映出來,無法充分發(fā)揮法律責(zé)任管理的價(jià)值。
四、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弱者保護(hù)立法的相應(yīng)完善措施
在國(guó)際私法保護(hù)制度的概念當(dāng)中對(duì)弱者的概念予以進(jìn)一步的確定,并且對(duì)相應(yīng)的保護(hù)方法進(jìn)行有效的構(gòu)成是整體制度的核心內(nèi)容。對(duì)我國(guó)的國(guó)際私法弱者保護(hù)制度概念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完善,可以從以下兩個(gè)方面入手,對(duì)相應(yīng)的保護(hù)方法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探究。
(一)對(duì)整體弱者的保護(hù)范疇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界定
1.對(duì)國(guó)際私法中關(guān)于弱者的定義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解讀
在具體的制度建立過程中需要對(duì)既有的涉外家庭關(guān)系中所含有的弱者思維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打破。并且將整體的弱者概念運(yùn)用到處理特定的涉外民事法律問題之中,在國(guó)際私法概念下的弱者概念是指從法律的適用方法以及對(duì)相應(yīng)糾紛的解決方法角度進(jìn)行弱者的概念考慮,而并不是使相應(yīng)的具體權(quán)利弱者[7]。對(duì)這一概念進(jìn)行明確的劃分,將使我國(guó)的國(guó)際私法弱者保護(hù)制度在改進(jìn)過程中能夠得以明確化的建立。因此,在對(duì)我國(guó)的國(guó)際私法弱者保護(hù)制度進(jìn)行鑒定時(shí),應(yīng)將整體的范圍建立在對(duì)勞動(dòng)雇傭合同以及消費(fèi)者合同等諸多方面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衡量。并且對(duì)涉外家庭中所采取的弱者概念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弱化。由于我國(guó)的弱者保護(hù)制度從其立法時(shí)間講,其生效時(shí)間相對(duì)較短,并且在短時(shí)間內(nèi)難以對(duì)相應(yīng)的法條內(nèi)容進(jìn)行系統(tǒng)性的修整。因此可以在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保護(hù)概念的使用過程中引入司法解釋的方式,對(duì)相應(yīng)的弱者概念予以進(jìn)一步的說明。對(duì)法條中所出現(xiàn)的弱者概念以及所適用的對(duì)象予以相應(yīng)的闡釋,避免在適用過程中出現(xiàn)一定的歧義性誤解。
2.明確對(duì)國(guó)際私法中的弱者保護(hù)概念中的弱者進(jìn)行保護(hù)的方法
在具體的適用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通過相應(yīng)的弱者保護(hù)法認(rèn)定強(qiáng)者主導(dǎo)的法律合同及相應(yīng)條款,不具備相應(yīng)的法律效力,或者通過強(qiáng)制的方法對(duì)合同中具有明顯爭(zhēng)議的部分予以強(qiáng)制性的排除。其具體的使用方法應(yīng)該是對(duì)強(qiáng)勢(shì)方的法律權(quán)利與相應(yīng)的限定,而不是為弱勢(shì)方提供所謂的“最好的法”。在履行過程中,需要注意對(duì)合同中相應(yīng)的法律條款予以無效化界定時(shí),并不是指對(duì)整體合同中的爭(zhēng)議部分進(jìn)行完全無效化處理,而是應(yīng)當(dāng)對(duì)存在爭(zhēng)議的內(nèi)容與弱者所居當(dāng)?shù)厮m用的法律進(jìn)行充分的考量[8]。
(二)對(duì)我國(guó)國(guó)際私法弱者保護(hù)的適用范圍進(jìn)行細(xì)化完善
1.對(duì)涉外消費(fèi)者合同進(jìn)行相應(yīng)的弱者保護(hù)制度適用
如果協(xié)議中所涉及的相應(yīng)法律法規(guī),從保護(hù)消費(fèi)者權(quán)利的角度進(jìn)行分析,與消費(fèi)者經(jīng)常居住的地區(qū)所適用的法條相符,或要求高于弱者居住地所適用的法條,則應(yīng)判定其協(xié)議內(nèi)容有效。如果相應(yīng)的內(nèi)容與消費(fèi)者經(jīng)常居住地區(qū)所適用的法律不符,或者其法律較比消費(fèi)者居住地區(qū)所存在的法條效率相對(duì)較弱,則應(yīng)按照消費(fèi)者所城居住地區(qū)使用的法律法條對(duì)協(xié)議內(nèi)容進(jìn)行相應(yīng)的考量。舉例說明,在法律適用法中可以對(duì)相應(yīng)的第42條法條進(jìn)行具體的修改,其修改內(nèi)容可以改為:在雙方所簽訂的消費(fèi)者合同當(dāng)中,就當(dāng)事人簽訂協(xié)議所選擇的法律與我國(guó)所規(guī)定的相應(yīng)法律存在一定程度的沖突性,進(jìn)而不予適用,并適用于消費(fèi)者長(zhǎng)居地所具有的法律法規(guī)。若當(dāng)事人在簽署合同中并沒有對(duì)法律進(jìn)行選擇,應(yīng)當(dāng)提供消費(fèi)者在進(jìn)行消費(fèi)時(shí),其商品與服務(wù)提供地做適應(yīng)的法律,若不能提供相應(yīng)的法律條款則應(yīng)按照消費(fèi)者常居地所適應(yīng)的法律法規(guī)予以履行。通過這樣的方式對(duì)法律條款進(jìn)行處理,其一,能夠確保整體當(dāng)事人雙方所簽訂的相應(yīng)協(xié)議在法律適用的角度上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消費(fèi)者一方,進(jìn)而確保其法律法規(guī)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正性。其二,對(duì)法條進(jìn)行如此詮釋將不對(duì)消費(fèi)者在進(jìn)行法律選擇條款使得權(quán)力予以否定,進(jìn)而有助于對(duì)外國(guó)法進(jìn)行相應(yīng)的查明。在上述兩點(diǎn),對(duì)后者進(jìn)行相應(yīng)考量時(shí)期,協(xié)議當(dāng)事人應(yīng)當(dāng)負(fù)責(zé)對(duì)相應(yīng)的外國(guó)法律進(jìn)一步的提供與查明。而法官對(duì)當(dāng)?shù)氐姆赏鸵欢ǖ氖煜ば裕⑶一诖饲疤嵯拢瑢⒑苋菀讓?duì)外國(guó)法與本地法之間所存在的區(qū)別及法律適用程度予以進(jìn)一步的考量。進(jìn)而能夠方便在法官對(duì)相擁糾紛進(jìn)行具體判定時(shí),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正性。并且通過這種方法的設(shè)定也將有助于法律適用,建立更加完善的正義導(dǎo)向[9]。
2.對(duì)涉外勞動(dòng)合同進(jìn)行相應(yīng)的國(guó)際私法弱者保護(hù)制度適用
應(yīng)當(dāng)對(duì)當(dāng)事人選擇法律的權(quán)益予以進(jìn)一步的考量,但其具體的考量范圍應(yīng)當(dāng)建立在遵循我國(guó)強(qiáng)制規(guī)定的基礎(chǔ)之下。因此,在對(duì)相應(yīng)的涉外勞動(dòng)合同進(jìn)行弱者保護(hù)制度建立時(shí),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進(jìn)行詮釋,即相應(yīng)的涉外勞動(dòng)合同允許對(duì)當(dāng)事人協(xié)議選擇法律予以相應(yīng)的適用,但其前提應(yīng)不違反我國(guó)的相應(yīng)規(guī)定。若當(dāng)事人所簽訂的合同中并沒有對(duì)法律進(jìn)行選擇,應(yīng)當(dāng)適用受雇傭者工作地所適用的法律。如果對(duì)受雇傭者工作地不能進(jìn)一步得以明確,則應(yīng)當(dāng)適用于用人單位經(jīng)歷所適用的法律。對(duì)于勞務(wù)派遣相關(guān)問題,可以考慮適用我派遣中的派出地所適用的法律。就目前我國(guó)所面對(duì)的涉外勞動(dòng)合同的實(shí)際情況進(jìn)行分析,大部分的勞動(dòng)合同中,在對(duì)勞動(dòng)者進(jìn)行保護(hù)的方面予以界定,使其相應(yīng)標(biāo)準(zhǔn)往往會(huì)高于我國(guó)對(duì)勞動(dòng)保護(hù)所設(shè)置的標(biāo)準(zhǔn)。如果在進(jìn)行立法時(shí),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對(duì)勞動(dòng)者的權(quán)益進(jìn)行更好的保護(hù),則應(yīng)當(dāng)充分肯定這種協(xié)議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而不是在具體的界定過程中,對(duì)優(yōu)質(zhì)的法律法條予以全盤否定。如果受雇傭者所處地點(diǎn)的勞動(dòng)保護(hù)法律法規(guī)與我國(guó)的勞動(dòng)者保護(hù)法律法規(guī)相比存在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則應(yīng)強(qiáng)制性的對(duì)其協(xié)議的實(shí)際生效力度予以限制,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保護(hù)制度所應(yīng)有的正義性。
3.對(duì)不涉及弱者保護(hù)制度中的涉外家庭關(guān)系進(jìn)行處理
由于從法律概念而言,無論是父母還是子女,其均不屬于國(guó)際私法弱的保護(hù)制度體制下的弱者概念。因此就其根本而言,不存在是否適用于相應(yīng)法律的問題。我國(guó)的國(guó)際司法保護(hù)制度當(dāng)中,對(duì)涉外家庭關(guān)系進(jìn)行詮釋時(shí)可以從以下角度進(jìn)行闡述:父母雙方與子女的人身與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對(duì)其共同長(zhǎng)居的地區(qū)法律予以適用。若在具體的關(guān)系當(dāng)中不存在共同長(zhǎng)居地點(diǎn)時(shí),若其中一方的常居地點(diǎn)為我國(guó),則應(yīng)適用于我國(guó)的法律法規(guī)。若沒有一方的常居地為我國(guó)境內(nèi),則應(yīng)對(duì)其協(xié)議中,與存在爭(zhēng)議聯(lián)系最為密切的地點(diǎn)為基準(zhǔn),進(jìn)行法律的適用考慮。就目前我國(guó)所涉及的涉外家庭關(guān)系而言,任何一方均不在國(guó)內(nèi)的情況極為少見。當(dāng)這種情況發(fā)生時(shí),往往是由于存在某些固定的資產(chǎn)在我國(guó)境內(nèi)。因此對(duì)上述問題進(jìn)行界定時(shí)應(yīng)予以“聯(lián)系最為密切”這一原則進(jìn)行底線性闡釋[10]。將涉外家庭關(guān)系內(nèi)容進(jìn)行如上修改,將滿足相應(yīng)條文的周延,對(duì)于涉外撫養(yǎng)權(quán)以及相應(yīng)的監(jiān)護(hù)關(guān)系予以具體的法律適用考量時(shí),其考量的關(guān)鍵點(diǎn)應(yīng)著眼于對(duì)被撫養(yǎng)者或被監(jiān)護(hù)者所應(yīng)得到的監(jiān)護(hù)及撫養(yǎng)程度予以進(jìn)一步的考量,而不是對(duì)相應(yīng)的物質(zhì)內(nèi)容進(jìn)行利益最大化的處理。
五、結(jié)語
綜上所述,我國(guó)的國(guó)際私法弱者保護(hù)制度的完善應(yīng)建立在對(duì)國(guó)際私法中弱者定義進(jìn)行進(jìn)一步明確的基礎(chǔ)上,進(jìn)而通過相應(yīng)的制度完善性,避免強(qiáng)勢(shì)一方通過法律的適用選擇,對(duì)弱勢(shì)一方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而其立法目的并不在于強(qiáng)制性要求對(duì)弱者的利益予以最大化。對(duì)保護(hù)弱者的法律適用予以進(jìn)一步選擇時(shí),應(yīng)當(dāng)按照合同中所限制的法律選擇范圍為主要參考,并適當(dāng)?shù)膶?duì)弱者單方面選擇法律的權(quán)利予以相應(yīng)的考量,在整體法律的選擇中,其選擇的實(shí)體法與法院所存在的強(qiáng)制規(guī)定不應(yīng)發(fā)生沖突。
參考文獻(xiàn)
[1] 楊慧.淺談弱者思想政治工作的現(xiàn)狀及對(duì)策[J].中外交流,2019,26(37):258-259.
[2] 闞妮妮,王猛,駱曉娟.司法保護(hù)強(qiáng)國(guó)夢(mèng)視域下弱者司法輔導(dǎo)工作探析[J].司法保護(hù)時(shí)空,2018(23):354-355.
[3] 鐘建良.試論弱者的思想特點(diǎn)與管理方法[J].司法保護(hù)世界:學(xué)術(shù)版,2018,000(001):6-7.
[4] 王文韜.試論弱者的思想特點(diǎn)的全面探究[J].法治交流,2017,003(002).
[5] 鄒詩鵬.“實(shí)踐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的相通性——基于《關(guān)于弱者保護(hù)理念的提綱》與《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的探討[J].司法主義與現(xiàn)實(shí),2015(04):22-32.
[6] 韓立新.《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之《弱者保護(hù)理念》章編譯上的根本問題——寫在新MEGA I/5《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卷正式出版之前[J].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31(06):135.
[7] 袁圓,柴芳墨.論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與民事訴訟程序的新發(fā)展[J].人民論壇·學(xué)術(shù)前沿,2019(09):104-105.
[8] 丁朋超.我國(guó)弱者保護(hù)制度的反思與發(fā)展進(jìn)路[J].政法學(xué)刊,2019,36(04):79.
[9] 張悅.“互聯(lián)網(wǎng)+司法”之網(wǎng)絡(luò)直播弱者保護(hù)問題實(shí)證研究[J].遼寧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6,44(06):121-123.
[10] 張馨月.淺析我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法院制度[J].法制博覽,2018(04):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