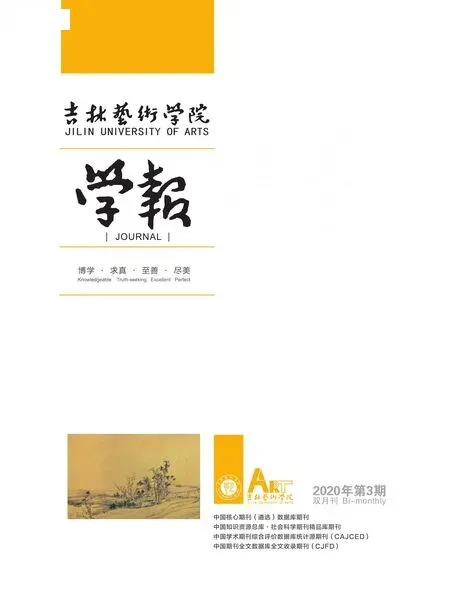承繼與變異
——客家嗩吶“七盞燈”儀式音聲的考察與研究
羅鋼芹
(嘉應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廣東 梅州,514015)
一、“七盞燈”形成的人文背景
在歷史長河中,無論是我國南方還是北方,吹打樂都在各種民俗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客家族群中,客家人習重禮儀,無論是婚慶、壽慶,還是祭祀、社火都少不了吹打樂班的煽情助興,吹打樂已成為客家人精神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時至今日,絕大多數的客家人都沒有習慣嗩吶(sorna)這個稱謂。在當地,無論在文字記載還是日常生活中,客家人都習慣和中原漢人一樣將嗩吶稱之為“笛”,而吹打樂班又稱之為“笛班”,樂手稱為“吹笛佬”。在客家社會千百年的嗩吶吹打流傳過程中,客家人以其智慧和才華將中原傳統文化與客家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創造出一種獨具客家特色的嗩吶吹打形式——嗩吶“七盞燈”。
客家嗩吶七盞燈的形成與客家地區特定的族群屬性、人文信仰、地域特征和時代特征密切相關,它的形成也反映了客家社會基本的人文信仰和社會需求。
1. 人文信仰
客家民間自古就有尚巫崇神的傳統,民間信仰活動在客家族群里是一種既古老又普遍的文化現象。客家人是南遷的中原漢人,在數次的南遷過程中,客家人將中原文化帶到南方一帶,如今的客家地區正是南北文化交匯融合之地。因此,客家人的神明崇拜也由此變得非常復雜,既崇拜全國性的神明,也崇拜地方性的神明;既崇拜道教神明,也崇拜佛教、巫教神明等。客家人每逢冠婚喪祭,都要舉行慶典活動來敬神祈福,這些信仰活動為七盞燈民俗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文信仰基礎。
2. 禮樂思想
禮樂制度是我國古代重要的社會制度之一。“禮”主要是對社會中不同人的身份和地位進行劃分和規范,“樂”主要是根據禮的等級不同和對象不同,運用與之對應的音樂來和諧社會關系。據《史記》記載:“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生,政之行也,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1]可以看出,在古人的喪、婚、冠等禮俗活動中,都有“樂”進行參與,禮樂思想也成為封建統治階級治國安邦的重要思想。
中原社會的禮樂思想在客家人心目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直到今日,在客家的各類民俗禮儀活動中,民間音樂的參與仍然非常廣泛,客家嗩吶七盞燈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客家當地流傳著一句順口溜:“七寸吹打拿在手,五音六律里邊有,冠婚喪祭沒有我,冇聲冇息蠻難過”(冇,讀音mao,即客家話“沒有”)。雖然是一句不經意的順口溜,但充分說明了嗩吶吹打樂在當地民俗禮儀活動中的重要地位。
3. 名稱寓意
“七盞燈”名稱中的“七”和“燈”字在客家民間有著獨特的內涵。客家人常常認為“七”字代表著“吉利”,客家民間有“七上八下”“七生八死”的說法,喪事中又有“做七”的習俗等。[2]如“七盞燈鬧壽堂”時,藝人喊到:“一盞燈到壽堂,椿萱并茂壽年長;二盞燈到壽堂,八一誕辰樂洋洋;三盞燈到中堂,壽星福氣的確強;四盞燈到中堂,福星高照壽滿堂;五盞燈壽年延,椿萱壽似彭子年;六盞燈頌壽仙,福如東海樂無邊;七盞燈亮堂堂,壽比南山幸福長。”客家人對“七”的崇拜,歸根結底均源自于“七”在客家社會蘊含的豐富文化寓意。
“燈”字在客家社會常常代表著“丁”和“火”,即認為“丁財兩旺”。如結婚慶典時,藝人一走進主家大門便喊到:“新郎新娘,喜結鴛鴦,百年好合,地久天長。”主家接喊:“口為圣旨。”當載燈藝人慢步走向正廳時,隨行的司儀喊到:“要燈不要燈?”新郎新娘齊聲喊到:“要燈。”(即“要丁”)接著,載燈藝人走到正廳中央處停下,司儀在卸燈前喊四句吉利話:“七盞油燈亮閃閃,照得廳堂金輝煌,今年喜迎靚新娘,明年生得狀元郎。”嗩吶七盞燈的名稱迎合了客家人在數字和文字中的特殊寓意,而這種特殊寓意也促成了嗩吶七盞燈在客家地區的廣泛流傳。
二、“七盞燈”儀式的音聲特征
1. 樂器與道具
七盞燈樂班由7人組成,即嗩吶2人,鑼、鼓各1人,小鈸1人,護燈2人。樂班中使用的嗩吶由樂手手工制作而成,高音嗩吶音桿長約30公分,低音嗩吶音桿長約37公分,用黃檀硬木制作,銅喇直徑20公分。鑼、鼓、小鈸與常規民間樂隊使用的型制一致。
道具主要由“燈”和“毛巾”組成。據七盞燈傳承人彭熾宏介紹,過去使用的都是“馬燈”,而現在使用“碗燈”,“碗燈”就是在碗口邊緣貼上一圈齒紋狀的紅紙條,碗內立一根紅蠟燭制作而成。道具中的“毛巾”主要用于遮住載燈藝人的臉頰,防止燈火燙傷。從七盞燈儀式中使用的“燈”來看,“馬燈”明顯是北方文化的產物,體現了七盞燈對北方文化的良好傳承。而現在使用的“碗燈”,則是客家人結合當地文化不斷改良的結果。
2. 表演特征
從表演上看,嗩吶七盞燈吹打樂有“吹”“打”“念”“舞”四個表演特征。其中“吹”即指吹奏嗩吶;“打”指打擊樂的伴奏;“念”指儀式人員念誦的祝詞;“舞”指嗩吶藝人“走舞”的表演形式,這也是最為精彩的環節。在嗩吶七盞燈表演的過程中,通常由低音嗩吶手來進行載燈、送燈表演,司儀會將七盞油燈分別擺放在載燈藝人的頭、肩膀、肘部、手腕上,此時,載燈藝人吹奏嗩吶,邊舞邊行地完成整個送燈儀式,表演過程驚險刺激,需要載燈藝人掌握高超的載燈表演技巧和嫻熟的嗩吶吹奏技術。從整個嗩吶七盞燈的表演來看,中原雜耍的表演成分和粗狂豪放的曲風特點尤為明顯。因此,整個嗩吶七盞燈表演具有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特征。
3. 程式性與新生性特征
嗩吶七盞燈的表演非常講究程式性,這主要體現在整個民俗表演的每個環節上。雖然近些年受文化環境的影響,嗩吶七盞燈的表演難度在逐漸降低,但不管是哪支七盞燈表演隊伍,在表演過程中,都分為“祝詞”“上燈”“送燈”“接燈”這四個環節。并且每一個環節的位置是固定不變的,表演時也不會出現省略某個環節的情況。
美國民俗音樂學家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認為:“任何表演都意味著它從來都不是第一次,表演的本質在于話語的去語境化(decontextualistation)和再語境化(recontextualistation)當中,而后者尤為重要,表演總是呈現出新生性的維度(emergent dimension)。”[3]筆者認為,嗩吶七盞燈的每一次表演,都受到表演者的主觀因素影響,即使是表演相同的內容,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表演隊伍,甚至是相同的表演隊伍,都會有表演風格上的一些差異。因此,嗩吶七盞燈的每一次表演都呈現出新生性的維度。
4. 曲牌特征
根據表演內容的不同,嗩吶七盞燈吹打分為“喜調”和“悲調”兩種曲牌。在儀式表演過程中,各曲牌講究“專曲專用”,即根據民俗活動內容的不同而選用相對應的曲牌。如在各類喜事活動中,嗩吶七盞燈常使用乙字調、六字調、尺調子等喜調類曲牌;在白事活動中,嗩吶七盞燈常使用悲調、雙字調、反合調等悲調類曲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載燈藝人還會根據曲牌類型來改變表演方式。如演奏喜調類曲牌時,載燈藝人面帶微笑,精神抖擻,此時的嗩吶口微微朝上,演奏速度較快,藝人的表演動作和步伐也隨之加快。演奏悲調類曲牌時,載燈藝人面部表情凝重,此時嗩吶口明顯朝下,藝人的演奏速度和表演動作、步伐均放慢。
5. 音調特征
在旋律音調上,嗩吶七盞燈的大部分曲牌均采用羽調式和商調式為主。以羽調式婚慶曲牌為例(見譜例1),一方面旋律以La-Re為骨干音,主題音調以商音下行四度跳進到羽音(主音)作為旋律開始,特別在旋律進行中,商音的位置被多次強化,這些因素使曲調流露出一股中原曲風豪放粗狂的音樂特點。另一方面,在旋律音調中又穿插了一些婉轉的小波浪旋律線條,這使得曲調又流露出婉轉、細膩的客家小調風格。因此,嗩吶七盞燈的音調風格具有承繼性和變異性的雙重文化特征。
6. 結構特征
七盞燈吹打樂在儀式中往往以單一曲牌不斷循環來完成表演。從曲牌的結構來看,七盞燈吹打樂使用的曲牌大多為一段體,但嗩吶藝人擅長將單一的音樂主題進行重復和變奏來形成較大的音樂規模。另外,在一些大型的禮儀活動中,嗩吶藝人又會根據場合需要,將同類曲牌進行組合演奏,如在“七盞燈鬧喜堂”儀式中,藝人常以《鬧喜堂》+《四季春》曲牌來完成儀式,營造喜氣洋洋的婚慶場景。
7. 演奏特征
兩支嗩吶在音色上,一明一暗;在演奏上,偶爾齊奏,大多是繁簡結合,主題旋律在兩支嗩吶間互相承接(見譜例2);在演奏音量上,強弱交替、承接,互相陪襯,仿佛是兩支嗩吶間的對話,一問一答。旋律長音處常有“下滑音”奏法,這與客家人慣用的感嘆語調十分相似,表現出藝人對藝術的精湛處理。打擊樂的節拍固定,音量較弱,偶爾嗩吶聲停,單獨出現一段打擊樂演奏,讓人感覺突然“安靜”下來,產生遐想。
⑤從排沙角度,長江流域的雅礱江、金沙江、青衣江、嘉陵江、涪江、渠江、漢江的丹江口以上屬于多沙區,而金沙江和雅礱江的源頭、岷江、烏江、洞庭湖水系、鄱陽湖水系為少沙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少沙區水庫蓄水時間可以適當提前,而多沙區水庫蓄水應該滯后。
七盞燈嗩吶中的旋律承接、交替、繁簡復合等手法,明顯承繼了北方嗩吶的演奏特點,而旋律中頻繁的“下滑音”又是對客家話語調的模仿。因此,七盞燈的演奏是一種南北文化的融合,既承繼了北方嗩吶的多聲復合技法,又融入了客家語調的模仿成分。
三、“七盞燈”吹打樂的現狀與保護思路
1. 現狀分析
“當一種文化形態與傳統觀念相背離,傳統的東西要么通過某種特殊的方式得以流傳,要么就被新的文化所替代。”[4]由于受到市場經濟和外來文化的影響,客家嗩吶七盞燈在生存和傳承上正經受著嚴峻的考驗。
(1)生存環境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客家地區的經濟高速發展,大量中青年農民外出打工、學習、經商,隨著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紅白喜事從簡的思想在他們心中與日俱增。大部分年輕人已經不愿意大張旗鼓的操辦婚禮,有些甚至不舉行任何儀式。在喪事方面,以前大多要做三天兩夜的道場,而現在幾乎只做一天,有些甚至不做。除此之外,隨著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民間其他的慶典活動也在大量減少,如壽慶、滿月酒、喬遷、廟會等。生存環境的變化使得七盞燈藝人們的收入大大減少,據老藝人彭熾宏介紹,現在他的樂班一年都接不到10場表演。
(2)銅管樂隊的沖擊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銅管樂在客家地區大量興起,占據了城鄉禮儀的半壁江山。特別是對于一些富裕的家庭而言,能請一支規模龐大的銅管樂隊往往能給他們心里帶來一種榮譽感、自豪感。如今的梅縣一帶就經常活躍著十多個銅管樂隊,五華縣也有五、六個銅管樂隊。這些銅管樂隊常常取代民間吹打樂班,或與民間吹打樂班共同參與到民俗禮儀活動中。
(3)同行的“優勝劣汰”
由于交通工具和通訊工具的普及,藝人們的活動地域大大拓寬,藝人間的優勝劣汰也更為激烈。據藝人彭熾宏介紹,以前五華縣有六支七盞燈表演隊伍,但現在能完整地載七盞燈表演的只有他一家。剩下幾家由于表演少、疏于練習,現在只能載五盞或三盞燈表演,而且表演時還經常掉燈,已經很少能接到生意了。
2. 保護思路
(1)重建曲牌文本
據傳承人彭熾宏介紹,在20世紀60年代的“破四舊”活動中,嗩吶七盞燈的曲牌資料大多被燒毀,現在的表演曲牌大多靠載燈藝人的口傳心授進行傳承。從曲牌傳承方式來看,“口傳心授”傳承會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干擾,影響曲牌傳承的準確性。因此,對于曲牌的保護,當前應加快對七盞燈表演曲牌進行錄音、錄像和組織專業人員進行文本重建。
(2)加大傳承人的保護
文化學者馮驥才指出:“傳承人是民間文化最瀕危的現狀之一。”[5]可見,民間文化的保護,關鍵是要保護好傳承人。就目前的現狀來看,一方面政府要制定相關政策,扶持這項民間技藝,授予傳承人榮譽,定期給予傳承人一定的資金補助,肯定七盞燈吹打藝術的社會價值;另一方面,要加大客家傳統文化的宣傳,鼓勵年青人學習客家民間藝術,選拔一些優秀學員來傳承嗩吶七盞燈藝術,并給予一定的獎勵。
(3)重視客家民俗文化
七盞燈吹打和客家民俗文化之間,是“魚”和“水”的關系,離開了客家民俗文化市場,七盞燈便無生存之地。我們應重視客家民俗文化市場的保護,引導客家民眾認識客家傳統民俗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同時,將客家民俗文化與客家族群的認同感相互聯系,多方位、多舉措地提升客家民俗文化的地位,為民間藝術的施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四、“七盞燈”的文化人類學詮釋
1. 民族性的意義
民族性是一個民族特有的標志和特性。西學東漸一百多年來,西方文化在我國不斷滲透,并取得話語權,特別在音樂界的表現更是如此,西洋樂占據我國半壁江山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客家的七盞燈民俗表演,保留了我國民族文化中最基本的符號和特征。這些民族性特征和符號,一是表現在七盞燈民俗表演的本身,二是表現在客家人的各類禮俗活動中,三是則表現在禮俗活動背后的親和力和凝聚力上。七盞燈民俗表演對我們認識、傳承客家禮俗文化,認識民族性和社會心理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2. 族群凝聚力的體現
七盞燈吹打樂在客家民間往往成為凝聚族群情感的重要紐帶。在家族的祭祀、婚慶、壽禮、喪葬等禮俗活動中,七盞燈表演將宗親和姻親聯結在一起,家族凝聚力在認親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在民間集體性的禮俗活動中,如廟會和節日慶典活動中,七盞燈表演又將多個家族聯系在一起,集體的祭祀和慶祝促成了族群的團結,凝聚力也在族群的團結中逐漸形成。
家族、族群凝聚力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礎,它們在長年累月的民間禮俗活動中逐漸形成,民俗音樂在這種凝聚力的產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縱觀客家社會的禮俗活動,音樂和禮俗往往聯結在一起,共生共演、不可分割。七盞燈民俗表演在客家禮俗活動中,不僅是活動的背景和形式,有時更成為禮俗活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
五、結語
客家嗩吶七盞燈是一種南北文化結合的產物,既保留了北方嗩吶粗狂豪放的曲風特點和驚險刺激的雜耍場面,又融入了客家小調委婉細膩的音調成分,具有承繼性和變異性的文化特征。隨著文化變遷的加劇,嗩吶七盞燈的生存正面臨嚴峻的考驗。但我們相信,作為一種民族性的特征與符號,作為客家社會族群情感凝聚的重要紐帶,嗩吶七盞燈一定能在客家社會的民俗活動中繼續擔當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