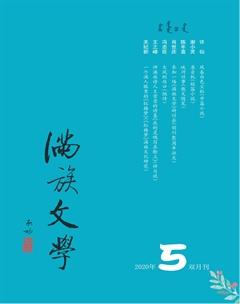一個滿人眼里的《紅樓夢》
關紀新
先回憶一件對我影響很大的往事。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有幸趨前拜望一位老人,共和國前期的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先生。他提出一個問題:滿族為什么落敗?老人自問自答:因為他們太把自己看成是中國人,沒有自外于這個國家,追求光明和進步,沒有像蒙古人那樣精心保留根據(jù)地,結(jié)果是飛蛾撲火……一場悲劇。李老的話對我猶如醍醐灌頂。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政策的首要制定者,對滿族這個民族歷史有較深研究。這席話遠非官樣文章,卻道出了一般人所難道出的重要哲思,促使我展開多年不渝尋覓本民族歷史殷鑒之旅。
滿洲是個有過歷史大作為的悲劇民族。當初,這個民族人口少、體量小、發(fā)展滯后,卻敢想勇為,把天捅出個大窟窿,結(jié)果沒能躲過社會局限性的懲罰。
我是滿族文化與文學的學術(shù)從業(yè)人。我讀《紅樓夢》,是從滿洲民族歷史命運和古今文化思考入手的。拙著《滿族書面文學流變》闡釋了我對滿洲文化大背景下之《紅樓夢》的感受。論文《一夢紅樓何處醒——假如啟用滿學視角讀〈紅樓夢〉又會怎樣》,則集中推出了我的讀紅心得。
我以為:
——作者身份是徹底滿洲化了的內(nèi)務府漢姓包衣世仆;
——小說并非一般性描寫封建社會貴族生活,而是完整、具體、鮮活地摹現(xiàn)出清中期滿洲貴族現(xiàn)實生存及精神世界的大千樣況;
——《紅樓夢》用哀婉筆調(diào),狀盡了清代滿洲貴族之家盛極而衰的衍變,卻沒有反皇權(quán)傾向以及反滿洲傾向;
——書中大量涉及滿洲貴族府邸“家奴”形象及其心理,是作者深刻的社會記憶,為其他非滿洲作家筆底所無,關于家奴世仆的刻畫跟后世指稱的“階級敘事”并不搭界;
——《紅樓夢》突破中原千古文化重壓,一反常態(tài),唱響歌詠女兒“清爽”圣潔的新調(diào)式,實出自滿洲特別的“女尊”精神傳統(tǒng);
——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擁有薩滿文化因子,認定自然界“萬物有靈”這一薩滿教核心觀念,在小說里不期而遇者頗多,作者更以薩滿警世方式預言盛極而衰的世事規(guī)律;
——《紅樓夢》破天荒地展示了清代旗人京腔京白在造就文學巨制上令人意想不到的藝術(shù)征服力,以本民族雅俗共賞的審美尺度向標榜“文以載道”的中原文藝氛圍吹送著綠野清風,并為后世京味兒文學的建立創(chuàng)開先河;
——作為滿洲內(nèi)務府包衣旗人的曹氏雖非宗室,卻在興衰各階段與宗室成員聯(lián)系緊密,生活在共同的社會圈子,認識乾隆年間京師滿洲文人集團有助于對曹雪芹和他小說的研究。
我讀《紅樓夢》的主要體驗是:
小說《紅樓夢》,是源起于女媧補天剩下的一塊石頭,結(jié)穴于這塊石頭去人世間“瀟灑而又痛苦地”走了一遭所翻演摹錄的大型敘事。“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jīng)鍛煉之后,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這是開頭至為緊要的交代,近年間引起一些“紅學”專家關注。有論者認為,“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即長白山“勿吉”崖“清根”峰。我對這一發(fā)見持審慎的肯定態(tài)度。長白山脈曾為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滿洲族脈提供了世代繁衍的場域。滿人進關后其魂牽夢縈的民族圣鄉(xiāng)仍是長白山。近乎通盤滿化的曹氏雪芹家族在這上面跟出自女真舊系的滿洲人高度認同。然而,倘若一字對應一字地斷定“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就該破解為長白山“勿吉”崖“清根”峰,還是有點兒風險。不過,從《紅樓夢》總體文化傾向上來蠡測,將“大荒山無稽崖”,大致認作作者有意指代滿洲發(fā)祥地及其文化之根,亦不會去雪芹本意太遠。
小說主人公賈寶玉,來自大荒山的“頑石”、“靈石”,是被作者寓意模塑的、代表滿洲元文化基準內(nèi)涵的“喻體”,他從離開大荒山投胎賈府到復遁空門再返大荒山的人世游歷,暗寫出了作者對清初以來滿漢之間社會文化折沖的強烈心理感受。帶有滿洲民族原初文化質(zhì)地的寶玉,來到中原人文環(huán)境,極力保持真性情,卻為強大的異質(zhì)文化不容。已經(jīng)不合時宜的“靈石”心性,便是滿洲先民于天地與自然萬物當中形成的思維與心性,是對“大荒山”有靈性的自然界的秉承與師法,它極近似于薩滿教的思想范式。《紅樓夢》不曾提及薩滿文化,雪芹的精神世界卻較深入地擁有此種文化因子。“薩滿”概念被隱藏的同時,作者卻又縱筆疾寫出來他所欲以宣示的諸多薩滿教文化理念。《紅樓夢》要以薩滿教的方式,來預卜和警示些什么,即是作者意欲訴諸讀者的思想。自康、雍之際始,滿洲社會最嚴重的問題莫過于“八旗生計”。人們提到“八旗生計”多關注下層旗兵人口激增引發(fā)糧餉不支貧寒迭起的問題,殊不知這滿洲上層“大有大的難處”,一樣存在“生計”難題。雪芹要向讀者攤開的,是滿洲上流家庭或尚在潛伏或業(yè)已爆發(fā)的生計危機。他“十年辛苦”所要完成的,就是一個滿洲暴盛家庭于毫不自覺的狀態(tài)下一舉跌落于讀者視野的震撼過程。作為強化這條主線的寫作副線,講述了“顰顰寶玉兩情癡”,看似構(gòu)成絕佳配偶的“木石前盟”同樣走向完輸完敗。書里一切有價值的事物皆面向美好目標而走行不遠,兜一個圈圈兒便無可奈何地縱身于毀滅。
雪芹是敢于正視天地翻覆的大藝術(shù)家,也是一位極端的悲觀主義者。他在書中消耗許多精準用情的話語,來抒發(fā)胸中的大凄涼大悲切大痛悔。《紅樓夢》從作品敘事到詞曲搭配,用意全在于要寫出身處“盛世”之下“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根性悲觀邏輯。現(xiàn)世生活的樂極生悲、痛悔無望,作者置信不疑。他的追悔究竟是什么呢?是僅只在于豪門由盛及衰、由奢返貧的教訓么?自然有這一層,卻又不會僅此。由作者暗自布排了偌多滿洲元文化——薩滿教文化基因來看,雪芹的“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絕不只為傾吐賈府的傷心往事。業(yè)已具備滿洲元文化精神站位的作家,尚要表達的,是對于本民族進關以來文化遭遇的辨思。只要悉心閱讀就會感覺到,雪芹與其筆端的寶玉,不大喜歡儒教,不大喜歡道教,不大喜歡佛教,對中原文化敬而遠之。他們認可滿洲尊崇與敬畏自然之文化滋養(yǎng),更愿意在滿洲先民留下來的文化江河當中暢游。然而入關了,需要到儒、道、釋交融的汪洋中長驅(qū)游弋,需要在儒、道、釋規(guī)定的框架里合拍舞蹈,雖說也有些滿洲人較早適應了此種變化,就其整個民族來講,不適應則肯定是主流。一個難以適應異質(zhì)文化圍困的民族,會觸發(fā)災難,特別是當這種異質(zhì)文化本身就顯現(xiàn)出殘燈末廟景象的時候。滿洲進關前后在其高層出現(xiàn)的是否有必要準備撤回東北的辯論,余音尚在,賈府深陷他方文化境地的故事已經(jīng)上演。雙重文化之間的折沖興廢,早就苦苦折磨過清初滿洲人中的民族文化敏感者。“春江水暖鴨先知”,做過雙重文化比對的《紅樓夢》作者,乃是一只絕頂智慧的、既游過暖流又游過寒水的“鴨子”。
“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xiāng)是故鄉(xiāng)。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不須枉猜與索隱,這段曲詞足夠明白。雪芹將其文化冷暖的滿腔悲慟與追悔,一股腦兒撒到這部書里,平心而論,委實有欠公允。可一個人總有他的心理偏愛,總有他的傾向與局限。雪芹這樣聰穎卓異的文學家,能有這般深徹的歷史文化洞悉,極其難得。我不能茍同把雪芹和寶玉生硬地推到封建時代“反叛”的位置上,把作者和他的男主人公看成是充斥悲情的文化英雄,會更恰當些。
滿洲族文學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參憑于歷史大背景的民族文化反思。清初以納蘭性德為代表的滿洲族別書寫,此特點已現(xiàn)端倪。乾隆年間的曹雪芹通過《紅樓夢》將之激為洪波。絞結(jié)于歷史幻化、糾纏著文化遐想的滿洲文壇后起之秀例如老舍諸人,還將在隨后的時代就此奉獻良多。雪芹以《紅樓夢》參與滿漢交往時代的歷史文化思辨,其價值觀服膺于滿洲傳統(tǒng)傾向。主人公由大荒山“靈石”化身為人卻直截楔入進關百年后的滿洲望族家庭,這一點精巧絕倫的時空錯置(頗類后世的“穿越”書寫),恰好有利于觀察關外與關內(nèi)、百年前與百年后滿洲文化遭逢之眩暈跌宕,有利于寫透不同歷史歲月間同一文化持有將人們引向天壤不同的境地。作者對滿民族建清定鼎之利害得失有著怎樣的運思跟判斷,值得人們根據(jù)作品去反復考量。
“開弓沒有回頭箭”,歷史航船不可能駛回最初的港灣。社會的滄桑嬗變,常跟絕代風騷、雄踞史冊的大英雄們開些玩笑。一部捶胸頓足痛悔過往的《紅樓夢》,終于成了滿漢文化交通碰撞的生動摹本。
大學問家王國維慧眼如炬,指出過《紅樓夢》與中國文學(應當讀作中原漢族文學)質(zhì)的差異:“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于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存乎此。”
(作者原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主編)
〔責任編輯 宋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