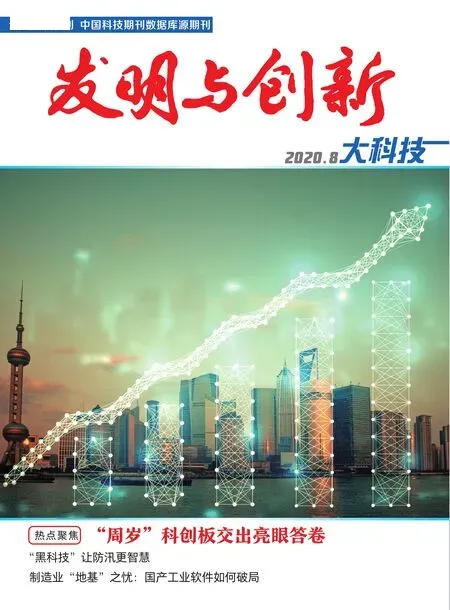共赴一場“逐火”盛宴
2020-09-03 01:25:14
發(fā)明與創(chuàng)新
2020年29期
火星,是太陽系由內(nèi)往外數(shù)的第四顆行星,也被科學家們認為是唯一可能會適合人類移民移居的星球。從天文學的角度看,在很早之前火星是處在宜居帶中的,這也就說明火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生命。
7月23日13時25分,我國在海南島東北海岸中國文昌航天發(fā)射場,用長征五號遙四運載火箭成功發(fā)射首次火星探測任務(wù)“天問一號”探測器,成功將探測器送入預定軌道,開啟火星探測之旅,邁出了我國行星探測第一步。除了我國,世界上還有不少國家也已啟動火星探測任務(wù),美國、阿聯(lián)酋將計劃于近期發(fā)射火星探測器。
探“火”迎來窗口期
作為地球的鄰居,火星并不算是“近鄰”。地球赤道周長約為4萬千米,光速僅需約0.13秒便可環(huán)游。但地球與火星的距離在5600萬~4億千米之間,這意味著就連光速單程可能都需要3~22分鐘。因此,探測火星需要選擇它與地球距離較近的時機。由于地球和火星都圍著太陽公轉(zhuǎn),怎樣才能有最近的距離呢?
全國空間探測技術(shù)首席科學傳播專家龐之浩形象地比喻道:“這就像田徑賽跑,地球在里圈,繞太陽轉(zhuǎn)一圈約是365天,而火星在外圈,繞太陽轉(zhuǎn)一圈約是687天。地球繞太陽轉(zhuǎn)的速度快,火星繞太陽轉(zhuǎn)的速度慢。如果太陽在中間,火星和地球在兩邊的時候,它們的最遠距離能達到4億千米以上,因此最好是在地球和火星距離比較近的時候發(fā)射,這樣就能讓人類“探火”之旅的“趕路”時間更短、所攜燃料更少、成本更加低廉。
地球、火星和太陽排成一條線的時候是最近的距離,約為5600萬千米。……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