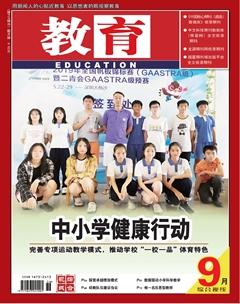正確認識傳統文化
張岱年(1909—2004),曾用名宇同,別名季同,河北獻縣人。中國現代哲學家、哲學史家。1933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任教于清華大學哲學系,后任私立中國大學講師、副教授,清華大學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1980年后任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名譽會長。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復雜的內容。正確認識傳統文化,就必須:第一,對于傳統文化進行全面的考察,力求避免“以偏賅全”的片面性;第二,對于傳統文化的核心即傳統哲學有比較深刻的理解,領會其中的精湛思想;第三,對于中西文化的異同也有比較全面的理解。
以下試舉例加以說明。
(一)二十年代以來,有一個比較流行的說法,認為中國文化是主靜的,是靜態的文明;西方文化是主動的,是動態的文明。事實上,這是一種片面的觀點。中國古代,固然有主靜的哲學家,但也有主動的哲學家,更多的哲學家則主張“動靜合一”,主靜的哲學家有老子、莊子、王弼、周敦頤等。老子講“致虛極、守靜篤”。《莊子·天道篇》云:“圣人之靜也,非日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饒心者故靜也。”王弼認為,宇宙萬象之中,靜是根本。周敦頤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這些是主靜的哲學。孔子則與老子不同,兼重動靜,他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孔子以仁智并舉,以為動與靜都是高尚的風度。孔子的生活態度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基本上是主動的。《易傳》宣稱:“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肯定動靜都是必要的,宜動則動,宜靜則靜。程頤不同意王弼對于復卦的解釋,認為:“一陰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周易程氏傳》)重新肯定了動的重要意義。朱熹、王守仁都是講動靜合一的。到明清之際,王夫之提出靜是“動中之靜”的觀點,肯定動是絕對的,靜是相對的,與王弼之說恰恰相反。在道德修養方面,王夫之也強調動的重要。他說:“圣賢以體天知化、居德行仁,只在一動字上。”我們綜合先秦至明清的哲學思想來看,可以斷言,主靜的思想并不占主導地位,怎能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主靜的文化呢?從文化的本質來看,文化發展的關鍵在于創造,創造都必須進行活動,在活動的過程中,在一定意義上,要保持一定的寧靜。寧靜只是活動的補充。應該承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主靜的思想亦只是主動思想的補充。
(二)近來又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貶低人的尊嚴的,是否認人的獨立人格的。我認為,這種看法未免失之于膚淺。封建時代強調尊卑上下的等級,專制主義強調臣對于君、子對于父、妻對于夫的隸屬關系,這些固然都是顯著的事實。但是古代哲學中卻也有肯定人的獨立人格、重視人的尊嚴的進步學說。如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明確肯定平民具有獨立的意志。孟子說:“人人有貴于己者”(《孟子·告子上》),明確肯定人人具有內在的價值。這些觀點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涵義。道家更是重視個人自由的。在儒家道家的影響之下,知識分子中間形成了“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這正是重視個人尊嚴的表現。宋明理學固然是維護封建制度的,但是理學家都強調“立志”,也就是肯定人們應有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意志。陸九淵說過:“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的做個人”。“堂堂的做個人”即是具有獨立的人格。應該承認,這一類重視人格獨立的思想才是封建時代傳統文化的精華。
(三)二十年代,有人認為中國文化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質文明,這更是一種片面的觀點。就精神文明而論,中國先秦哲學可以說與西方古希臘哲學媲美。但是,古希臘有兩種學術成就,都是中國所缺乏的,一是歐幾里得兒何學休系,二是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體系。能說中國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嗎?先秦時代,墨家對于幾何學與形式邏輯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可惜都還沒有構成完整的體系。中國文化對于世界文化的貢獻是四大發明,四大發明對于近代西方文明的興起是有重要貢獻的。這四大發明都屬于物質文明,能說中國沒有物質文明嗎?過去論中西文化的異同,多偏重中西之異,事實上,也應重視中西之同。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惟有兼重同異,才能對中西文化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同任何事物都包含矛盾的兩方面一樣,中國文化也是具有內在矛盾的統一體,其中既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既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必須正確認識本民族的優良傳統,這是繼續前進的內在根據。如果否認本民族的優良傳統,把過去的歷史都看成一團糟,那也就失去了前進的基礎,今后的發展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了。同時對于傳統文化的缺欠,也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克服那些阻礙進步的傳統習慣勢力,刻苦努力、奮勇前進。
“人貴有自知之明”,民族也是一樣。惟有認識了自己的缺點,才能舍舊取新,大步前進;惟有了解自己的優良傳統,才能保持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摘自《文史哲》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