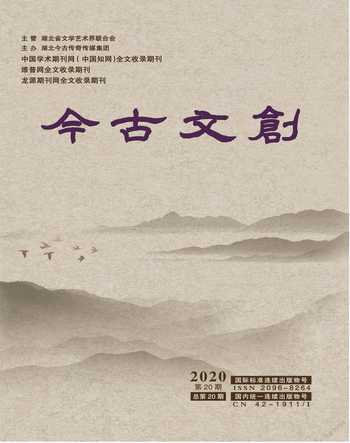個性主義與革命精神
【摘要】 縱觀丁玲延安時期的創(chuàng)作,知識分子的“個性主義”與共產(chǎn)黨員的“革命精神”兩種思想基因始終貫穿其中,只是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下,二者處于此消彼長的狀態(tài)。考察丁玲延安時期創(chuàng)作中彼此交錯的個性主義與革命精神,才能更清晰地了解丁玲,才能發(fā)現(xiàn)其延安時期作品的時代價值及其局限性,同時,也有助于梳理和認識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qū)文學思潮的演變、分析文學創(chuàng)作與政治的關系。
【關鍵詞】 個性主義;革命精神;思想基因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20-0012-04
作為一名深受“五四”新文化影響的作家丁玲,其早期作品《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小火輪上》等繼承了五四新文學人道主義與個性主義的傳統(tǒng),關注人的自我價值和人生意義,揭示了中國女性覺醒后的豐富而復雜的心理世界,這些作品奠定了丁玲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但考察評價丁玲,如若不理解其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nèi)心緣由,不理解其性格中強烈的人生抱負和革命傾向,則不足以完整把握丁玲其人其文的復雜性,也就很難理解丁玲后來的走向革命和革命話語下文學創(chuàng)作中個性話語和革命話語的此消彼長。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丁玲延安時期創(chuàng)作中個性敘事和革命敘事兩種敘事話語,往前追溯了丁玲的個性特征和潛隱的革命傾向,探索了丁玲內(nèi)心深處一以貫之的思想意識和創(chuàng)作基因。
一、“革命內(nèi)部的革命”
1936年11月,丁玲以一個成名作家的身份到達陜北后,備受重視和重用。在保安,她被安排到了最好的房子里即蘇維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熱情接待。在革命圣地延安,丁玲一心想當紅軍上前線,雖然蘇區(qū)的領袖們很希望丁玲“靜心的從事寫作生活”,“然而她已決意暫時放棄寫作生活,要在紅軍革命工作和陜北群眾中極力豐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再來開始創(chuàng)作”,她“不愿老戴著一個作家的頭銜,在蘇區(qū)里晃來晃去”。
在陜北,丁玲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革命活動工作,她隨紅軍總政治部到前方,擔任中央警衛(wèi)團政治處副主任、組織和領導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到前線宣傳演出。雖然這期間她被當選為“中國文藝協(xié)會”的主任和從事選編紅軍長征征文等革命文藝工作,但當時她的心思不在成立文藝協(xié)會上,丁玲儼然成為了革命隊伍中的一名革命者并且很享受當時的狀態(tài),她說:“這樣的生活,比起寫作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我喜歡這樣緊張的生活。”因此,她延安早期的文章多是突出戰(zhàn)斗性,敘述簡潔進展快速。
丁玲在延安的種種表現(xiàn),很多人認為丁玲左轉了并為之扼腕,為失去一位極具個性的作家抱憾不已。事實上,丁玲的轉變和當時她個人的處境不無關系。擺脫三年南京“囚禁”生活的丁玲,深切體會到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以滿腔熱情毅然放棄赴法國留洋的機會,抵達陜北,投身革命和革命文藝運動。丁玲延安早期“政治化”的作品真實反映了丁玲當時的心境。一個在南京被囚禁了三年的作家能在解放區(qū)得此殊榮且在政治上有所施展并得到上級的肯定,當然會有極大的成就感,感激之情自不待言。
可以說,丁玲剛剛到解放區(qū)時有很大的報效心理,她眼中的延安是帶給她希望的圣地。但是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時間后,當她發(fā)現(xiàn)她心中的“圣地”也有等級觀念、也有官僚主義,也存在對生命個體的漠視時,她那種與生俱來的獨特性以及知識分子的獨立和批判精神,使她開始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俯瞰延安,她對待解放區(qū)的立場由一開始的“充滿美好的想象”逐漸轉變?yōu)椤袄潇o地現(xiàn)實審視”,她以知識分子的敏銳和現(xiàn)代立場,感覺到了延安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多面性,因此,丁玲在創(chuàng)作“革命文學”時,在彰顯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同時,顯示出了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不隨波逐流的價值判斷。
1941年10月,丁玲在《解放日報》文藝專欄發(fā)表了《我們需要雜文》,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批判意識,丁玲呼吁:“我們的這個時代還需要雜文,我們不要放棄這一武器。”接下來,丁玲又發(fā)表了《三八節(jié)有感》,以深邃的女性關懷意識述說了在革命政權內(nèi)部革命秩序里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的事實。丁玲同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醫(y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也潛在地表征著個人與集體、理想與現(xiàn)實的緊張關系。
在1942年6月的延安文藝整風運動中,《在醫(yī)院中》這篇小說被當作立場有問題的作品受到批評,在1958年的《文藝報》“再批判”中又被視為“奇文”和“毒草”刊登出來。那么在這篇作品中,丁玲對革命踐行的批評,是否是她對革命的否定?事實上,丁玲的《在醫(yī)院中》所反映出來的革命內(nèi)部的問題正是1941年前延安的情況以及延安當時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的基本想法。
當時“暴露”根據(jù)地的“黑暗面”的作家還有蕭軍、艾青、羅烽和舒群等一大批知名作家,我們不能說這些作家不革命。對于他們尤其是丁玲來說,革命的號召力在于其對現(xiàn)實批判的有力和有效性,并提出一種關于生存狀況的更讓人憧憬的想象,但理想本身的非現(xiàn)實性使她難以滿意既存現(xiàn)實,而始終處于為達到理想而與現(xiàn)實“斗爭”的動態(tài)之中。
丁玲通過陸萍的視角將筆觸集中指向于陸萍與周圍環(huán)境之間的復雜關系及當?shù)厝说木駹顟B(tài),對于主人公陸萍及其性格,丁玲是同情的,無批判的,對于主人公所處的環(huán)境及周圍的人物,則是暴露和否定的。這些批判和揭露在延安當時當?shù)氐恼涡蝿莺臀镔|條件下確實有其合理性,同時也說明了丁玲作為深受五四精神影響的女作家,她以一種知識分子對革命的想象參加了革命并對革命抱有很大的期待,但在制度化的革命陣營里,其“革命”精神沒有被制度化,當最初的革命熱情漸漸化為冷靜的審視和思考時,對革命的想象在現(xiàn)實環(huán)境產(chǎn)生了變化,這種理想與現(xiàn)實、精神與體制之間的沖突,必將使革命者的革命熱情與所處環(huán)境處于一種悖論境地。
在此意義上,丁玲的批判性寫作就成為“革命內(nèi)部的革命”。
丁玲延安早期的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yī)院中》一樣,也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這篇小說中,丁玲揭示了解放區(qū)干部和群眾身上濃厚的甚至有可能會殺人的封建思想。另一篇小說《夜》則采用了解放區(qū)文學中少見的人性與情欲視角,塑造了何華明這一人物形象的多層次性,這比起同時期那些“高大全”式的領導干部,何華明無疑要真實可信得多。
在以上作品中,丁玲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解放區(qū)的某些陰暗面,實際是出于對解放區(qū)的愛,既然發(fā)現(xiàn)了“太陽”里的“黑子”就難以容忍它的存在。這種知識分子立場和意識的介入彰顯了丁玲處于革命政權內(nèi)部時的冷靜和理智,在當時的語境下雖然丁玲由此遭到了批判,然而現(xiàn)在回過頭看,反而是丁玲對革命的一種“忠貞不渝”,是“愛之深責之切”。
二、《講話》之后的個性堅持
許多研究者認為在接受毛澤東《講話》觀點之后,丁玲的小說失去了個性主義,個性話語淹沒在了革命話語之中。這不符合丁玲作品的實際。
不可否認,1942年的延安文藝整風運動對丁玲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此后,丁玲自動放棄了前一階段的思想與藝術探索,轉變了個性話語創(chuàng)作立場,自覺遵循戰(zhàn)時文化規(guī)范的要求并重新開辟創(chuàng)作之路。
于是,從1942年下半年起我們看到了“另一個”丁玲。擅長小說創(chuàng)作的丁玲,竟然在五年之內(nèi)沒有寫過一篇小說。1942年到1947年,從描寫八路軍戰(zhàn)士自我犧牲精神的《十八個》起,到《二十把板斧》《田保霖》《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qū)》《記磚窯灣騾馬大會》《民間藝人李卜》《袁廣發(fā)》《三日雜記》等,丁玲幾乎成了報告文學的專家。尤其是發(fā)表在《解放日報》上的《田保霖》,毛澤東因為這篇文章在多種場合表揚過丁玲,“丁玲現(xiàn)在到工農(nóng)兵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毛澤東的高度贊揚表明黨已經(jīng)接受并認可了她的這一創(chuàng)作方向,因而,她一發(fā)而不可收,創(chuàng)作了好幾篇類似的作品。
丁玲在保證“政治正確”的前提下,并未放棄她對包括女性在內(nèi)的個體命運和價值的關注與思考。但是,在革命話語占主導地位的語境下,她一時又難以找到將文學與政治很好結合的方式。直到《講話》后的第五年,丁玲以土改斗爭為題材,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才最終完成了她的心愿。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雖然帶有很強的政治性,但丁玲并沒有完全依照當時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即階級立場來表現(xiàn)這場斗爭,而是憑借她親自參加土改的切身感受和多年來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來表達自己對土改的理解。她沒有將土改僅僅作為一場貧雇農(nóng)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爭取政治權利和經(jīng)濟權利的階級解放運動,而是站在廣大的人類解放的立場,將階級解放與當時歷史境況中可以實現(xiàn)的超越階級解放范疇的人的解放有機結合起來,從廣大的人類的解放的高度來審視土改,從而塑造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黑妮、顧順這兩個人物形象。
按照當時主流文學創(chuàng)作原則,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物一律是丑陋的,形神俱丑。可丁玲偏偏塑造了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美麗的黑妮。黑妮從小沒有父母,被二伯父地主錢文貴當作仆人一樣使喚和利用著。她美麗,單純,向往美好自由的婚姻,但錢文貴為了自己的利益,試圖操縱她的婚姻,美麗善良的黑妮對婚姻自由的追求沒有因為錢文貴的干涉阻撓而改變。
顧順是分地時被馬馬虎虎劃作富農(nóng)的顧涌的三兒子,他與黑妮的遭際相類似。由于富農(nóng)對貧雇農(nóng)存在封建性剝削,所以他們不可能成為共產(chǎn)黨在農(nóng)村的可依靠對象,而富農(nóng)的子女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被歧視的對象。因此,在當時很多作家的筆下,富農(nóng)的子女都是落后分子。可是,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顧順是積極要求進步的“規(guī)規(guī)矩矩”的青年, 是個土改積極分子。
通過黑妮和顧順這兩個人物形象可見,丁玲對于處在兩個階級、兩種勢力生死搏斗之間的無辜者,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和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丁玲關懷的是每個人的自由和解放,這種自由和解放不僅包括個人在物質上的滿足,更包括個性的完善,個人做人權利的被尊重。黑妮、顧順在物質上不算貧窮,然而他們在精神上及個性發(fā)展上還存在著諸多的不自由,他們應該并且可以通過土改去獲得這些方面的解放,機械盲目地將他們劃入剝削階級陣營是形而上學的做法。
三、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尋求生命的熱和力
丁玲在20世紀30年代成了“革命作家”,在此之前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個性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她的早期作品探討的是個體生命的價值、自我實現(xiàn)和人生的意義。崇尚個性自由和無政府主義的丁玲為何會走上革命道路,在加入政治革命行列中后,其成功之作又為何存在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不盡一致的東西?根據(jù)現(xiàn)有的作者生平資料與對丁玲作品的分析,我們有理由推斷,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尋求生命的熱和力、參與社會改革的強烈的事業(yè)心,是丁玲一生不懈的追求。
受母親的影響,丁玲很早就樹立了強烈的人生抱負和事業(yè)心。丁玲的母親是對丁玲影響最大的人,如果說丁玲的才氣更多來自父親,發(fā)奮自立的男孩子性格則源自母親。丁玲的母親于曼貞女士出生于書香門第,嫁到蔣家后,丈夫早逝,家境敗落,但她獨立、堅強,在向警予等人的影響下,她積極接受進步思想,帶著丁玲和弟弟靠教書謀生,成了一個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工作者。
后來,在丁玲14歲時,丁玲的弟弟因患肺炎去世,丁玲和母親相依為命。丁玲的母親為環(huán)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為,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丁玲身上。她帶著丁玲遠赴他鄉(xiāng)求學,她希望丁玲能“為社會上作一番事業(yè)”,“找著一條改革中國社會的路”。可以說,丁玲是母親的精神寄托和事業(yè)上的希望。丁玲說“那時最怕的也就是自己不替她爭氣,不成材,無所作為;我甚至為此很難過。”
母親獨立不倚的人格和對丁玲的殷切期望,使得丁玲具有不同于普通女子為社會著想的人生追求。基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丁玲在胡也頻犧牲之后將不滿周歲的兒子交由母親撫養(yǎng),自己在上海開始新生活,因為對于丁玲來說,自我實現(xiàn)是最重要的。1947年,丁玲在給逯斐的一封信中談及孩子和事業(yè)的權衡時,她說:“老實說,我還是更愛我的工作。假如孩子成為我工作的‘敵人’時,我寧肯犧牲孩子。”丁玲的一生正是這樣,不斷追求人生的理想,尋找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也正是這種追求成就了丁玲不凡的一生。
丁玲后來為何走上了創(chuàng)作之路,用她自己的話說:“我那時為什么寫小說,我以為是因為寂寞,對社會不滿,自己生活無出路,有許多話需要說出來,卻找不到人聽,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機會,于是便提起了筆,要代替自己給這社會一個分析。”和現(xiàn)代文學史上女作家張愛玲、蕭紅自小就喜歡文學不同,在不同時期的丁玲自述中,少年時期的生活令丁玲印象最深的不是文學閱讀與寫作,而是社會活動帶給她的沖擊以及激發(fā)起的投入社會、改革社會的欲望與激情。從故鄉(xiāng)湖南常德到省會長沙讀中學,再到現(xiàn)代都市上海和都城北京尋發(fā)展,丁玲參與社會改革的渴求一直是丁玲前行的動力。后來,由于追尋無果而異常苦悶,丁玲說:“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于是我寫小說了,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鄙視和個人孤獨的靈魂的倔強掙扎。”
可以說,《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這兩篇丁玲在大革命失敗數(shù)月后創(chuàng)作的最初的兩部小說不過是作家本人在尋找出路而不得的狀況下的一種心理治療術,一種釋放苦悶與絕望的手段。某種意義上,丁玲與“文學”的擦碰,完全是一種無奈之舉,用她自己的話說,在某些人眼中高不可攀的“文學”成就在她那里一點不重要,因此,與其說丁玲的起點是“文學”,不如說是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尋求生命的熱和力的人生抱負和人生理想。
由于《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攀上了文學的高峰,但丁玲內(nèi)心真正尋找的卻是不同于普通女子,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改革社會的出路。她在1985年3月1日致白濱裕美信中說:“我那時實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懷念在上海認識的一些黨員,懷念同他們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離開了他們。那時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遠離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頻在內(nèi),都不能給我思想上的滿足。”
丁玲在1984年4月15日致徐霞村信中說:“也頻能愛我,但他在政治上不能做我的向導”。后來,從事創(chuàng)作的丁玲與丈夫胡也頻、好友沈從文創(chuàng)辦《紅黑》月刊時談及她與沈從文的思想差別時說:“他已經(jīng)不甘于一個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滿足于一個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當一個教授。他到吳淞中國公學去教書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識地對左翼的文學運動者們不知為什么總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為比他們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終規(guī)避著從文的紳士朋友,我看出我們本質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爭執(zhí),破壞舊誼,他和也頻曾像親兄弟過。”可以看出,丁玲具有強烈的事業(yè)心和革命傾向,交友看重政治態(tài)度。
后來促使丁玲永久地與共產(chǎn)黨的革命隊伍聯(lián)結在一起的,可以說是丈夫胡也頻因加入革命隊伍宣傳革命被殺害的仇恨與她在南京囚徒生涯的恥辱,國恥家恨加速點燃了丁玲的革命熱情。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共產(chǎn)黨提出的政治理念與知識分子崇尚個人獨立意志的民主思想存在一定的契合。這也就是為什么丁玲在1936年逃離南京時,沒有聽取馮雪峰的建議到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也沒有聽取潘漢年的建議轉赴法國宣傳中共主張并為紅軍募捐,而是積極地投入了黨中央的懷抱,執(zhí)意要去陜北,并做好了棄筆從戎的打算。可見,丁玲將走向“革命”看作了通向自我實現(xiàn)的具體途徑。
成為“革命作家”之后,丁玲并未放棄五四精神,她仍然特別重視思想革命,而且,追求個性自由的一面也一直潛伏在她身上,她能夠不依附于任何現(xiàn)實政治勢力,能夠根據(jù)自己的價值判斷發(fā)出不同聲音,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時代語境下,她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yī)院中》《夜》以及后來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仍存在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不盡一致的東西。
四、結語
丁玲作為知識分子的五四精神在戰(zhàn)時政治文化規(guī)范中的實踐,這種實踐表明了具有五四精神的丁玲與中國革命的復雜關系。正如李向東、王增如在《丁玲傳》中所描述的“這是一種既相向而行,生死與共而又不無矛盾和抵觸,甚至必有抵觸和磨折的復雜關系。而之所以如此復雜,則既關于現(xiàn)代中國革命的特性及其對革命文藝的規(guī)定性,也關乎丁玲自己的革命性和個性”。考察丁玲延安時期創(chuàng)作中彼此交錯的個性主義與革命精神兩種思想基因,對于我們認識和理解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qū)文學思潮的演進和分析當時文學家與政治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個案。
參考文獻:
[1]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188.
[2]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325.
[3]丁玲.丁玲全集(6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9.
[4]丁玲.丁玲全集(12卷)[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6.
[5]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48.
[6]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47-48.
[7][8]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50.
[9]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62.
[10]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11.
作者簡介:
呂文玲,女,碩士研究生學歷,河南商丘人,研究方向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傳統(tǒng)文化。鄭州市城市可讀性建設研究基地成員,鄭州職業(yè)技術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