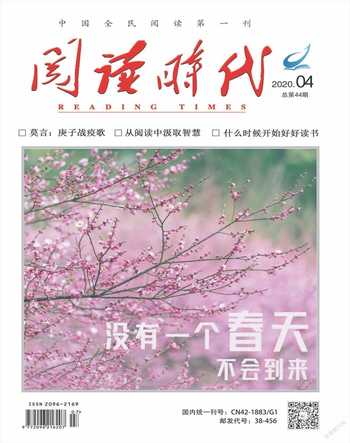冷暖盡在“形容詞”
周柳鶯
傳說漢字是由一位叫倉頡的古人制造完備起來的。其實一人之心,何以能識宇宙之玄機,識人間之冷暖?若不是后人不斷挖掘補充,使之盡善盡美,也是難以想象世間萬物,將用什么方式去書寫。只有文字讓一顰一笑,一動一靜的事物長存,得以弘揚。
其實文字的功績不在文字本身,是一個個帶有修辭色彩的形容詞和副詞。形容詞所顯現出的各種表象,都可以回歸于視覺世界。那些曾經的過去和過去的曾經,又是怎樣的生動、深刻地存活過了。文字之中,最玄妙的應是一個個惟妙惟肖,神態各異的形容詞了。一切生命的顏色,都是由形容詞描畫涂抹而來,而每一個恰當的形容詞的應用,又將一個個或明媚或晦暗、或愉悅或痛苦的故事躍然紙上,讓讀者看得瘋狂,也看得癡迷,不得不感嘆先人城府,浸染了故事的生命,最終又用聯動的形容詞賦予故事的永生。
以前曾驚羨于古人的某些比喻,依靠不同組合,產生出具有靈性的想象不是太難。在代表想象力豐富的同時,作者的心靈世界和意志,借此發揮作用,比如說悲哀到“肝腸寸斷”,鐘情到“柔腸百結”,沮喪到“五內俱焚”,憤怒到“怒發沖冠”,深刻到“刻骨銘心”,困難到“進退兩難”。驚羨歸驚羨,既然有這樣的精確比喻,造詞的人,定是所言非虛。能造出如此恰如其分的詞,也許只有那些愛恨分明,鐘情重義的先人才有吧。
傳說,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愁白頭,“不知君心苦,只是未到傷心時”。今天的人如何能體味到古人的“灰色比喻”?誰會想到,一個個傷心欲絕的故事由來。形容詞是用來修飾名詞或代詞的,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質、狀態和特征。形容詞也有短語的結構,是帶有“的、地、得”的動詞,構成形容詞短語,或是動詞短語,還是其他的像“悠遠、幽靜、澄徹”這樣的詞。只有那些能真正安心于靜樸之境,無聲之遇的人,才能領悟到詞語的含義。他們與天地為伍,有“孤舟蓑笠翁,獨鉤寒江雪”“玉鑒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的心境。他們有喜怒哀樂,全然無需憑借外物之力,宇宙浩然,蒼生碌碌,自不缺我這一瓢飲。
積極樂觀豁達的人,屬于他們的形容詞應該是最多的。如果說“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是生活中阿Q精神的話,他們的苦也許只是幸福的點綴。于是乎“明媚春光、柔波柳浪”皆入情懷,“繁花似錦,功名富貴”都可不求,“巧笑顧盼、春衫飛袂”鐘愛有加,“碩果飄香,高樓飲風”皆是人生快事……讓快樂并著快樂,幸福并著幸福,這便是生活的原生態。
燈火闌珊處,飲食男女在人間的生活,只為“情”字。而有人卻喻它為“毒”。細品何為情,可有毒?“多情自古空余恨”,若被所傷,定是重情重義之人。像楊過和小龍女,愛得癡纏,愛得刻骨,只想相依共生,做對神仙眷侶。不過人海茫茫,相知相守,卻是極為罕遇之事。尋常普通人,才是真正的風景。“在天愿做比翼鳥,在地愿做連理枝”“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天地攜手,燈下共讀”,我們可尋文字的形容之中,找到縹緲悠遠的身影,覓得可希可盼的遐想。不能體君事,但愿與君共傷懷,實在是難得。形容詞成了一個特定模板,在無數文本中不斷重演。
近來覺得“堅強”二字,算是一個滄桑的字眼,沒有經過痛苦、心碎的經歷,我們就不能真正體味“堅強”的重要和難得。化解人生之痛,也許靠佛之“悟空”,士之“通達”,而要直面針氈之刺,親嘗鉆心之痛,遍嘗煎熬之苦,深悟孫悟空八卦爐之燒灼,五行山下的重重久壓,才能讓時間的佛手印,拂去心靈的陰影,真正迎來心靈對快樂的頓悟。
無論曾經相親還是曾經久違,文字總都以其美麗的溫暖,創造出深邃的美麗。未曾忘,也永不言棄。在文字一隅的形容詞,以飛翔之態,覓得一方清靈山水和自由時空。縱觀文字的歷史,漫長悠遠,輕風拂處間。我希望,文字所散發出的清秀活力,于我、于文字、于生活都心有余香。
文字很神奇,它描述再現詮釋事物的真相,讓后人進行評說,于我所閱讀所感受的理解,你我都成了文字有緣人。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