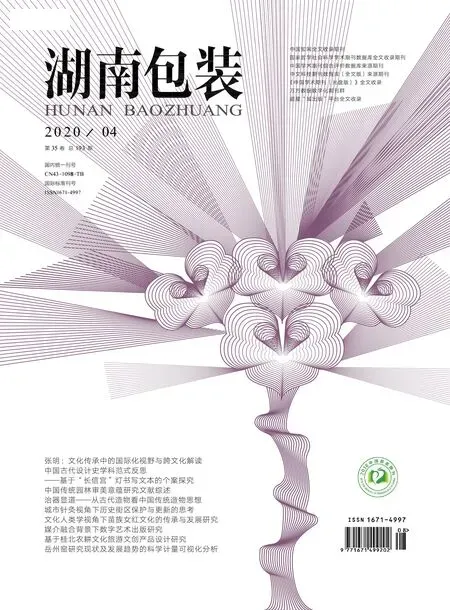中國古代設計史學科范式反思
——基于“長信宮”燈書寫文本的個案探究
吳文治 1.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上海 210620
2.同濟大學上海國際設計創新研究院 上海 200092
中國古代設計史(或稱中國藝術設計史、中國設計藝術史等)是過去近三十多年設計史研究的重心,直至20 世紀末以后,中國近現代設計史才開始覺醒。如何銜接彌合工藝美術史研究傳統和西方現代設計概念之間的裂痕,一度成為設計史界與工藝美術史界費盡心力的事情。隨著設計觀念的廣泛傳播與設計學科的蓬勃發展,設計學界對于設計學的科學性、合法性的反思顯得十分迫切。過往,中國知識人多少背負著“巍巍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和清末以來“落后挨打切膚之痛”的雙重情感,這種爭論容易被置于預設和不自覺的“文化傳統”“文明差異”“文明沖突”等“文化土壤”差異的宏大命題當中,并夾雜著“民族自尊”“中體西用”“洋為中用”的“經世轉化”思想的潛在影響。
在經過近40 年的討論后,中國(古代)設計史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如夏燕靖的《中國藝術設計史》(2016)、趙農的《中國藝術設計史》(2015)、李立新的《中國設計藝術史論》(2011)、高豐的《中國設計史》(2008)等。工藝美術史在經歷了一定的曲折之后,也沿著自身名稱和發展軌跡向前推進,新出或重版著作亦多。如田自秉的《中國工藝美術史》(2018 修訂本、2014)、尚剛的《工藝美術史新編2版》(2015)和《極簡中國工藝美術史》(2014)、杭間的《中國工藝美學史》(2019 第三版、2007)和《中國傳統工藝(英文版)》(2018)、朱和平的《中國工藝美術史》(2019)、張玉花和王樹良的《中國工藝美術史》(2019、2018)等多種。由此可見,經歷了1998 年“工藝美術”專業的取消到2011 年重設,在國家層面可謂也體現出工藝美術向設計“進化”過程中的“返祖”現象,對設計史的反思也促成了部分學者思想的轉變[1](杭間在此文中寫道:“1986 年,……我在當時的《中國美術報》發表了……《對‘工藝美術’的詰難》,魯莽提出要以‘現代設計’取代‘工藝美術’,……現在看來,我們那時的誤會基于對設計‘現代性’理解的兩個差異:一是認為‘設計’總是建立在工業文明的基礎上;二是‘工藝美術’作為農耕文化自然經濟的產物,將會隨著社會形態的發展而淘汰。這種‘進步論’的參照物其實是西方文化,其邏輯也是建立在技術進步的背景上的,它致命地忽略了設計的‘文化’因素,以及設計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來的多樣化生存。”)。

圖1 “長信宮”燈在二號墓的發掘位置[2]233

圖2 “長信宮”燈出土實測圖[2]259
隨著設計史研究的推進,對于自身學科范式的探索和反思,催生出設計學研究者的“自我覺醒”意識和進入主流學術的“自我訴求”意愿,這體現在諸多學者的研究中。筆者擬基于設計學范式(中國古代設計史的書寫范式)討論的大背景,通過對不同學科專業中關于“長信宮”燈書寫文本的個案研究,探求設計史與其相關學科之間的關聯性與差異性,對其所延續的傳統和成長的歷程進行考察:今天的中國設計史研究是否進入了現代意義的設計史研究語境?當代中國設計學研究與設計史書寫在本位文化與對標體系的坐標之間,是否找到了科學路徑和處理方法?并就中國古代設計史研究提出建議。
1 嚴謹:考古文本中的“長信宮”燈
關于“長信宮”燈的文字資料中,《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有著全面的記錄。這份總共1639 字的報告,可以分為4 個組成部分來分別解讀。第一部分,是關于出土情況的基本介紹,第二部分,為“長信宮”燈本身物理狀態的描述,第三部分為燈具銘文的歷史考證與相關推測,并有部分構件的重量、容量記載,最后部分可視為工藝美術史或設計史中的常見內容。
《滿城漢墓發掘報告》第一部分提到,“‘長信宮’燈,出于主室門道內口西側,出土時燈的各部分散于地面……燈的外形作宮女跪坐持燈狀,體內中空,無底。通體鎏金。全器由頭部、身軀、右臂、燈座(分上下兩部分)、燈盤和燈罩(由兩片屏板組成)六個部分分別鑄造組合而成。燈通高48(人高45.5)厘米”[2]255。這部分內容提到了出土時在墓葬中的方位、出土狀況,以及造型特點、制作工藝、組成部分和高度尺寸(圖1)。
第二部分非常詳細地描述和分析了整個燈的人物形態、動作姿勢、衣著特征、工藝做法、基本原理、組成部分等,并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了燈罩、燈盤和燈座的具體細節。如,對造型的描述為“宮女頭梳髻,發上覆簂(即巾幗)。上身平直,雙膝著地,跣足,足尖抵地以撐全身。右臂高舉,袖口形成燈之頂部,肘部可以拆卸,整個右臂起煙道的作用;左臂伸向右方,手持燈盤……”對燈罩的分析為“燈罩由內外兩片弧形屏板組成,合攏成圓形,高10.4、直徑14.8 厘米。內片屏板角部稍殘,外片一角有直角形缺口,與燈盤方柄相扣。[2]255” 燈盤的記錄是,“燈盤直壁平底,壁分內外兩重,形成寬0.9、深1.8 厘米的凹槽之一周,兩片屏板嵌于凹槽之中,可以左右推動。盤心有一蠟釬,系安裝蠟燭之用。盤的口沿飾寬帶紋一周,底部形似圈足,置于燈座上。燈盤有一平出方銎柄,原系安裝木柄,銎中朽木尚存。柄長5.5 厘米,燈盤高4、直徑16.3 厘米。[2]255、258” 燈座則描述了結構組成和造型“燈座分為上下兩部分,可以拆卸。上部形如豆座,上面可以直接插入燈盤底部;下部形如豆盤,盤口與上部的底座相扣。宮女左手緊握燈座底部的圓形座柄。[2]258(圖2)”
第三部分,對“燈座、燈盤、燈罩屏板及宮女的右臂和衣角等處刻有銘文9 處,共65 字”做了記錄,共有6 小點內容。如第一小點記載為 :“(1)上部燈座底部周邊 :‘長信尚浴,容一升少半升,重六斤,百八十九,今內者臥。’外側刻‘陽信家’。燈盤實測容量為265 毫升,重量1235 克 ;上部燈座實測重量為262 克。根據實測結果,銘文所載的容量當系指燈盤的容量,而重量則為燈盤和上部燈座重量的總和。”緊接著,對“銘文中‘長信尚浴’‘今內者臥’等字樣”進行分析,認為“應是該燈入‘長信宮’后所刻的。[2]261” 最后通過分析漢代婚姻制度、長信宮主人與漢文帝的親緣關系等,推測竇綰可能是竇太后的家人,這件銅燈可能是竇太后送給竇綰的。
第四部分是對“長信宮”燈設計的總體分析。“‘長信宮’燈的設計十分精巧,宮女的造型極其生動,燈的各部分作有機的聯系,構成一個整體,同時又可以拆卸。燈盤可以轉動,燈罩可以開合,從而可以根據需要隨意調節照度的大小和照射的方向。燭火的煙炱可以通過宮女的右臂進入體內,使煙炱附著于體腔以保持室內的清潔……。[2]261”
從上述引文來看,第四部分中,“設計十分精巧”“造型極其生動”“各部分作有機的聯系,構成一個整體,同時又可以拆卸”等,完全可以視為設計史的通常寫法。如果稍作拓展,則其他三部分中,也可以在現有的其他史學論述中找到相應描述。
另外,考古學關于“長信宮”燈的相關論文,也對此作了相應的“設計解讀”:滿城漢墓出土的“長信宮”燈以其優美的造型,獨特的設計,精湛的技藝,形成了科學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體現了裝飾性與實用性的和諧統一,不僅是一件國之瑰寶,而且成為了漢代燕趙地區乃至中國古代的標志性藝術珍品[3]。旋即進入考古學的古史辨環節中。由此可見,考古學中蘊含著工藝美術史的先天條件和史料來源。如尚剛所言,“一般講,時代愈先,考古學界的投入就越多,成績也就越大,中國工藝美術史研究對其倚重也越多”[4]。這對于中國設計史而言同樣適用。“長信宮”燈在考古報告中的描述,為我們建立了與設計史、工藝史等進行文本對照的樣本。畢竟,整體來看,現有工藝美術史和設計史在“設計解讀”上雖有一定補充,但整體水平仍然有待提升。
2 演繹:設計史文本中的“長信宮”燈
高豐的《中國設計史》(下稱“高本”)對于“長信宮”燈,僅僅是一筆帶過(原文: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及其妻竇綰的墓葬,出土了包括有著名的“長信宮”燈在內的銅燈20件,另有鐵燈、陶燈45件)。該書的特點在于,它并沒有局限于單件物品的介紹式論述,而是將“燈具設計”作為一節,從功能合理、結構科學、造型生動、裝飾富麗4個方面總結了漢代燈具設計的成就[5]。不無遺憾的是,當我們讀到徐騰飛的《科學與審美的統一——長信宮燈研究》(2005 年)一文時發現,高本大部分照搬了徐文的研究結論[6]。

圖3 設計史研究中關于“長信宮”燈的圖解[10]50
李立新的《中國設計藝術史論》(下稱“李本”),也采取了與高本類似的方式,打破了常規的單件作品“流水式、介紹性”的描述,而是在“更為合理的功能設計和品類的系統齊全”總結下對造物設計中“物”的規范、簡化、系統、優化、協調、效益等原則進行了概括。然后寫到,“河北滿城突出的長信宮燈…這些青銅燈具的設計充分發揮了照明的功能,最突出的是燈罩設計,它由兩片活動可移的弧形罩板組成,可根據照明需要,注意調節光照方向和照明強度,同時又滿足了擋風、散熱等燈罩的基本功能。在滿足照明功能基礎上還考慮到室內環境的保護。……在結構上,燈具的每個構件包括座、盤、罩、枝、柱均可輕易卸裝,攜帶及清洗十分方便。[7]” 兩者都沒有單獨對“長信宮”燈做過多的“設計”發揮。
趙農在《中國藝術設計史》(下稱“趙本”)對于“長信宮”燈的描述并無特別之處,對其排煙原理也僅做了想當然的推理。如“中間空洞而封閉,利用虹吸的物理原理,將燈油的煙氣排放到身體中貯存的水里,使煙氣得到自然凈化”。對“長信宮”燈的評價“其設計思想超越了時空,亦是難得的超凡脫俗的佳作”也稍嫌夸張[8]。
沈愛鳳的《中外設計史》(以下稱“沈本”)則用到“宮女執燈的右手呈倒喇叭狀”“以分鑄法制成各部件后組裝而成,形態概括、做工精細”等。但對“利用虹吸原理凈化燈燭燃燒的煙氣”的論述則有失偏頗,因為虹吸原理預設的前提是“長信宮”燈底座能貯水[9]。
王強主編出版的《中國設計全集.第16 卷,用具類編.燈具篇》(下稱“王本”)在設計史中闡發最為詳細,但問題也很明顯。如“該燈以宮女身軀為體,體內中空,以盛放清水……燈盤中心有一可插燭的支釘”“煙燼……溶于清水,有煙而無塵。”[10]22(圖3)問題在于,燈盤中心是否是插燭的支釘?名稱是否準確?宮女體內中空但底座開口,不能盛水,也不存在煙燼溶于清水的可能。
以上所列,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前中國設計史(古代)研究“長信宮”燈的大概面貌。高本、趙本是按照傳統編年史的體例撰寫,李本則尤以造物概念和“有史有論、史論結合”為突出特點,沈本除了“虹吸原理”預設能盛水之錯誤外并無特點,王本則是類編體例的書寫方式。總體來看,當前的中國古代設計史研究,大約都是采用這3 種方式。
當然,在具體內容上,趙本融入了部分建筑、村落、城市等的內容,探索了中國設計史研究更廣闊的包納性可能。當我們總體比較5 本設計史中關于“長信宮”燈的書寫文本時,綜合起來可以歸納為造型、尺寸、材料、結構、工藝、原理、裝飾是7 個核心要素,這大概也可以視為設計史書寫的七要素。需要提出的是,高本、李本并沒有直接指明“長信宮”燈個案能貯水,趙本、王本則直接論定該燈可以貯水,并以其作為重要原理進行演繹論述。經實物勘察和多方請教求證,可以確認“長信宮”燈的燈身底座完全不密封,底部為開口狀,不能貯水,中央電視臺拍攝的專題紀錄片在這一點上也發生錯判(圖4)。這也說明,所有關于“長信宮”燈貯水的“設計”分析演繹,都是不成立的。這一答案,與《滿城考古發掘報告》“無底”和尚剛在《中國工藝美術史新編(2 版)》中“不能貯水”的定論是一致的。
3 多維:工藝美術史等文本中的“長信宮”燈
杭間曾針對設計史與工藝美術史的差異性寫道:“在中國古代造物的歷史中,‘工藝美術’的‘對象’也同時是‘設計史’的重要‘范疇’,……只不過是,當我們用‘設計’的眼光去看那些原來屬于‘工藝美術’的東西時,它多了一些現代的角度、生活的視野以及從廣義功能出發的審美維度。”但兩者不能等同,不能互相取代[10]序言。 錢鳳根則把工藝定義為:采用慢節奏、低效率和小規模制作的手工為主的生產方式,產品在小范圍或本地區內采取物物交換的方式,手藝技藝成為價值和附加值的重要依據。制作個體或主體主導的價值標準幾乎不會發生什么變化。與之不同的是,設計是以機械為主的快節奏、高效率和大規模機械化、流水線制造的生產方式,完全改變物品的價值內涵。在多區域乃至國際范圍內采取流通的銷售方式,因此,物品的價值標準不再由制作主體或設計師主導。這樣定義和區分的好處在于:第一,工藝和設計因地區和時代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而并存,動態的觀念可以避免按時代風格模式描述它們的困難,而陷入編造新名詞的左右搖擺之中;第二,以設計師設計作品為主導的設計史方法,實際上是美術史模式下的工藝價值觀的延伸,是對設計史發展的束縛[11]。 有學者認為,“工藝美術史是設計史的一部分”[12],現實著作中,似乎“中國古代設計史成了工藝美術史的一部分”,前者只是“低質寄生”于工藝美術史。
田自秉在《中國工藝美術史(修訂本)》一書 “虹管燈”中對“長信宮”燈的描述是:“河北滿城出土的著名長信宮燈,塑造出一優美的仕女形象,左手托燈,右手提燈罩,以手袖為虹管,處理得十分自然。燈體成圓形,有兩塊瓦狀的罩板,可以任意調節光照的方向。[13]”尚剛在《中國工藝美術史新編(2 版)》寫道 :“釭燈往往裝飾華麗,而設計極富匠心。它們設吸煙管,能將煙氣導入燈身,燈身常可貯水,以使煙氣溶于水中,可降低空氣污染。燈罩的罩板可以開合,以調節光線的強弱和光照的方向。……長信宮燈最著名,但它屬于單吸煙管的一類,且底部有空,不能貯水,故不及其他釭燈適用。[14]”另,尚剛在《古物新知》一書“適用原則”中談到,“造型和裝飾都要合宜,濫施雕琢與適用的原則大相徑庭……但無數作品都是其智慧和才華的豐碑。楷模是漢代的釭燈和唐代的香囊,它們融美觀與適用于一身,構思之巧、制作之精,其設計原則至今仍可視為典范”[15]。顯然,“長信宮”燈亦在此列。


圖4 長信宮燈的出土情況、原理誤讀及實物照片
依文獻資料來看,涉及“長信宮”燈的文本,除了前文所述三科之外,還有藝術史、美術史、機械史、醫藥衛生文物圖典、雕塑史、古代青銅器史、《辭海》和數不勝數的常識類出版物。當我們一一閱覽并仔細比對之后,不難發現這些描述基本不出于前文的書寫范圍,因此也無需一一列舉。以下僅舉幾例分析。
藝術史方面,在中國文物學會專家委員會主編的《中國藝術史圖典》(下稱《藝典》)中對“長信宮”燈值得注意的是“盤心有一蠟簽”和“經有關冶鑄工藝史學者研究,此燈的頭部、右臂、身軀連同左手都由失蠟鑄成,內范基本依鑄件外形制作,甚至左手握燈座處內空形狀亦與手指外形相同,所以鑄件壁厚均勻”[16]。其對冶鑄工藝的補充則較有價值。
美術史方面,洪再新的《中國美術史》(下稱“洪本”)中相應的背景描述“活躍在兩漢社會的藝匠百工,根據所在地的美術傳統,加上全國流行的時尚,有效地滿足了雇主的需求”[17]。可作為其他材料的補充。
機械史方面,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編的《中國機械史(圖志卷)》(下稱《機械本》)突出了鎏金技術的分析。記之為 :“鎏金技術至遲始于戰國時代,它是把液態汞金齊涂布于銅銀等器物的表面。再經加熱烘烤,令汞揮發而使金均勻地附著其上的工藝。長信宮燈至今仍金光耀目,足見西漢時鎏金技術之精湛。[18]”
《辭海》中“長信宮燈”詞條,并無特色和獨到之處[19]。(《辭海》中“長信宮燈”詞條記錄為:西漢宮廷用的銅燈。1968 年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之妻竇綰墓出土。燈作宮女跽坐執燈形,通高48 厘米。通體鎏金。宮女右臂和體內中空,可以將煙炱導入體內,使室內空氣清潔。燈壁可開合,以調節光照的方向與照度。燈上刻有“陽信家”等字。長信宮是西漢太后所居宮名。竇太后是劉勝祖母,該燈應是竇太后賜給竇綰的。此燈設計合理,工藝精湛,宮女造型生動,是漢代青銅燈中的佳作,代表了漢代青銅工藝的水平。現藏河北省博物館。) 孫機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下稱“孫本”)中寫道,“此燈作一宮女跪坐捧物狀。宮女梳髻覆幗,頭部微俯,著深衣,跣足。跣足是在君前示敬之意。整個身姿也流露出一種恭謹的神情,正符合她的身份。宮女的雙臂安排得極為自然;其實上臂內是煙管,下臂還要起支承燈座的作用。此燈雖只有單煙管,但燈體底部有打孔,對氣壓可起調節作用。不過燈體內因此不能貯水,消煙的作用就比不上能貯水的那一種了。[20]”通過查閱國外關于長信宮燈的相關研究文獻,我們可以看到,國外極其有限的展覽用介紹性文字,主要引用的是孫機的研究成果,體現出孫機先生在這一領域具有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圖5)。
從上述所錄文獻來看,《藝典》對于“內范”“壁厚”等分析不多見,洪本和《辭海》都沒有特殊之處,即沒有突破考古發掘報告的基本認識,在部分名詞(如蠟簽)方面亦沒有得到確證,總體上呈現出改寫、簡寫于考古發掘報告的痕跡。最大的亮點出現在《機械本》中對“鎏金技術”的分析,這是其他各專業視角沒有提供的信息,部分反映出機械史在設計史書寫中可能提供的幫助。
4 啟示:中國設計史的內外經驗
“長信宮”燈的歷史書寫,給我們提供了包括考古學、工藝美術史、設計史等學科專業在內的文本樣本,這種結果顯然沒辦法令我們感到滿意。我們需要什么樣的中國設計史?如何來書寫今天這個時代的中國設計史,是一個需要所有設計史家深入思考的問題。設計歷史的書寫雖然有著悠久歷史,但作為學科的設計史卻是年輕的。如果把1977 年英國設計史學會的成立作為其正式進入學術視野具有標志性的事件,也不過40 余年,中國設計史的研究顯然更短。時間雖然短暫,設計學科與設計史的發展卻經歷了非常重要的發展,世界范圍內出現了各種設計史寫作的探索和嘗試,體現出設計史一種強烈的“學科自我反思”。也正是得益于這種學科意識的覺醒和探索,設計史的研究日新月異。

圖5 “長信宮”燈國外展覽性介紹的相關內容
一開始,設計史是沿襲藝術史和工藝美術史的傳統,將典型的“物”、代表 “人物”作為其關注的核心,即所謂“造物”“設計師”研究,這類研究采取的是英雄史觀,關注的是代表性、經典的案例。如1936 年尼古拉斯·佩夫斯納的《現代設計的先驅者:從威廉·莫里斯到格羅皮烏斯》。接著,設計史的研究跳出了“造物”“創造者”局限,拓展到了“無名”領域,這是設計由經典向日常、由英雄到大眾的轉變。如1948 年西格弗里德·吉迪恩《機械化的決定作用:對無名史的貢獻》和1964 年伯納德·魯道夫斯基的《沒有建筑師的建筑》等。設計史開始轉向“塑造物、人以及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各種轉譯、改編、交易、變化以及變形的歷史”[21]3。這一轉向給設計史研究帶來了廣闊天地,同時其他學科介入設計史的探索也更為深入和普遍。設計史與社會史、女性主義、思想史、技術史、物質文化(米勒1987 年出版的《物質文化與大眾消費》、莉森·J·克拉克1999 年出版的《特百惠:20 世紀50 年代美國塑料的前景》、阿特菲爾德2000 年的著作《野性之物——日常生活的物質文化》、史密森學會的學術會議論文集《來自物的歷史》《從物得悟》)、文化史(雷吉娜·李·布拉什奇克2000 年出版的《想象消費者:從韋奇伍德到康寧的設計與創新》、保羅·貝茨2004 年出版的《日常物品的權威:西德設計文化史》)等之間進行深入互動,似乎可以理解為以下3 個存在遞進、循環關系的過程。當然,這些過程并非具有明顯的界線或者先后順序,每個階段都可能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另一個階段。一是從一種宏觀的整體架構出發,描述出一個大致的設計史輪廓。二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傾向于聚焦具體學科、具體問題或微觀案例的研究。三是由于分科研究、微觀研究和案例研究導致的“碎片化”,又需要找到一種能夠增強這些成果凝聚力和內在聯系的“宏觀理論架構”或“有效的整體思維視角”,將其進行有機建構為一個新的整體。
對于設計史的研究觀察,傳統的做法習慣于從藝術史、工藝美術史獲得的編年史體例,是設計史書寫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轉向,則是類似出現的作為技術和材料史的設計史、教育和觀念史的設計史、物質世界的人類學與經濟史的設計史、人造物符號功能史的設計史和與設計相關細節的日常實踐史的設計史等的轉向,這是分科研究賦予設計史的不同維度。當設計史轉向文化史時,又在此回到整合、平衡、協調各分科研究成果的過程中,旨在推動多學科相對獨立研究之間的“凝聚力”與“互動性”,設計史發生了質的變化,并重新構建并闡釋了更具深度、寬度和廣度的自身。
正是由于“在追溯歷史時內置的含糊性,并具有各種本質性張力,這些張力存在于意識形態與實踐之間、心靈與物質之間、文化與商業之間、生產與消費之間、實用性與符號性之間、傳統與創新之間以及真實與理想之間”[21]2。 因此,設計史的研究始終在“尋找一種平衡跨學科方法去抵消一種幾乎從單一審美維度評估設計的藝術史的方法,其中更重要的是找到一種方法可以呈現設計本身的跨學科特點”[21]26。
由此,以上所述對中國設計史(古代)的研究有什么啟示呢?筆者嘗試總結了以下5 點看法:
第一,要總體把握古代制度文化、市民文化、經濟狀況、技術水平、生產體系和生活觀念等,特別要重視考古文獻與實物的考察,這方面需要對中國(或其他國家)古代的歷史文化整體相當熟稔,對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持續動態的關注,以此作為設計史寫作的宏觀背景,并融入到“物”“物背后的歷史文化肌理”“物的生產、流通、傳播與消費”等的具體解讀當中。
第二,要充分吸收目前國內外設計史跨學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法,針對具體的研究對象制定不同的研究路徑,進一步探索設計史的新寫法。比如設計史的文化史視角、設計史的物質文化視野、技術史材料史、社會史的視角等。
第三,不應耽于設計史與其他史學研究的邊界困惑,而以解決具體問題為導向,始終保持設計史研究的開放性與包容性。設計史研究既不可能完全拋開藝術史、工藝美術史的研究成果借鑒,也無法獨立于人文科學的思想價值體系。因此,建立設計史與其他一切相關學科的良性互動關系,事關設計史研究的成長性與生命力。
第四,如尚剛先生所言,明代前后的中國設計史研究,對材料的倚重和具體研究方法具有明顯的差異。明代以前文獻相對較少,主要依靠考古發掘的實物。“二重證據法”中,對于實物本身的全方位、細致入微的研究應該是設計史研究的重點。這一類實物研究既包括博物館陳列的經典文物,更要側重于包括李立新等強調的“田野中”的“文物”——即民間散落的日常之物。
第五,設計史的研究不應局限于向后看的滿足,更應體現出向前看的思路與價值導向。由于設計學科本身具有非常強的實踐性特征,這就要求設計歷史的當代詮釋都應該建立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方法論框架下進行,才能由“史”的研究導向“實踐”的推進。從這一點來看,可能設計史的研究訴求比任何其他學科都更為強烈。
5 余論
當今多數中國古代設計史著作,很大程度上承襲延續了“藝術史”“美術史”“工藝美術史”的傳統路徑,對于設計、設計史的理解或書寫,在方法上、文獻上、視角上突破和創新仍顯不足,有限的“設計”演繹研究亟需加強科學考證和嚴謹性。中國設計史的書寫既不應該、也不可能回到工藝美術史的老路上去,因為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變了;也不能僅停留在完全攫取現代設計的概念而生搬硬套,因為歷史傳統和文化語境仍存。從設計史各個相關學科關于“長信宮”燈的書寫文本“管中窺豹”,我們似乎可以看出研究存在的短板和未來的努力方向。
誠然,如方曉風所言“設計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確實面臨研究范式的問題,研究范式的確立,不是朝夕之功可以完成的,但不能因此而無所作為。設計學的研究范式總體上還處在摸索的階段,遠未達到成熟的狀態,在現階段還是需要對可能的范式有所提示,推動整個學科更好地向前發展”[22]。
有學者曾經提出,中國的工藝美術史應該由中國學者書寫。同理,中國設計史的書寫即使不是全部由中國學者來書寫,我們也應該對自己的設計史研究承擔最主要的責任。“長信宮”燈并沒有引起國外學者的深入研究,一般稱之為“Douwan’lamp”或“Changxin Lamp”,僅有少數一些展覽介紹和研究文獻也基本上是置于秦-漢藝術大背景下的粗略概述。“長信宮”燈的設計史研究,僅僅是中國設計史中的“滄海一粟”,但由此給我們帶來的思考空間是巨大的,也留下了一些懸而未決的疑問。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科學研究與實驗探索來驗證支撐。此外,“長信宮”燈的生產工具、生產工藝、宮廷用物的民間參與、工匠技藝的民間性與宮廷性之間的關系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研究者只有充分利用現代技術的手段,更加充分全面地認識每一件充滿智慧的“遺物”,詳細的一只一只地“解剖麻雀”,才可能脫離虛華的辭藻和感性的溢美之詞,達到中國設計史研究應有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