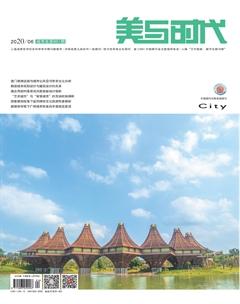游客感知視角下益陽禪宗文化旅游形象探析
陳慧君 高赫添
摘 要:為探索湖南益陽禪宗文化發(fā)展模式,解析禪宗文化旅游形象結構,文章以益陽白鹿寺風景區(qū)為例,通過實地考察、數據分析等方法,分析游客對白鹿寺旅游景區(qū)的表意形象認知、情感認知以及文化認知等因素,為進一步完善白鹿寺文化景區(qū)旅游形象的結構模式奠定可靠的數據信息。結果顯示:游客對于白鹿寺旅游形象的感知多在于情感認識,對其表意形象認知相對較弱;游客感知所產生的差異性主要受到游客年齡、閱歷、文化背景、旅游次數以及景區(qū)當地經濟線路等因素影響;對于游客反饋內容進行分析,游客對白鹿寺文化旅游景區(qū)評價相對較好,且游客重游率與推薦率相對較高。
關鍵詞:益陽白鹿寺;表意形象認知;情感認知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0年益陽市哲學社會科學課題“基于游客感知的益陽禪宗文化旅游開發(fā)評價及模式研究”(2020YS179)研究成果。
一、益陽白鹿寺旅游景區(qū)概述
文化旅游景區(qū)在建立完整文旅體系的過程中,文旅景區(qū)形象的確立是文化旅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和完善文化旅游地形象有助于對旅游地進行合理規(guī)劃定位并進行商業(yè)戰(zhàn)略營銷。因此,游客對于禪宗型文化旅游的行為感知特征、形象感知異同及未來對同類型景區(qū)形象對比,以及根據游客感知通過文旅景區(qū)形象進一步進行文化輸出為本文研究的出發(fā)點。
白鹿寺之名源于公元806年,廣慧禪師在茅庵聚眾弘法,曾遇白鹿銜花獻佛之奇觀,此事廣為流傳,唐憲宗獲悉后,經查實準奏建立寺院并賜名“白鹿寺”,而白鹿寺所處山頭也因此得名白鹿山。現今白鹿寺建筑體系健全,佛像種類眾多,包括彌勒佛殿、觀音殿、大雄寶殿以及藥師殿等,個別殿堂內部侍立其他神佛像,如彌勒佛殿中主佛旁侍立四大天王,大雄寶殿內部侍立十八羅漢,是益陽市規(guī)模最大、歷史最為久遠的寺廟之一。白鹿寺從唐宋時期的興起、明清時期的鼎盛,到20世紀60年代前后寺廟被毀壞,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寺廟重建可謂幾經浮沉。2003年3月底白鹿寺徹底完成了寺院的最后修繕,并以白鹿寺為中心開發(fā)相應的旅游產業(yè),包括旅游決策、賓館飯店、旅行社、交通線路、文創(chuàng)旅游產品等一系列文化旅游產業(yè),形成高效益的旅游產業(yè)鏈,為益陽的文化旅游產業(yè)發(fā)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近幾年來,益陽文化旅游吸引了大量的境內、境外游客,2019年1至7月,益陽市接待入境游客人次數、人天數分別為22991、37698,同比分別增長30.12%、45.13%;入境旅游(外匯)收入737萬美元,同比增長41.5%。三個增長速度均名列全省第二。攜程網的數據顯示,根據14374名去過益陽白鹿寺的游客的信息反饋以及旅游建議,14371名游客表示對白鹿寺有一定的興趣并表示想去。
二、游客行為模型下益陽白鹿寺旅游地形象構建
文化旅游形象的確立是景區(qū)文化輸出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通過對文化概述、觀念輸入、地方文化以及大眾對文化所持有的信仰、直觀印象進行高度整合,形成一個視覺、聽覺、感覺三維一體的感官型觀念文化旅游形象系統(tǒng)。現如今禪宗文化旅游事業(yè)也借此勢頭逐漸興起,因此出現了許多學者針對這一內容進行深入研究:李偉、李露在對國內游客自駕游行為數據進行分析時,以河南省游客為典型例子,通過對游客認知形態(tài)、情感意識兩大方面進行數據整理,探析河南省整體旅游形象;呂麗、王娟等選擇禪宗名勝古跡為研究方向,以武當山為典型建設旅游形象,在認知、情感的基礎上融入了對景區(qū)整體感知的內容;Echtner與Ritchie 從不同角度對目的地形象進行了全面的概括,認為旅游地形象包含三個連續(xù)的緯度,分別是功能/心理軸、普通/獨特軸和整體/屬性軸; Fakeye 與 Crompton將旅游地形象分為原生形象、引致形象、復合形象。
三、研究方法
根據上述基礎理論和相關研究內容的分析與整理,此次對白鹿寺的數據測量基于對前人研究的數據,運用“結構法”對白鹿寺文化旅游景區(qū)的表意形象認知、情感認知和文化認知等內容進行進一步的細分和觀測。形象認知的測量指標是建立在景區(qū)資源、地方文脈特征的基礎上進行數據收集,涉及旅游景區(qū)特色資源(自然、人文特色資源)、景區(qū)設施建設(包括基礎設施、休閑娛樂設施)、景區(qū)服務(路線導航及標識、導游及服務人員態(tài)度、安全設施等)。
(一)研究設計
文章根據白鹿寺文化旅游景區(qū)自身特點設立了相應的測量項目。情感認知的測量方式通過心理學的評價方式進行數據評估,測評內容是指游客對白鹿寺各方面的感知,通過使用“毫無吸引力的”“令人身心愉悅的”等情感詞匯進行區(qū)間劃分,明確游客感知的情感維度。根據游客對上述文化的評價,對相應文化產品的購買欲等方式進行數據分析。
(二)數據收集
本次調查采用隨即抽樣調查的方式,以網絡為媒介隨即發(fā)放調查問卷,有效回收176份,有效率為92.7%。此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女性居多;15至25歲的年輕群體總數約占42.71%,26至35歲群體人數也偏多,占比約28.1%;旅游者文化多以大專以及本科以上為主,約占69.4%,旅游者文化總體程度偏高;首次來白鹿寺文化景區(qū)的游客占比偏高,占比約76.1%,二次來白鹿寺的游客占比14.5%;對游客后期反饋數據分析,游覽過白鹿寺后愿意將白鹿寺推薦給親朋好友的占比較大,占比約93.2%;游客旅游目的多以觀光游覽、休閑度假、禪宗朝拜為主,其中禪宗朝拜占比12.7%。
四、游客感知視角下白鹿寺旅游景區(qū)形象差異分析
相對于其他類型的旅游景區(qū)的游客,禪宗旅游景區(qū)的游客感知在不同程度上會產生較大的情感差異,產生差異的原因首先是受眾文化背景對白鹿寺文化理解程度產生一定的偏差,其次游客在旅游前所設立的旅游目的有很大區(qū)別。本此研究將游客劃分為游覽觀光、休閑娛樂、求佛求知、療養(yǎng)等幾大類,其中求佛求知類型的游客占比數量偏大,大部分屬于信徒類型游客,信徒對相關禪宗文化的內容有較為深刻的領悟能力與研究能力,導致其在游覽過程中會抱著朝圣的心理對白鹿寺景區(qū)的自然景觀進行主觀行為感知。
(一)研究結果分析與探討
文章從游客感知的角度分析白鹿寺旅游文化旅游景區(qū)旅游形象,結合游客在游覽過程中對白鹿寺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的情感感知、形象感知與人文感知三方面內容的數據進行整理分析,針對不同類型的游客的旅游意向進行區(qū)間分類,解讀游客所產生的不同類型的感知差異,所得結論如下:
游客對景區(qū)的表意形象認知主要是對景區(qū)自然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以及與其相對的服務環(huán)境三方面進行形象認知。白鹿寺文化景觀形象相對于自然景觀形象更為突出,但游客在游覽過程中對文化的領悟程度相對不足,除卻信奉佛教的游客外,游客對文化感知的程度隨著受教育程度、對白鹿寺的旅游頻率或對其他有相似教義的景區(qū)的旅游次數等數據上升而逐步升高。
數據分析顯示,白鹿寺文化景區(qū)旅游形象的確立主要受到游客表意形象認知與情感認知兩方面影響,其中情感認知所占比重較表意形象認知比重更大。表意形象認知即是對景區(qū)自然資源、人文資源的第一形式進行直觀認識,其認識方式類似于圖像學第一階段對事物自然含義的直觀判斷。游客根據自身經驗、閱歷將在白鹿寺所聞所見與預想過或者游歷過的類似寺廟、建筑、景物進行直觀對比,形成對白鹿寺的表意形象認知,調查顯示,游客對白鹿寺表意形象認知與其他景區(qū)的類似建筑重復度過大,使得形象認知這一內容對白鹿寺旅游景區(qū)的旅游形象影響相對較小。
(二)研究局限
此次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日后的研究將會對白鹿寺文化旅游景區(qū)進行進一步深入探索。第一,在分析不同類型游客對白鹿寺旅游文化景區(qū)的表意形象認知、情感認知的同時,有必要與其他不同類型的旅游景區(qū)游客的認知進行比對,根據比對數據對旅游景區(qū)形象進行調整,檢測結構模型的實用性與適用性,同時進行游客感知數據的二次收集時,應將季候交替、環(huán)境變遷等環(huán)境因素考慮其中,研究游客感知是否會因為以上因素而產生一定的改變。第二,本次數據收集基數雖然是200人,但檢測內容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未來研究將會增加數據基數,提高容錯率。第三,本次研究主要對象為益陽白鹿寺景區(qū),白鹿寺屬于佛教一脈,其旅游景區(qū)結構模式并不一定適應益陽其他文化旅游景區(qū),因此在進行模式推廣之前應結合其他景區(qū)的游客感知以及文化輸出形式進行分析。
參考文獻:
[1]李偉,李露.基于內容分析法的國內自駕游客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以河南省為例[J].四川旅游學院學報,2020(2).
[2]趙炎秋,姚堯.21世紀國內圖像理論與視覺文化研究述評[J].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9(4).
[3]李霞,余榮卓,羅春玉,等.游客感知視角下的國家公園自然教育體系構建研究:以武夷山國家公園為例[J].林業(yè)經濟,2020(1).
[4]呂麗,王娟,賈垚焱,等.宗教名山型旅游地形象感知與游客行為意向研究:以武當山風景區(qū)為例[J].旅游經濟,2020(1).
[5]杜夢醒,劉萍.基于游客感知角度提升旅游景區(qū)服務質量的對策研究[J].經營與管理,2020(3).
作者簡介:
陳慧君,博士,湖南工藝美術職業(yè)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視覺藝術設計。
高赫添, 湖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藝術設計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視覺藝術設計。